|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第二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并非一部考据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而是旨在提供一种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式。从1992年到现在,这种图式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依然经受了考验,并未被后来的研究成果超越。
全书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
从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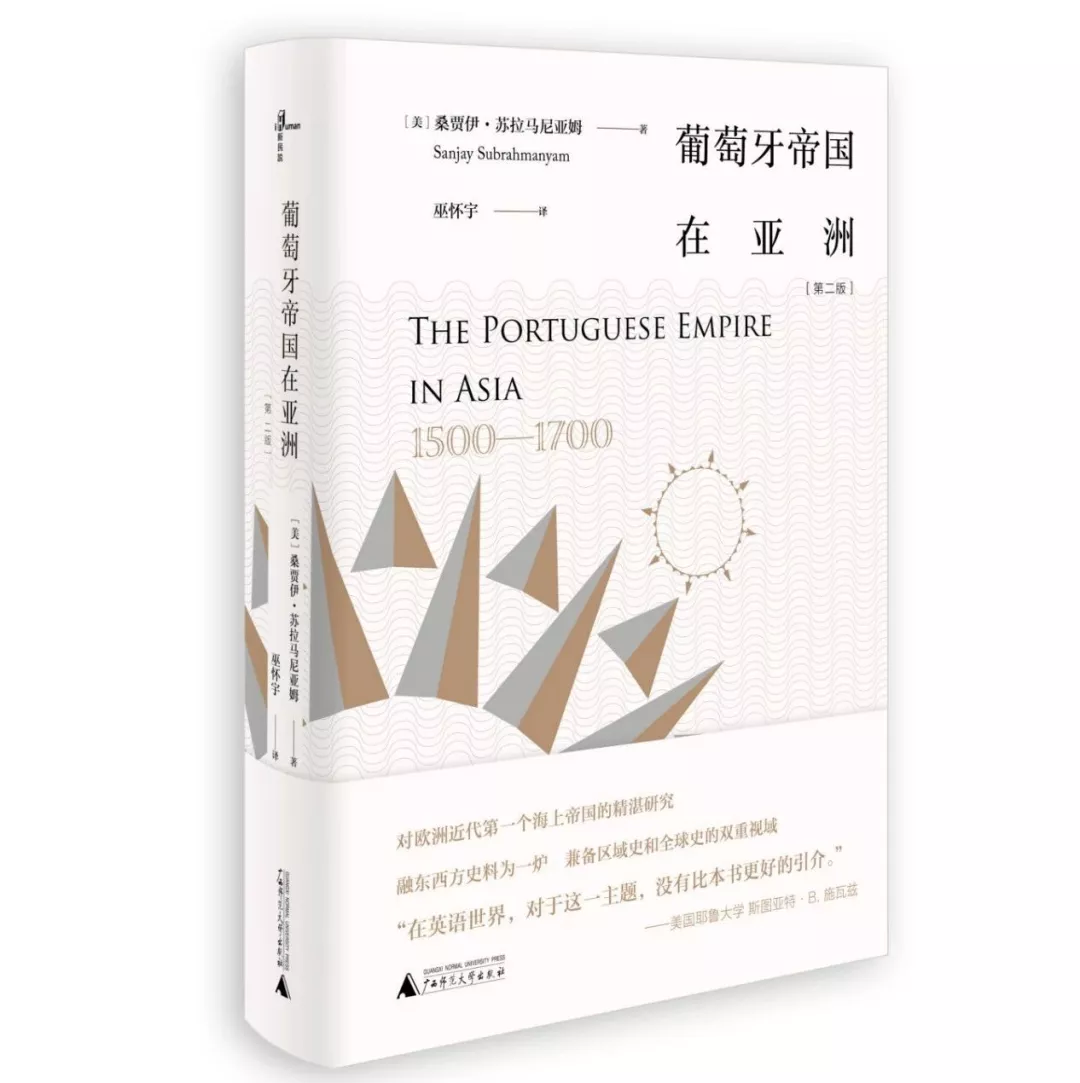
在强盗行径与资本主义之间
在17世纪早期,一艘来自欧洲的船只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遭遇了海难。幸存者中有一群后来哗变了,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信徒,这一团体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万物,万物必然皆善,恶就不存在。懦弱的船长乘小舟逃跑了,哗变者控制了船上的幸存者,他们后来杀死了大部分的男人,女人则留下做小妾。最终,上级部门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由原来那艘船的船长带领去镇压哗变;大多数哗变者被杀,还有一些被放逐荒岛。
这群人究竟是欧洲哪国人呢?这一事件中他们没有姓名和头衔,所以很难猜测。是这一时期偏离航向的意大利或法国探险船吗?这些船经常在马达加斯加、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ignes)、苏门答腊等地遭遇不幸和混乱。他们是不是葡萄牙人,而这是18世纪早期编写并于里斯本出版的《海上悲剧史》(História Trágico-Marítima)的节选?抑或他们是英国人,而这个故事是后来出现的赏金猎人被歪曲的先驱?
事实上他们不是以上任何一国人,而是荷兰人。这艘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号,于1629年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的阿布罗霍斯(Abrolhos)群岛遭遇船难。船长弗朗西斯科·佩尔萨早些年曾是荷兰驻苏拉特的代理商,以编年体这种当时在荷兰并不流行的形式,
写下了关于莫卧儿帝国史的鸿篇巨作。他后来声称巴达维亚号的船难是上帝对哗变者的报复,并最终在审判席上直面哗变者头领杰罗尼穆斯·科内利斯(Jeronimus Cornelisz),下令先砍下他的手,再吊死他。
17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人中,这样的行为和事件屡见不鲜,常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讲述。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它们带着典型的中世纪式残酷,甚至——就这起哗变本身及其意识形态而言——是非理性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无法与荷兰人朴素、理性、加尔文主义且精于算计的形象相契合,这种形象在关于该时期的历史写作中随处可见。这一整个插曲显然更能嵌入西班牙或葡萄牙扩张的历史图景。
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是,我们赖以写作史书的史料并非总会确证历史学家们的偏见。关于葡属亚洲的写作中偏见太多,既有葡萄牙民族主义史学家的,也有亚洲人、非洲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其中一些可以被迅速丢弃,基于它们要么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葡萄牙人在追求超验目的和价值中的“普世使命”(universal mission),要么时代错乱地将现代国际冲突的模式套在16世纪。但其他一些视角值得深思,因为它们植根于对诸体制的比较研究,在当今历史学家中广为流传。韦伯式解释仍是研究早期近代亚洲的葡萄牙人的主流解释。
该解释路径受到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决定欧洲诸民族历史的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区分的启发,声称就像南欧其他国家,这一时期的葡萄牙在制度和心智上,都比北欧(尤其是新教国家)远为更接近亚洲。尽管葡萄牙人比亚洲人更为精通海战,但他们与亚洲的相遇很难产生丰富的创造力,因为二者的体制都仍属于前现代的旧世界。更重要的相遇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人、荷兰人与亚洲之间。
以上概述的观点并非韦伯本人清晰表述的(尽管可想而知他会赞同它),而是出自一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华横溢的荷兰社会学家凡·勒尔(J. C. van Leur)。他的比较视角如下:
葡萄牙人的权力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其功效有限。尽管从果阿到欧洲的船运受集中控制,但他们的领土星散于数千英里跨度上的定居点港口,没有多少统一性。也没有区分民事和军事部门的官僚等级制,只有一群贵族和雇佣兵队长,其中每个都有自己的跟班和心腹,或出于忠心、或为求私利而追随他们。有权威的官员常常自己置办装备,并想方设法以权谋私,缺乏长远的考量。葡萄牙人的权力并不源自接管东方贸易或建立领土权威,而是征集贡赋和战利品。非经济动机——对掠夺,而非对利润的渴望——在其海外扩张中扮演了首要角色。(Van Leur 1955: 170)
他进一步指出,葡萄牙人“脆弱的帝国”是建立在“战争、强制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并未真正触及亚洲的“传统商业结构”。这是因为葡属亚洲政权的商业和经济形态“与亚洲贸易和亚洲政权的相同”。他的定论如下:
葡萄牙殖民地政权没有在南亚引入任何新的经济因素。它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态——垄断、财政压榨、政府的“财政化”——都源自哈里发王国和拜占庭,然后转移至葡萄牙,而且可能被那里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继续进行……并非里斯本和塞维利亚,而是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恩克赫伊曾和伦敦成为了新时代的先驱。(Van Leur 1995: 118-119)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该观点在1960年代初为梅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等学者所争议(1962),又在下一个十年由丹麦学者尼尔斯·斯滕嘉德赋予了新的生命,他的观点——正如韦伯和凡·勒尔一样——也是比较研究的。他们将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人在17世纪初的正面交锋,视作欧洲与早期近代亚洲关系的结构性危机的症状。斯滕嘉德将在亚洲的葡萄牙人和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归为一类,视作“再分配性企业”(redistributive enterprise),并与东印度公司进行对比,后者在组织上的理性、经济,且以利润而非权力为目标,使得它们成为“生产性企业”(productive enterprise)(Steensgaard 1973)。
凡·勒尔与斯滕嘉德的方法特征是结构性的,即假定荷兰人、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的制度集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有其独特的本质结构,然后对这些本质结构各自的特征予以辨别,并暗中将其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例如文化差异。这样一种路径在定义上就预先排除了葡萄牙人的心智、制度和方法在1510年可能不同于在1610年,也排除了不同的葡萄牙人群在整个事业中可能有不同的路径,而且其权重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
最近关于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著作质疑了这一立论的基础,即认为该时期荷兰的社会组织观念是由强调勤俭、节约和盈利的实践(对立于“理论上的”)伦理主导。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举例指出,这一时期荷兰的商业大家族——像特里普家(Trips)——的生活一点都不节俭;至于另一方面,即对利润的渴望,以及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家精神,在荷兰社会的既有体制内,都遭遇了强有力的反对。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这一时期的荷兰贸易并非很热衷通过竞争提高效率,而更倾向于通过立法、国家权力和暴力来推动贸易。这即是荷兰国际贸易的扩张与收缩的时间点,与它的政治变动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Schama 1987: 339-343; Israel 1982,1989)。另外,历史学家曾迷崇“特许贸易公司”及其理性,如今越来越清楚的是在尼德兰的这些机构背后,长期都有家族和庇护人组成的网络,可与英属东印度公司和伊比利亚人的网络并论(Adams 2005)。
另外,我们已经知道,在荷兰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控制远途贸易的全球斗争中,没有哪一方做到了赢遍全球。荷兰人赢得了亚洲,但巴西以及宽泛意义上的南大西洋,直到18世纪仍在葡萄牙人手中。如果两者真的是“中世纪”和“近代”的斗争,且一套制度注定(如凡·勒尔和斯滕嘉德所设想的)要取代另一套,这种不齐一的结果就无法解释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要么是当地环境和力量的居间作用,导致了这一差别,要么结果其实取决于竞争者在诸地区的武力投送能力。如果后一种理论能够成立,荷兰人在亚洲“胜利”的原因,就比“制度创新”或特许贸易公司的独特性,要俗套且具体得多了。
我们同样要注意,荷兰人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他们在亚洲的胜利。17世纪的最后20年间,英国人迅速在欧亚贸易方面赶上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内部贸易方面,荷兰人在大约 1700年之后就停滞不前了,此后的真正获利者是英国私营商人,他们的组织模式与特许贸易公司并无多少相通之处。从这一视角看,那种熊彼特式的观点,即将17世纪初视作小规模贸易运作的终结和大型(且明显具有创新性的)贸易垄断时代的开端,有些人为武断。
因此本书也部分关心在后见之明中固有的危险,这一路径会将历史学家引向最危险的陷阱——时代错置。不幸的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分化与裂解,影响了那些研究更早一个时期的历史学家,也影响了葡萄牙在亚洲的历史的写作方式。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第二共和国(Estado Novo)的黑暗岁月中,葡萄牙人在其他欧洲人眼中的形象,即“欧洲的黑人”(Kaffirs),在某些意义上与被殖民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相差不大。正如后者的“落后”常被归因为它们的文化体制,以及它们在摆脱这些据称已然陈旧过时的东西上的无能,葡萄牙也被视作如此。当然一个区别仍在:20世纪的葡萄牙仍然有殖民地。但这还不如说,是它的制度陈旧过时的另一证据;这些领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而纯属历史惯性的结果。一边是葡萄牙、西班牙、南欧某些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另一边是北欧和北美——这一空间上的区别一旦确立,时间上的区别也就相应建立,即试图将欧洲人在亚洲的行为,大约以1620年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将“传统”与“近代”分离开来,同时断言在亚洲(甚至伊比利亚)的历史中,16世纪并不具有作为转变阶段的历史意义。
在此,人们应当回忆起,这一路径是葡萄牙历史学家自己也有参与,且持续性地为这座辉格史学(Whig)的大厦添砖加瓦。V. M. 戈迪尼奥的著作是现代关于葡萄牙人在15至16世纪海外扩张的最重要史学作品,其观点近于认为,商业扩张未能影响到葡萄牙其心智、态度和社会结构(它们仍是古老的和封建的,而不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和资本主义的),这导致了葡萄牙的落后以及在16世纪末的注定失败。他如是说:
15至16世纪的商业化(在我们严格界定的意义上)产生了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它将自身封闭在僵化的界限之内,如此在后世既无法成功地工业化,也无法进入科学与公民权的领域。(Godinho 1981-1983, iv: 223)
亚洲史学者们对这种立论相当熟悉,他们提出了类似的“均衡陷阱”(equilibrium traps),认为它使得亚洲在 16至17世纪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然而我们贯穿整本书的观点则是亚洲和欧洲的变化才是值得注意的,葡萄牙人所闯入的这个亚洲政治与商业世界,在1700年时已经与1500年时截然不同。那么其中发生的基本变化有哪些呢?
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说过,1500年之前的亚洲国家可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大型的农业国家,大多位于内陆;另一类基于贸易,例如霍尔木兹、亚丁、卡利卡特和马六甲。1500年之后这一区分开始消解,商业精神开始广泛流行于很多国家,使得它们在贸易上更积极主动。这一变化部分源自精英人群的跨地区迁徙流动,以及最初兴起于商贸界的会计和管理技术被国家所采用。同时,比起之前的世纪,1500年后的诸世纪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此前未曾有过的可能性。贸易量增加了,商品的种类也多样化了,其中包括大量金银条、手工制造品和香料。葡萄牙人正是在这一变动的背景中活动的。

在葡萄牙人于1500年前后首次航海探索亚洲时,葡萄牙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比较直接的角色。国家本身被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张力撕扯着,在航海扩张问题上没有显见的共识,这解释了为控制贸易的可能性而成立的几届政府都很短暂。16世纪初,葡萄牙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重商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奇怪结合,前者鼓励印度洋贸易,后者为取道红海攻打耶路撒冷提供了动机。这一意识形态渐渐地被另一种精神所取代;到16世纪中叶,国家认为贸易有损于其尊严,开始撤出。对此,国内外皆有批评,16世纪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曾是唐·若昂三世的崇拜者,在世纪中叶也以诗《多名》(In Polyonymum)讽刺他:
独一无二的卢济塔尼亚人, 作为阿尔加维、印度、阿拉伯、 波斯、几内亚和非洲、 刚果、曼尼刚果和索法拉的统治者,
你的名声遍布海的两岸。 你至高的头衔囊括了 埃塞俄比亚的炽热之地, 和大洋,这环绕三大陆的万水之父。 没有哪个港口、贸易和岛屿中的 最轻微的利润不曾为你的头衔 贡献它们的光辉。 因此,既然你有如此多的名字, 我是否应当称你为多名的伟大君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