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祠,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礼记·祭统》:“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褅,秋祭曰尝,冬祭曰烝。”《谷梁传·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烝”,晋范宁注:“春祭曰祠”。《公羊传·桓公八年》:“春曰祠”,东汉何休注:“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从这些文本的解释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祠的意义所在,所谓祠,其原意专指春祭,指的是春季在宗庙进行的祭祀活动,一般而言这是指天子或者诸侯的祭祀行为,当然后来也逐渐用来泛指祭祀活动。因祭祀活动总是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所以,祠又可以作为供奉鬼神、祖先或者先贤的祠庙。由此,当我们说到祠的时候很容易同祭祀的仪式、祭祀的场所以及祭祀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礼记 
而祭祀的行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的重要性甚至在战争之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从远古开始就非常重视祭祀。按照何休的说法,“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公羊传·桓公八年》何休注),祠祀之重要性就在于,这样的一种行为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向祖先或者神鬼表示敬献贡品以供食用,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宗族的繁衍,换而言之,这就是孝之表达的具体形式。由祠而食而孝,宗法伦理的根本精神由此而确立。正是因为祭祀这样的事情关注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行为表达,更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是社会统治的基本伦理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价值是超越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的。所以,按照《左传》的说法,祭祀是国之大事,甚至排序还在战争之前。这里至少传达出两条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传统中国社会非常重视祭祀这种行为,换句话说,祭祀是受到普遍重视的日常行为方式。所以,在历史的具体事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与祭祀相关的行为被不断地提起,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比如祭天告祖,比如春、夏、秋、冬等等,无不是以祭祀的形式来表达敬畏和感激之情的。有祭祀就有一定的祭祀礼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传统的礼文化。其次,祭祀的功能并不在于祭祀行为表达的本身,换句话说,祭祀的意义超越于祭祀形式本身。从形式本身来说,祭祀不管它的具体程序如何复杂、如何差异,其所传递出来的都是献祭者与祭祀对象之间的关系,亦即献祭者通过一定的仪式向祭祀对象表达其情感。但是,祭祀的意义则超越于这种情感表达的,亦即献祭者通过献祭行为所要传达的意义可能是超越于行为本身的,比如传达对于宗法制度的孝的观念的重视,以此强化孝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等。简而言之,就是说,祭祀这种行为具有普遍而又超越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普遍而又超越的意义和价值直接所指向的实际上就是信仰的维度,也就是说在祭祀行为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其所传递的信仰内容。而祭祀之所以能够具有信仰的维度,其原因在于首先祭祀所面对的对象是已去世者,而在逝者背后所传递出来的是灵魂不灭的观念,既然逝者的灵魂是不灭的,而不死的灵魂毫无疑问可以护佑生者。在某种意义上说,灵魂不死的观念构成了生者祭祀逝者的桥梁,正因为不死,所以信仰才具有了超越现实的可能,或者说满足生者对于超越存在的期望。 由此而来,就产生了信仰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突破自身限制的需求而转向对于超越者的依赖,从而获得生存的安全感。于是,在每一种祭祀仪式的背后,都毫无疑问地透露出了其信仰的维度,比如祭天告祖的行为,传递的是对于天地神鬼和祖先亡魂的信仰;对于往圣先贤的祭祀,传递出的是对于先哲的精神力量的信仰。所以,祭祀是表达信仰的一种非常普遍而有效的方式,正是在祭祀行为中,个体或者群体的信仰透过具体祭祀行为实践而得以传达出来。 洪氏宗祠 
由于宗教性的信仰对于个体或者群体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个体或者群体在其现实生活之中都会由于自身的有限性(或者局限性)而产生的对于现实状态的不安,甚或是恐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超越个体的、现实的有限性之上的力量,来给个体以精神的依靠和现实的慰藉,从而使得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能够突破自身有限性的可能,得以积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未知因素而获得安全感。出于自身的安全感的需求,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普遍存在原始先民群体中,就非常直接地表明了宗教信仰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与人类相伴随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人类就会有宗教信仰的存在。而信仰之产生的基础,如前所言即在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因为被信仰对象之能够成被信仰者所接受,其最基本的特征即在于它是超越于现实的、具有被信仰者所不具备的某种能力,如天地先祖对于人类的赐福护佑等等。于是,祭祀逝者,成为了建立生者与死者(或者说信仰者与被信仰对象)之间联系的根本桥梁。因为祭祀是生者与死者之间情感沟通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现实的,即通过献祭(如上文所言的“食”),表明信仰者与被信仰对象处于一种非常亲密的事实联系之中,这种亲密性的纽带使得通过祭祀的方式而获得被信仰对象的护佑成为可能。所以,如果缺乏这样的亲密纽带,则祭祀行为是要受到质疑的,并且其所能达到的事实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此外,任何的祭祀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的,这些仪式并不是简单的程序性过程,而是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的,仪式是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有许多功能,无论在个人层面上,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者推翻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通过仪式将宗教生活有序地组织起来,使得宗教得以继续存在;仪式又是一种手段,社会集团凭借这一手段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同时将整个宗教组织内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企求的统一体。因此,“行为中的宗教主要通过仪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仪式是行动中的宗教”,宗教仪式不仅加强了信仰者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个人与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宗教仪式在本质上被看作是用来表达和加强集团情感和团结的一种主要途径,也是集团进行教导和道德训诫的一种重要手段。爱弥尔·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便对宗教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宗教明显是社会性,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仪式不仅需要通过群体发挥作用,而群体也需要通过仪式产生作用。因此,两者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选择。而正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宗教形式所具有的意义被凸现了出来。 爱弥尔·涂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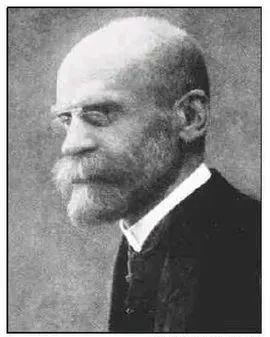
正是因为祭祀对于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传统中国社会中,祭祀也是受到了最为重要的关注,被认为是国家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而祠庙则是传统中国社会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所以,要考察中国的宗教性传统,就不能不考察祠祀的社会生活事实。祭祀活动的信仰维度,即在于祭祀者通过具体的祭祀活动而将自身与超越结合起来,从而获得现实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宗教活动的事实内容和宗教的仪式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活动,祠祀也必须是规范化的,将祠祀纳入统治的范围,也是政治与信仰之间关系的最为简单的表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对于祠祀的对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有功烈于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从《礼记》的这段规定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传统祠祀的基本限定。首先,祠祀的对象是相对广泛的,也就说祠祀并不一定局限在祖先,包括山林、川谷、丘陵、日月星辰在内,都可以成为祭祀的对象,这与万物有灵的基本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其次,虽然祭祀的对象非常广泛,但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标准即在于能否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有功烈于民、民所取财用,这个标准表明了儒家的伦理教化的基本倾向和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换而言之,要成为被祀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祠祀看成是宗法血缘社会的基础,只是从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上去讨论祠祀问题。但是,如同前文所言,祠祀所包含的信仰维度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祠祀的存在及祭祀的方式,都表明了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形式的载体,祠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了解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祠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离开祠祀,实际上就是离开了中国人信仰生活的基本事实,于是也就会产生诸如中国有无宗教问题的争论。其实,中国传统有无宗教并不重要,这里涉及的更多是概念界定、理论探讨的问题。而宗教信仰更多指向的是人类生活的具体事实,所以,要讨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就必须进入中国人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事实,这就是以普遍而又持久的祠祀信仰为基础的日常宗教行为方式。
伦理的教化,实际上所传递出来的,也是一种对社会确定性和安全感的追求,这种确定性是建立在社会价值的稳定性基础之上的。或者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或者就是社会功业的楷模,除此之外,即不够成为祠祀的资格的。
由此,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就有了正祀和淫祀之别。所谓正祀,即是被国家所认可的祠祀,这也是国家权力介入宗教信仰的基本表现,“凡、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非是,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这是具有神道设教意义的行为,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卦》),它所指向的乃是对于社会的伦理教化的意义和社会整合的需要,由此而达到统治的良性秩序。而淫祀,则是指那些没有列入祀典的,即未被官方认可的祠祀形式,这些祠祀在统治者看来,或者涉及神异之事、荒诞之务,与伦理教化无益,与民生日用无关,这些行为都是“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礼记·曲礼下》),祭祀本身就是为了基于求福这样的目的,而淫祀则被认为是不能获得神灵赐福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宗教信仰行为是不能与信仰者的祈求联系在一起的,信仰者无法从淫祀中达到其信仰行为的目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既然是一种谄媚的行为、功利的行为,怎么可能由此而得益呢?从正祀和淫祀的区分来看,统治者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主张正祀,排斥、禁止淫祀,以确保统治的需要。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也有原本属于淫祀范畴内的祠祀,后来因被统治者所接纳而进入祀典的诸多例子。
不管正祀、淫祀的区分或者变化,这都表明了祠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力。任何的祠祀,所涉及的都是对于一定神灵的崇拜,而透过祠祀所透露出来的中国人所信仰的神灵,无疑也是非常庞杂的系统,就如同祠祀是非常普遍的一样,包括山林、川谷、丘陵、日月星辰在内的天地万物均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而受到信仰者的崇拜、祭祀。如果按照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排他性来说的,中国传统的信仰形式确实比较奇特,因为中国人信仰的神灵具有非常广泛的包容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不同神灵的具体信仰形式可以在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中融洽相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自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事实有关。传统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的基本需求是力图在被信仰者那里找到应对现实的动力或者利益,换而言之,透过对被信仰者的祭祀,希望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回报,即通常所谓的祈福。而所有的被信仰对象,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里都是具有这种赐福能力的,所以,信仰对象的广泛并不会在信仰的事实中形成冲突,相反,对于神灵广泛信仰,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为自己的信仰活动提供更大限度的利益,至少可以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从最简单的信仰行为来看,正是这种由于信仰的功利心理,使得在具体的宗教信仰活动中能表现出诸神和谐共处的事实场景。正是在这种多元共存的宗教信仰生态中,传统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得以真实地呈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