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在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横店。横店风景如画,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小村落——岩前村。村后有一座牛背山,高达百米,长数百米,因形似牛背而得名。在牛背山下出生的我,从小就跟牛打交道。牛是农民的宝贝,是农民耕田犁地的主要帮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时,我放牛上山。落日的余晖照着我放学的脚步,我返回山上,牛群静静地等待着。我领着它们穿过原野,沿着熟悉的小径缓缓行走,它们轻柔的叫声回荡在山谷,抚慰着我的心灵。 不上学时,当牛儿在山坡上自由漫步吃着草,我和儿时的伙伴们便在山间四处玩耍,争相爬上山楂树,比谁摘的果子多。口渴了,咬上一口新鲜摘下的山楂,顿时酸得一张稚嫩的脸皱成了一团,没过多久,一丝回甘缓缓升起,在嘴中游走。若是雨后初晴,一朵朵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蘑菇从泥土和枯木中冒出,采蘑菇成为应时的玩乐新项目,即便山路泥泞也阻拦不了我们上山的路。 当然,放牛的欢乐也会伴随着烦恼。偶尔,等我们玩尽兴了,回头找牛时,却发现几头牛失踪了。担心回家挨骂的我们心急如焚地边喊边找,有时发现牛跑到了山的另一侧;有时发现牛因为跑到人家地里吃庄稼而被人“扣留”等待赔偿;也有时牛真的不知去向,等到太阳下山、天色渐暗仍找不到。手足无措的我们只能抱头痛哭。 在无数个拂晓和黄昏中,我与牛儿同行在牛背山上。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身上,微风轻抚,那时,我时常仰望天空,无限遐思,总觉得山下深藏着宝藏。 小时候,我对考古的理解很浅薄,只当它是神奇的冒险。我常常借着洞穴和文物的故事,自诩为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带着牛群探幽解密,同时兼顾放牧任务。我幻想穿越丛林和草地,寻找古老的遗迹和埋藏的宝藏。 年岁渐长,我的梦想渐渐从儿时的幻想和冒险,变为少年追求真理和为世界做贡献的渴望。梦想激励着我努力学习,阅读大量书籍,不拘一格地拓展知识领域。 我很幸运,自青少年时期开始,就遇到了很多良师。 我高复班的班主任兼历史老师是毛纯良先生。鬓边白发生,常思少年时。如今我也逾花甲之年,回想起毛老师对我的关怀,心中依然充满感激,毛老师的谆谆教诲在耳畔回响不息,如同一串串珍贵的乐音。毛老师与其夫人程又新女士桃李天下,他们以知识、智慧和慈爱指引着我们茁壮成长。每每想到毛老师,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笑吟吟的脸庞。那时我正踯躅于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高考第一志愿虽填了经济类专业,但我的心中忐忑不安。我一直回味着毛老师的话,他曾恳切地对我说:“要坚持下去呀,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东西。”经济类专业是我热爱的吗?我并不确定。高考录取结果出炉,我竟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考古系。时光如水,奔流不息,我终于要踏上考古学的求知之路了。我渴望揭示历史的真相,将那些宝贵的遗产从泥土中带回人们的视野里。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我却如释重负,这或许是天意,命中注定我必然走上考古这条路。 步入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第一天,我满怀期待地走进那扇大门,它通往充满探索性的神秘领域。在考古系,我心无旁骛,专精一艺,整个心神都投入考古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中,古老的文明、埋藏的宝物,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故事,悄然呼唤着我。当历史的面纱被层层揭开,在我眼前,一个瑰丽而广阔的时空翩然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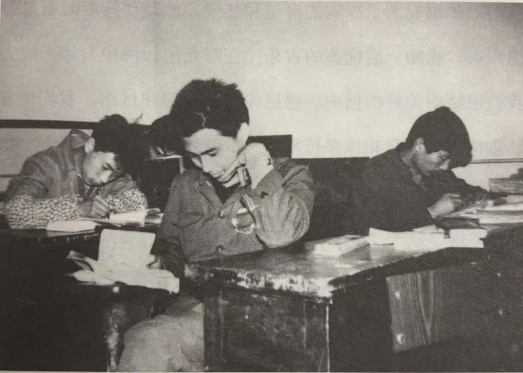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 课上,老师们对不同时代和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生动而细致入微的讲授。课下,老师们带领我们走向田野,用几十年丰富的经验手把手教我们实地调查和考古挖掘。在我眼中,考古学的世界是真实而立体的。在一次次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的实践中,我不断积累经验,那个当年想报考经济系赶热门的迷茫青年,已深深被考古学的魅力吸引,也在心中认定了要承担起考古工作的文化使命。 每一次挖掘都是一场历史寻梦之旅,每每与发掘出的古代陶瓷器、青铜器或其他器物邂逅,我都震撼不已。碰触着这些被尘封的文物,我仿佛穿越时光与古人相遇,感受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瑰宝,具有无穷的历史价值,是牵系着古今之人的情感纽带。 实践背后,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经过一次次震撼心灵的考古实践,我越发认识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指导实践中的作用,于是更加努力地深入研究。经过系统的考古课程学习,我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眼观六路,触类旁通,除了掌握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知识之外,还要广泛涉猎地质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文物的性质和年代。跨学科的综合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激发了我对各类古文化知识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求知之路不仅仅在于手中的课本和脚下的泥土,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各类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资源,也是汲取知识的宝库,每一次观瞻历史展品、翻阅古籍,都让我近距离体悟到历史的魅力。“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完成课业和实践之余,我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与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考古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这使我对考古各层面的学术知识有了更丰富的认知。 考古虽然充满魅力,却不是一条坦途,它有璀璨夺目的一面,也有灰头土脸的一面,尤其在面对重重难解谜题时,甚至会觉得分外孤独。幸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探索、学习,不断分享彼此的发现和思考。同学间携手并肩的合作与交流,倍添求知乐趣,让我无比兴奋。每个人的独特视角和创新思维,都会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那时,我们不仅要熟悉系统的中西方历史知识,还要学习与考古相关的地质、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因此考古专业的课业比其他专业更加繁重,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汗水。大学最初两年的理论学习,完全是分秒必争地刻苦努力。但要扎实地掌握考古技术,理论知识却只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考古终究是要“躬行”的。到了高年级,我们既要完成繁重的课业和学术研究,还要跟着老师们前往各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大量的体力劳动。在田野,在山林,在荒坡上,有我们躬身行走的身影;有我们手拿考古工具,测绘、勘探、挖掘的身影。夏天,顶着毒日汗流浃背;冬天蹲在寒风中,用小铲和竹签抠开比石头还硬的冻土。 
▲1983年,在山东长岛县大黑山岛考古实习时的合影 这种持续高强度的学习和实践,使我们磨炼出高超的技术能力与综合素质,我们学会了辨认土的颜色、质地,又学会了辨认遗迹、测量绘图、器物分类等的方法与诀窍。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样的强度都是一种巨大且痛苦的考验。一些同学身体和心理上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转了专业,寻找更合适的领域和发展方向。 就读考古专业的大部分是男生,但我们班竟有9个女生,实属难得。选择考古专业本就需要勇气,这些女生不仅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一点都不比男生少,更有女生的特殊优势——坚韧、灵敏和敏锐的观察力。面对各种实地考古和实习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她们不畏艰辛、乐观踏实,不断自我提升,展现了出色的学术和研究能力。她们对考古学的热情和执着,令我们男生备受鼓舞,更积极主动地投入考古学习与实践中去。 考古班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班风,离不开宿白先生的刻意培养。他夯实了我们的基本功,引导我们顺利入门,令我们受益终身。 那个年代一穷二白,即使是北京大学,教学设备也相当简朴,我们没有投影仪,更没有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遑论互联网,但这也造就了我们徒手画地图的技术。课堂上,每人都拿着一根铅笔,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先生将考古地图画在黑板上,我们则小心临摹,先生画一笔,我们就摹一笔,尽可能地将地理信息刻画得形象而准确。课堂上听不到交头接耳的讨论,只有一片铅笔画图的沙沙声。那时,课堂是一个奇妙的舞台,教师指挥,学生配合,如同在演奏完美的交响乐。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地图的每一条边缘、每一个标记都深深地刻印在了我们脑海里。每一次临摹都是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仿佛漫游在历史的长河中,身临其境地探索着那些古老而神秘的遗迹。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先生极有风度,尤钟情于折扇,常随身携带,唰地一甩,又倏地一合,过程行云流水似龙飞凤舞。每当他合拢扇子,背过身去写板书,讲台下的同学便争相模仿他甩动扇子的动作,彼此会心一笑。 先生的教导为我们开辟了宽广而坚实的学习之路,将我们的基本功打磨得如磐石般扎实。他的风度和教学方式也让我们对知识充满了探索的渴望和热爱。他舞动折扇时裂帛般的声音,犹如一曲优美的古乐,在时光的长河中奏响,成为我们记忆中美好的回响。感恩先生的教诲和付出,我们怀着敬意将他的智慧和风采传承下去,继续舞动着那把折扇,散播着知识和美好。 考古学赋予了我对历史在实物角度上的特殊认知和解读能力,我沉迷其中,深刻体验到时间的延绵与文明的传承。每一次发掘都像为历史寻回了一块块曾经缺失的拼图,在一次次的历史实物证据填补中,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而丰富的认识。这使我们能立足于世界考古学之林,鉴古知今。在众多的学科中,考古学是一颗璀璨而古老的明珠,它以独特的方式照亮了往昔人类的知识探索和文化积淀之路。感谢命运让我选择了如此独特的道路,有机会与古代文明对话,在历史的黄尘古道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