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深秋,一个秋阳高照的日子,杭州文史研究会的几位会员相聚在赤山埠一座农家小屋内。记得当时在座的有:时任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王利民、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倪素浓、文史委干部陈江明,以及楼毅生、陈志坚、吴志坚等多位文史学者,一共不超过10个人。笔者也有幸与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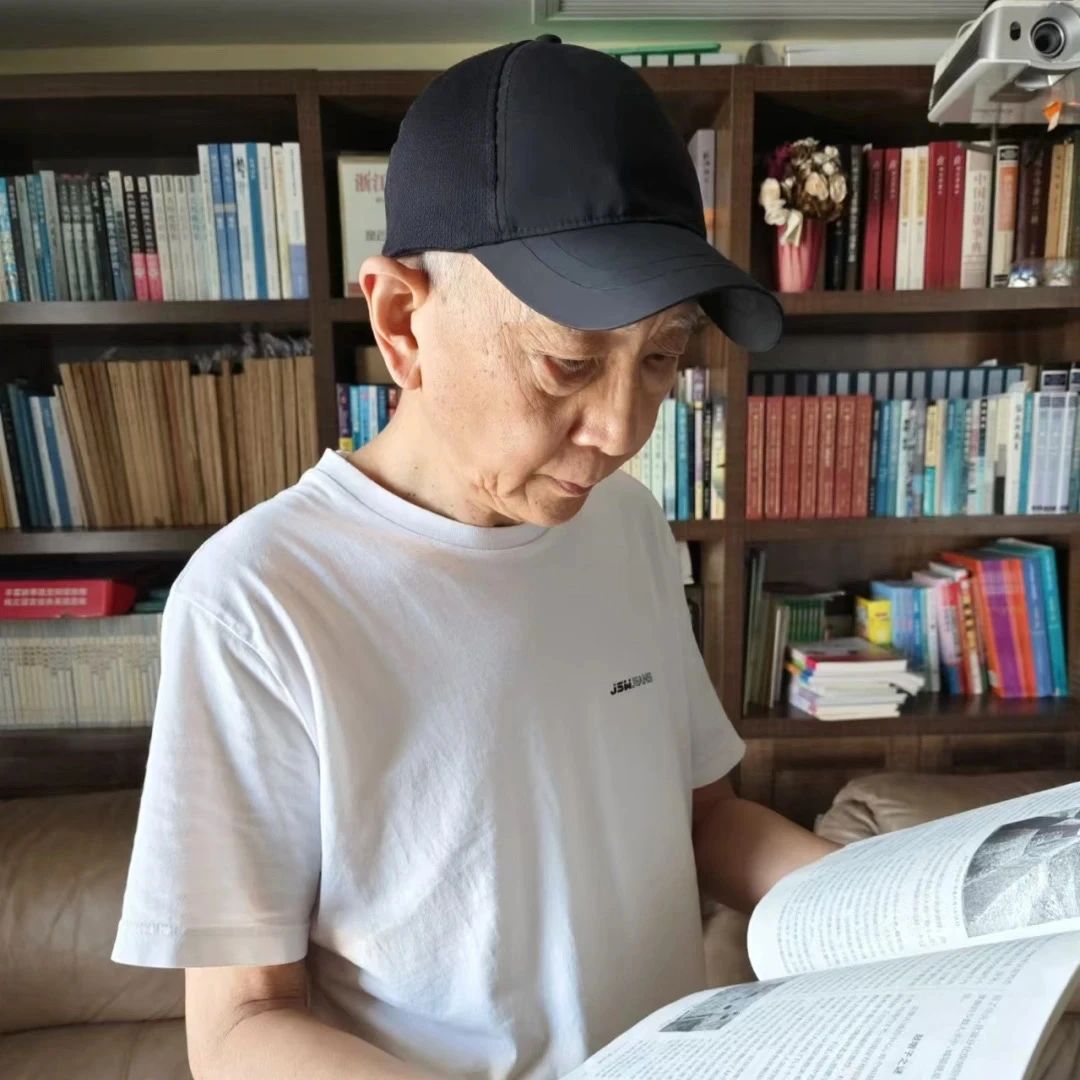
▲张学勤 早就盼望这样的平台 清茶一杯,聊天随意,围绕的话题则是王利民副主任的提议:创办一份介绍杭州文史的刊物。王利民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即杭州文史研究会秘书长,视野比较广阔,认为:杭州文史领域还缺少一个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碰撞各种学术观点的平台。 落座后,大家关心的一是资金,二是稿源。获悉可以由市政协文史委和杭州文史研究会共同来举办,话题就轻松了,毕竟,市政协文史委有专项的文史经费,杭州文史研究会则人才济济,不会缺撰稿之人。资金和稿源可能都不会成问题,加上政协文史委本身就有征集“三亲”史料的特长,所以,聚会的人无不认可这一提议,并初定一年出4期,为季刊,刊名“杭州文史”也无异议。 我在聚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早就盼望能有这样一份文史刊物。”这确是我的真心话!我的职业是专写新闻的记者,却老是喜欢写一些旧闻逸事,所以在职场经常会吃到闭门羹。 2002年5月,杭州武术界老前辈陈天申向我披露了一件往事:1931年,太极名师杨澄甫与南拳武师萧聘三,在浙江国术馆内,因小事引发动武,最终两人都因身受重击不久人世。由于此事属首次披露,我撰写了一则近4000字的文史稿件,发给了我所在的报社,经部主任、分管副总编审阅后,稿件顺利排版,出现在本报的毛样上。当天傍晚却传来消息,稿件被撤了。询问原因,知情者只是笑笑,不作回答。 随后,我联系了一家都市报,该报副总编看了稿件后,反复追问本报不用的原因。我只得如实告知“不知道啊”。该报因此也不敢用了。最后,这件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历史秘事,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首次披露。当年6月25日的《羊城晚报》全文发表了我写的《浙江国术馆,尘封一秘密》。 还有一篇文章也使我耿耿于怀。2013年11月,我根据史料撰写了一则《杨乃武出狱后又被劳教》的文章,但是,在杭州找不到发表平台,最后,这桩同样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历史要事,是在邻省安徽的《江淮文史》(2014年第1期)上公开发表的。 所以,结合自己的这些经历,我是大力赞成创办一份有关杭州文史的刊物,并表示自己会积极参与。 当了9年的第一读者 但是,真正动手创办一份刊物,可不是轻松之事啊!没有专职人员,从主编到编辑,从约稿、审稿、改稿,每件事都是市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兼职干的。直到 2014年底,《杭州文史》第一辑才露出整体模样,正式出版已经进入2015年,整整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出了这第一本!我没有参与第一辑的采编工作,只提供了一篇采访稿(访包伟民教授)。 第一辑还没有问世,第二辑组稿工作就已开始。我在查阅民国时期汪日章亲笔日记的基础上,匆匆撰成《汪日章缘何没当上贵阳市长》一文,递交了上去。 这年端午节前一日(6月19日),我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完全不了解第二辑的成书进程。直到2015年12月,第二辑《杭州文史》才印了出来,即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出了一本。 原计划一年出4期,结果两年多时间只出了2期。第三辑问世已是2016年8月。出版社的同志不知道内情,见封面上印着“2015年第三辑”字样,还以为出了编校差错。 第三辑还没有问世,《杭州文史》主编王利民,副主编倪素浓,便来邀请我参与《杭州文史》的编务工作。当时,我因心梗猝死,虽抢救及时,捡回一命,但仍三日两头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此时的我,正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听闻两位还要来请我参与工作,无意中给了我莫名的信心。 从第四辑开始,我的姓名便出现在副主编一栏中,其实只是担任《杭州文史》的前道阅稿编辑,从而有幸成为该刊物整整9年(2016-2024)的“第一读者”。从第4辑到第38辑,几乎每一辑文章,我都细细阅看,既拓展了眼界,也获取了新知,有许多文章真是过目难忘!如:敦煌出土元代杭州崔家巷金铺的广告、八卦田中心圆点是清朝一位部长的陵墓、《钱唐记》作者究竟是“刘道真”还是“刘真道”、“西湖”与“藕粉”的奇妙对接、美国船王大来运来28根巨型美洲红松建造灵隐寺、纸上寻访台湾女作家琦君在杭州的洋楼故居、林纾在西湖补柳,以及船型馆落户梅东高桥旁的曲折故事,等等。 相信《杭州文史》的众多读者,也会和我一样,在阅看这些文章时,一定会对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增进更多的了解,升腾更多的敬意。 步履蹒跚的时效性 我接手《杭州文史》第4辑阅稿工作,已是2016年6月,组稿、阅稿,忙活5个多月,第4辑终于在当年11月问世了。也就是原本计划在2015年出版的四期刊物,竟用了约三年时间,直到2016年底才完成。 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刊物的时效性特别看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很难想象会有人去阅看标注着上一年日期的“旧刊物”。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着力的一个方向,就是推进《杭州文史》的出版进程。 在2017年5月前,我们抓紧将2016年的四期刊物(第5至第8辑)全部出版了。还出版了2017年的第一期刊物(第9辑)。此后,我们基本保持着每年出版三期,而每年的第四期则争取在旧历新年前完成。 为什么在一年之中总是不能将四期刊物全部出齐呢?出版进程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在稿源。 在当今这个功利性颇浓的社会环境里,高校师生、社科学者都须面对各自的业绩考核,有好的文章,自然要送往能被考核制度认可的刊物。这是个人升级升等的必然选择。我们这本不被认可的小书,自然会遇到难题。 此外,我们刊物名称是“杭州文史”,用稿内容一般不会越出杭州地区,这就使组稿、阅稿更受限制。 然而,《杭州文史》上自主编,下至编辑,高举政协“团结、民主”两大旗帜,搭建文史论坛大平台,创设文史研究课题,吸引全国各地的文史学者来杭与会,共同探究杭州的历史,品味杭州的文化,从而为《杭州文史》提供了不少名家的大作。如:中国社科院楼劲研究员的《杭州成为东南都会的若干历史背景》、厦门大学王荣国教授的《杭州龙华灵照禅师弘法历程考》、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的《漫谈中国传统的真实观:以宋代为例》、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的《杭州成为东方巴黎并非遥远的梦想》、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游于艺”:宋代士人圈与“雅俗”观》、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的《宋朝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的《思想家眼中的历史》、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教授的《南宋宗室的人口、管理与教育》、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的《全球史视野中的“大元史”和“新清史”》、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的《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的《沪杭铁路百年回眸》、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的《清代以来杭州在徽商江南慈善网络化建设中的作用》,等等。 这些名家大作,大大提升了我们这本小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最初,我们只能主动出击,组稿约稿;到现在,我们开设的约稿邮箱已开始不断收到自发来稿,有的稿件质量还相当不错。十年,《杭州文史》这株幼苗已展现出勃勃生机,我也随《杭州文史》的成长,结识了不少朋友,汲取了不少知识。 随着第40辑的问世,《杭州文史》的第一个十年将划上句号,同时,也开启了它的第二个十年。今天,任该刊采编的人员已由兼职者,晋级至专职者,刊物也由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刊,增扩为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刊。相信在第二个十年中,《杭州文史》一定能够进一步提升时效性(一年内能出齐四期),也一定会奉献更多精彩的华章,真正成为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的一张靓丽名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