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回(1227~1307),是宋末元初有名的官僚、诗人、文学评论家。围绕着他在南宋知严州任上投降元军一事,自元代至清代遭到了无数文人诟病,以其不忠于宋,人品极差诋之。而现代学者针对其晚年寓居杭州的生活境况及人品问题,特别是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方回》条对他近似诋毁的记载,可谓“辨了又辨”。仅我所见就有四家。前人多以这些同辈或晚辈诗友之间的唱和之作以及后人对方回的追记来辨证周密所载“市井小人求之序……序还索钱,以致挥拳”之事等语涉诋毁,多集中证明曾为贾似道门客的周密为故主辩护,故大肆攻击与贾有仇的方回。对于周密记载中“仇远贺诗忤方回”一事,以往学者多以仇远、方回诗词酬唱的亲密关系,以及仇远的悼念来反证他二人不会以此结怨。也有人指出,在无法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其事的真伪之时,这场风波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误会与随意调侃,风波的化解也是出于政治利害上的考虑,而不是简单的感情的平复。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从一首诸学者频繁引用却未得确解的诗歌史料入手,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宋元之际的历史背景,再探对于方回差若天渊的记载背后的历史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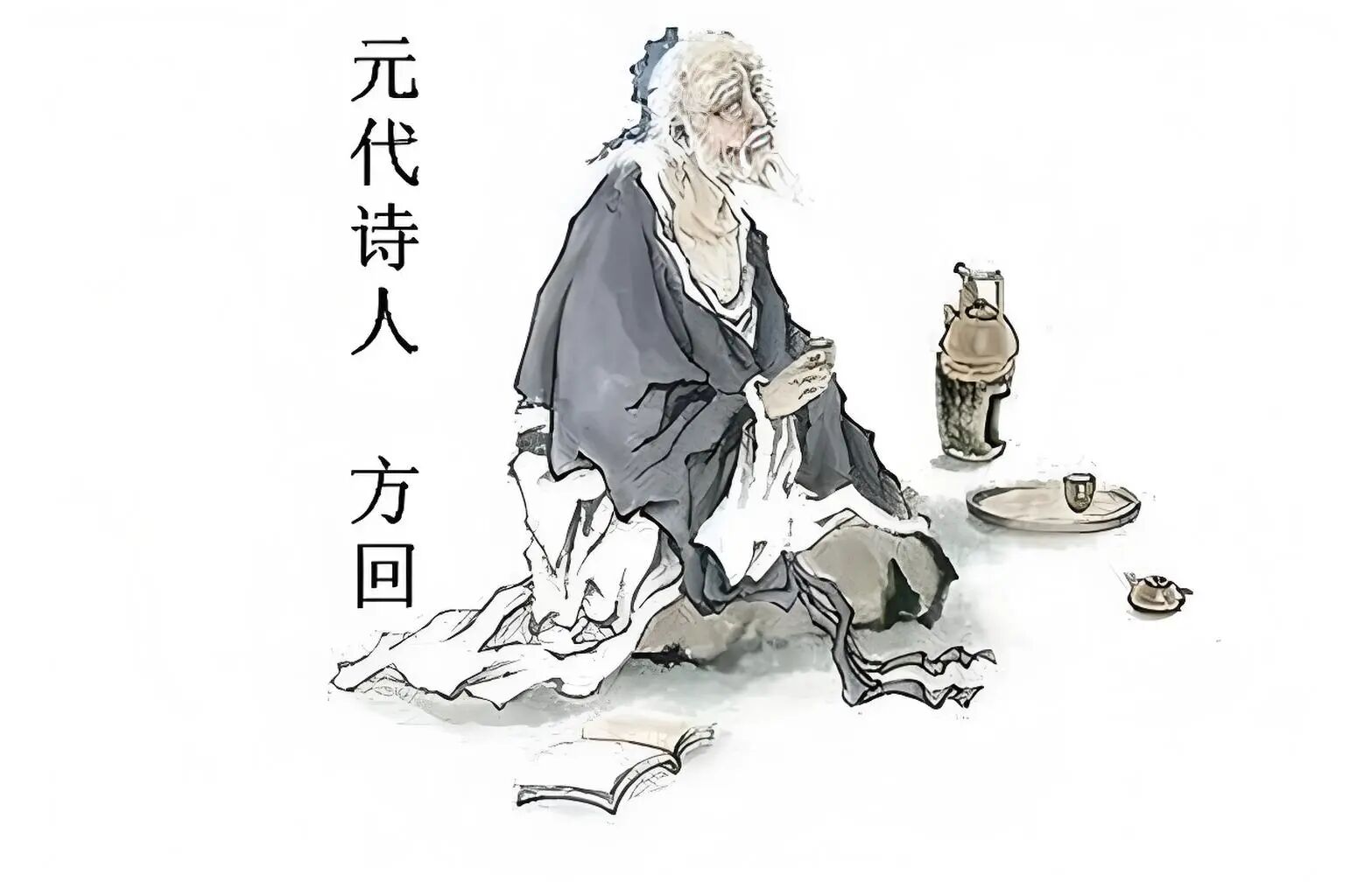
▲方回 壹 学者考证方回晚年在杭州的交往及身后之名时,常引仇仁近《怀方严州》一诗: 八十一年前,科名已褎然。依刘王粲檄,入洛贺循船。受禅碑谁上,闲情赋自传。江山英气歇,堪恨亦堪怜。 八十一年终,堪嗟旅榇穷。胸中元耿耿,身外竟空空。白首太元草,紫阳虚谷翁。平生有遗恨,五马未乘骢。 八十一年亡,哀哉老紫阳。佳儿方戒道,小妾漫专房。每忆先生被,常怀太守章。桐江诗万首,端可及龟堂。 八十一年身,栖迟客馆贫。登门曾有我,铭墓竟何人。醉梦髙楼月,悲歌故国春。可能函玉骨,归葬练溪滨。 八十一年休,云何不首邱。岂无商女恨,肯作贾胡留。书籍从人卖,田园有子收。乌聊山在望,风雪去悠悠。 学者引用此诗,并以方回与仇远六十多首诗歌唱和为证据,证明二人交往甚深,仇心中甚是推崇方回。诸家所论俱如此。但我们再看清人卢文弨在《仇山村金渊集书后》一文中的记载: 五言律中有《哀方严州》五首,严州乃方虚谷也。诗中具有微词。虚谷之为人,即不至如周公谨所诋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较然也。今本乃题为《怀方严州》,详诗意,当作于其新殁之日,非怀之也。 卢抱经校勘大家,其在清代所见的版本为《哀方严州》可作为一异文存在,以二字易讹写故。虽诗无达诂,但此一异文出,全诗背景与取向为之一变。然而,前人多不对此加以关注。即使有关注者多断章取义,以第四首证明仇远的哀痛之情。更有甚者,引用卢文,截断其异文之说,并提出不能看出卢言“微词”的说法,有隐去于己不利之证据的嫌疑。今首先将五首诗进行整体观察,概括其大意: 诗中言“登门曾有我,铭墓竟何人”之语,指方回身后之事寂寞凄凉,卢言作于新亡之时,亦无不可。然第一首言其政治境遇,以王粲、贺循典故暗指热衷权谋者与身居高位而思退者两种人。其列举这两种人身居高位时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作者对方回早年上书贾似道(王粲檄),后投降新朝(镌刻着汉、魏嬗替的受禅碑已不知何人所作,唯有渊明闲情之赋流传至今)的感慨。第二首,“白首太元草”,用杨雄退而草太玄之典,寓方回因政治失意,退而著诗之意。“平生有遗恨,五马未乘骢”,五马乘骢,指就地方郡守之职。方回建德路总管罢任,或因蒙古统治者设达鲁花赤管理地方,抑制汉人权力而罢任。此诗意为方回功名之心未泯,但身前寂寞。第三首最为复杂,整首诗情感不一。“佳儿”句暗指方回之子方存心入燕一事,方回曾经向亲朋挪借川资。然小妾一句与周密所言小婢半细事有暗合,此二句连缀,深具讽刺意味,与公谨所讥“假道学”之人相近。然而,后一句却抒发了方回对其照顾的深切感触,前人多以最后一联“端可及龟堂”联合,证明他将方回与陆游相提并论,彰显其诗才。殊不知方回实常以陆放翁自比,但气节难及,第二首末句已经辩证。最后一联以“端”发语,也可以理解为反问句。这后两句也可作如此理解:我每当回忆起先生的恩惠,总想到严州太守的官样文章,方回诗歌纵有万首,难及陆游之气节。毕竟,仇远强烈的隐士情绪也会带到他对方回积极出仕(五马未成骢)问题的认识上。最后一首言其殁于杭州,未能终老他乡。合于周密载其寓居杭州不归。“商女”“贾胡”二语,以不归家暗喻其留恋新朝,寓批评之意。 整体观察此诗,仇远诗中运用典故,所要表达的是对逝者方回出仕元朝的否定意味,以及作为影响较大的诗人身后寂寞的慨叹。我们颇能从这首“哀辞”中的某些字句看出仇远对前辈诗人的复杂态度,尽管仇远对方回之死也有些兔死狐悲的情感。是时方回已死。有道是死者为大,前辈逝者似已进入历史,固然不能苛责之,然而我们或也不能苛责后人贯注以己意的感慨。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方回降元问题也是仇远心中难以回避的阴影,而这首被我们引用数次的诗却成为了重要旁证! 方回仕元,是前人探讨此问题时的关键节点。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观察与其同寿的牟巘此时的状态。宋元之际,大多数士人对待仕元,并非像个别遗民那样激烈,学界已有讨论。况且此时的牟氏年已七十,我们从他的记载中,也略可窥探至元末期他对方回那一段“不光彩”往事的态度: 余病卧对墙壁,平生结习扫除略尽。每闻人谈旧章故实,往往面热汗下,巳为椎鲁木僵人。周公谨忽以《齐东野语》示余,岂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谨生长见闻,博识强记,诵之牍,存于箧,以为是编。所资取者众矣。其言近代事特详,盖有余之所未闻,或闻而不尽同者。乃自托于野。何居?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与其史也宁野,野固非所病也…… 牟氏在六十四岁时的记载至少暗示了一个事实:虽然其父牟子才在有宋一代位居宰辅,然而对宋季史事的了解总是有限。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问题他或记忆有误,或者根本说不清楚。时过境迁,很多关乎士人名节,忠奸善恶的大事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见,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牟氏这样的垂老之人,并不专心纠缠在纷繁复杂的往事之中。对方回的失节,牟氏的文字中竟没有只言片字加以谴责之,尽是些场面之作。而仇远作为与之相差近三十岁的年轻人,对往事更谈不到亲历,咏叹方回降元之事,或是因为仇远本人以遗民自居,故所持有遗民的价值观念使然。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对仇远对方回的真实态度大体上是揣测。但是,方回在七十大寿之时,如何一句“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就让他如此震怒,以至于要做出借刀杀人的极端行为? 不得不承认,相较晚辈赵孟頫,方回背负的历史包袱较大。故在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理学思维下,其不能不对类似牟巘的道德裹挟产生种种不舒服的表现。但是,让我们来看如下记载: 陵阳牟先生自还会稽,使者节食贫茹辛,卧苕溪上二十余年。夫人同郡邓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贰卿秀岩李先生之外孙,家世轩冕。忘其贵奢,相与隐约,产息烦衍,更衣而燠,并釡而饱。清风苦节,与陶渊明家伉俪,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贤而叹其约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长子,余同年弟成甫帅诸弟大设醴私第,为二亲寿。二亲燕而乐之,游从朋客甥孙。中外闻而为诗,以歌吟颂美者累十百人。 我们从现存的方回诗歌中,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人在他的七十大寿时为其颂寿,也不知道其七十岁寿辰时的情景。然而,我们检核《桐江续集》卷二十二《七十翁吟五言古体十首》其四云: 五男三女儿,侥幸肖吾祖。贤愚挂怀抱,笑陶敢效杜。长男近寄书,长女化为土。嗟予七十翁,哭此四十女。此女抱恨久,嫁不得其所。厥夫实鸱鸮,厥舅乃狼虎。谰讼欲杀予,破家谢官府。不禁毁璧痛,何啻茹荼苦。 长子方存心不在身旁,长女被亲家程氏折磨致死。七十老翁经历人间悲剧,其承受能力再强,却也难掩心中的失落。是年,方回与牟巘曾经因为牟氏来杭州纳女婿,曾有一面之缘,是时恰逢方回七十寿辰。二人有酬答之作传世。可以想见,在聚会中,方氏至少了解牟氏晚年的幸福生活和其子牟应龙(成甫)的孝顺。甚至我们能够想见二人寿宴排场的极大落差——尽管也有不少名士如仇远辈为方回祝寿,但家贫,儿孙远离都让他在和同为士林之望的牟氏的比较中显得气短。甚至,其老年时对婢女的感情,或可认作他晚年悲凉心态的发泄。故在一般道德的规范下,“老尚留樊素”一句所指,恰是蓄婢妾这种涉及阴私之事,而“贫休比范丹”无疑是巨大的精神刺激。更何况,“佳儿方戒道,小妾漫专房”二句恰能作为仇远以范丹讽刺方回的重要内证! 因此,“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恰恰是仇远真实想法的流露,他写出之后怕也并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轻易地得罪了如此状态的方回。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生活的窘困使得他最终选择了和方回相同的道路。 贰 我们知道,方回在至元二十二年,于杭州三桥小楼赋闲。至元二十三年,他并未被程钜夫征辟。这当然是由于其曾降元的经历和其年老使然。故其一直过着“英俊沉下僚”的生活。此时的杭州,作为未遭损坏的亡宋都城,仍旧留有旧日“首善之区”的遗韵,仍是文人雅集的交往之所。但是,文人的境遇却不比纸醉金迷的宋季。他们面临着元初士人共同的根本问题——生存。在科举中止的元代,读书人靠正常仕进,以俸禄供养的谋生之路被堵死。况且,地方战乱留下的巨大创伤导致了大量文人涌入杭州避难,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中一些人因为仕宦而离乡背井,从此和故土分离的现象。这导致了士人的财产并无租佃之税加以保障,即使有,却也在战乱的条件下无法保全。 “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这时的杭州有如一个避难和集会的场所。在士人无法成为大地主,亦无法做官谋生时,大家会抓住每一个北方诗人来到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宣传自己的诗文之名。生活在做官讲求“根脚”的元代,若想出仕,怕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戴表元竟无数次奔走于此,参加各种集会以达到其目的。参加集会的北方诗人数量也不胜枚举,有名者如赵孟頫、鲜于枢、高克恭等人。若我们相信周密的话,或许还有那位奔走权门的盲诗人侯克中。 可见文人们的“交往”也通常是有限度的,互赠诗文的行为,或许可以证实他们之间交往群体的存在,但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结论:在交际圈中的应酬之作也能作为二人感情深厚的例证。这样做或许只是表面上的亲密,情非得已的行为,或者通过这种行为体现出某种功能性——对于“江南文人”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这尤其是在元廷为官的赵孟頫辈所需要的——他自身代表的,是来自北方的新政治势力,他既要保持自身对南方士人的政治威慑力,又不能不在原有的圈子里找到其身份认同。——这既有统治者实践其文化政策的需要,又有统治者视其为方技之士,倡优畜之所引发的强烈失落感。或许元廷希望通过如此方式达到对江南士人的间接控制,但或许,对交税就是好人的蒙古统治者来讲,这些恐怕也是那些汉人儒士的“教导”吧。 对于方回来说,这毕竟是新朝,无论是谁,无论是否在本朝出仕为官,只要名望较大,就不得不在这个敏感的时期标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侯克中的介入,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侯氏倾向为仇远说话,聪明如方万里,也不可能不知道得罪他们这些和北方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吧!在这之后,方回仍然答应了仇远捐屋赀的请求,但如果二人结怨事为真,那么,他怕是亦有不愿意得罪隐性的政治压力的隐衷。毕竟,前人多言方回晚年的穷困潦倒,既如此,为什么他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一幅周济后学的嘴脸呢?再看大德四年,方回送其长子方存心至北方求官的情况: 中全一日过余而别曰:“存心今者行仕矣!”问何以行,何以仕。曰:“吾亲之名,之贫,之久不仕,自中外诸贵僚举知而怜之。于法,上大夫得谢任,子许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予之。吾庶几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荐,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愿焉而不得者也。” 这固然是为了家庭的未来考虑,且其家财基本已经散尽。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曾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他,心里断然不会忽略现实的政治压力。送下一代求官,或许也是隐性的效忠。甚至我们可以推测,他所发起的诗人雅集,更有传播其老来贫贱不仕的名声,特别是给那些可能会为自己的儿子谒官提供方便的人以一个必要的信号!毕竟他在前朝并非草民一个,他的周围也不是没有像牟巘、仇远之类的不仕之辈,只是从二人晚年的境遇上来看,牟巘最终选择了和儿子砥砺名节,也有家财尚可,不需仕进的因素——至少牟氏七十岁时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为仇远《山村图》题词的,也有“深诋方回”的周密!我们不得不说,求屋赀及随之而来的那些甜如蜜糖的诗歌酬唱,并不能证明方回内心真正原谅了仇远,而恰能从反面说明来自北方的政治重压下,方回这条老狐狸做出了无奈而正确的选择。而使得他们倍感压力的,不仅仅是暴虐的“北客”,更有“遗民不过二代”下新一代士人对南北混一新秩序的认同。 叁 综上,从方回晚年的境况中,我们看出它与周密的记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也表明周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然而,宋元之际的史料显示,周密与方回二人并无交往。学界所推测的周密和方回之间的矛盾的根源,无外乎两点,第一点就是前揭詹杭伦说其诗学观念的差异,第二点是周密曾经做过贾似道的门客受其恩惠,而方回曾经上书攻击贾似道,周密因故诋毁方回。我们不妨追溯到宋末——让我们姑且相信周密曾做过贾似道的门客,这是宋季士人奔走权门的典型案例,即所谓“奔竞之风”。但前人没有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科举制下产生的一批未能做官的读书人,其生存需要依靠大官僚或权臣,这实在无可厚非。晚宋兴起的“江湖诗人”这一群体大多属于没有,或在官僚集团边缘的读书人。我们莫要忘了,“江湖诗案”这针对这一群体的文字狱正是有赖于方回的详细记载,才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之中。而宋末兴起的民间版刻之风,也让统治者警觉江湖诗人的政治影响力,及对诗歌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尽管方回在统治集团内部对他们的行为和诗格颇多批评,但他事实上也不能免俗。我们大可推测,方回作为进士,却沉居下僚,未如没有功名的江湖诗人一般干谒奔竞,但他毕竟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他的父亲也给他打下了良好的仕进基础。对于高层政治,“禁民间作诗”只是阴谋论下的必要手段——或许文体的背后是他们的串联,而禁绝之也是一种对他们之间交往集会造成的政治影响力的否定,甚至同是文人群体,或许价值观相同,但方回或是通过对江湖诗人“不学”的讥讽,以显示他们和那群附庸风雅的书商,以及和书商有密切关系的人深刻的边界。但这种边界又是模糊的,毕竟他不能对诗歌创作和版刻活动免俗。 因故诗歌流派以及审美标准的差异,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士人群体的分化。而上述这种分化,则造成了周密与方回之间真正的鸿沟。视野及此,则他二人是否相识,周密主观上是否有为贾似道诋毁方回的成分,都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