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安惟善堂与杭州地方社会 惟善堂作为杭州地方的商人善后组织,施善行义的行为得到官府的肯定和褒奖,但其又不同于杭州众多的慈善公益组织,它救助施济的对象只限于徽州六邑的徽人,而且一般是贫困无依的徽商,虽不像徽商木业公所那样与地方民众有复杂的利益纠纷,但是惟善堂作为徽籍商人自助的善后组织与地方社会仍存在诸多矛盾纠葛,也要处理各种问题,在此方面惟善堂也是积极向官方寻求帮助以解困扰。 (一)积极寻求官方认可与保护 新安惟善堂在建立之初便屡次向地方官府请命,初衷是防止地方刁恶势力的侵扰,使作为外籍商人自筹的同乡互助善后设施亦能获得当地官方的认可,赋予其合法性,得到官方权威的保护。 1. 努力获得官方认可 清代中后期,杭州地区的善会、善堂组织数量可观。据夫马进的研究,可将杭州的慈善组织分为三种:一是由杭州善举联合体统辖管理下的官方色彩明显的大型善会、善堂;二是以杭州一般居民为对象的小规模善会、善堂;三是各种以同乡组织为基础的为同乡人服务的善会、善堂。前两者都主要以杭州本地人为领导者,是为本地居民服务的组织,经费主要来源于官方,受官方管制,俨然是国家事业的延伸,其合法性及权威性不容置疑。而新安惟善堂作为徽籍商人自发在杭州组建的善后设施,其经营管理和经费皆由徽商自行掌管,是一个完全自发组建的地域商人善后互助组织,所以善堂想要获得基本的保护和长久的发展,就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首先,新安惟善堂在堂中章程和规条的制定刊布上,往往主动将所拟内容先行呈送官方鉴定,请求府县察核定夺,才最终采用。如道光十八年,惟善堂出于“第思有基勿坏,不得不慎之于始,是以拟定章程,敬求察核施行,以全善举,永垂不朽”之由,“谨拟惟善堂章程恭呈宪鉴是否有当,伏候批示遵行”。细查章程和规条内容,其中对于路费工价及应对当地民众强占厝所等都有详细规定,而杭州官方也积极回应,称赞善堂章程、规条“曲体人情,悉臻妥善”,“周至无遗”,准许施行。杭州府正批示曰“惟善堂各条章程甚为妥善,洵属好义可嘉”,并给出建议,告诫惟善堂“惟捐资发商生息,必择其殷实可靠者,方免日久侵挪,以全善终而垂久远”,督促善堂司事要善始善终,协力共襄善举。实际上,新安惟善堂作为外籍商人的互助善后组织,堂中章程和规条的制定本属堂中私事,但是善堂董事积极将其呈送官方审核鉴定,获得官方允可,实际上是要求官方对其章程、规条赋予合法性的认可,给以法令的保护,一旦有人威胁善堂运营或破坏章程、规条,可以从法令上及时获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当地官府也乐见其成,赋予惟善堂合法性,形式上监管善堂,善堂便能自行经营善举,无形中减轻了地方政府救济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惟善堂请求官方对于捐助者和善堂有功主事者予以褒奖。善堂章程中规定,“一千两以上者,报县请奖,三百千以上者,禀府申详”。在实际运行中,标准又大为放宽,捐款者在一百两以上及五百两以下者亦“量加鼓舞”,给以奖励,官府应允。如道光十八年(1838),杭州府和杭嘉湖道分别颁给惟善堂及六邑义所众司事和善捐者匾额以示褒奖。诸如“成式可循、谊笃桑梓、敦善无倦、从善如登”等褒语,给众司事和善捐者莫大荣誉和精神鼓舞,官方的支持与导向使得众商捐助更为踊跃,善堂司事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2. 积极寻求官方法令的保护 面对矛盾和纠纷,惟善堂利用群体的力量向官方请求法令保护,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首先,防止地方地匪、无赖无端寻衅,阻挠善事。如道光十八年五月,惟善堂开工兴建大厅与厝所,怕当地刁恶势力阻扰,董事众人联名上书寻求官方立法的保护:“现当开工之际,地隣山僻,仍恐地匪无知窃取物料,土工匠作分坊把持,阻挠善举,种种窒碍,有妨善政,应请台大人钧批,行知仁钱二县出示晓谕,严行禁止,实为公便不朽。”杭州府宪台批复:“札饬仁钱二县一体严禁,可也。”仁钱二县据此会同出示晓谕:“自示之后,如有匪徒在新建惟善堂所乘间窃取物料及匠工把持阻挠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严拿究治,决不姑宽,均各凛遵勿违。” 同治七年(1868)、八年,惟善堂兴建施茶亭和厅房时也及时向官方请命立法,寻求保护,以免地方势力的滋扰,获得官府支持。 其次,防止抬工、脚夫等分段把持、勒索抬价,增加善堂负担。善堂多次重申常定抬工费或水脚费,官府勒石明示众人知晓,“不准额外刁难勒掯,一经堂董具禀,定即提案,从严究办,决不宽贷,各宜凛遵勿违”。咸丰二年(1852),湖州府德清县监生江秋水在塘栖镇建立怀仁堂义所作为惟善堂分所,“因地滨临大河,船只来往,每有地匪把持,哄抬勒索,埠规稍不遂意,抛掷砖石,损坏墙垣,借端滋扰,有妨善举”。针对此种恶况,新安惟善堂诸司事禀告杭嘉湖道官员,要求官方介入,严惩滋扰之徒,官府积极回应,严令地保及当地居民不得妨碍义所善事,对不法棍徒严行究治,妥善解除义所困局。 最后,禁止当地民众私自停厝于善堂,致使厝所挤压,影响正常运营。善堂董事曾向官府反映新安惟善堂“专为新安六县旅榇暂停而设,现已定有章程。每于春秋二季载送还乡,催令棺属认明领葬以安泉壤,庶无积累之虞,乃有近地居民强将棺木存放以图就便,并省租钱,甚至廿余年因循不葬”,所以善堂诸董事禀告县令,得政府严令催葬。当时有60多具棺木抬葬于外,还有40余具无人领葬由掩埋局代为埋葬在公地。同时,惟善堂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侵占善堂的土地公产,每每购置土地或得人捐地助产,务必向官方立案,完报各种地契、税粮,以确保土地的合法性和所属权。 清代杭州的商人遭遇到的最大打击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战火影响。劫后重建往往是同乡籍人重新振作的体现。身在杭州的徽商表现尤为突出,这与倡导者、组织者均有一定关系,“夫仁人孝子之用心,惟行乎心之所安而已。权厝所之有举莫废而死者安,死者安而其一家之人安,家积成邑,邑积成郡,而一邑一郡之胥安。茔之事一人任之,或数人任之,前之人任之,后之人复任之,纲举目张,无侵无旷,亦各安其所安,则心安而事无不安。持此以德,隆千百年不敝可也”。 纵观征信录中记录的善堂董事与各级政府间的文献对话,惟善堂的主要目的:一是积极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主动将自身一举一动备案官方,以获得其认可为行事前提;二是及时寻求官方的保护,依靠政府权威防止地方刁恶势力滋扰,在与地方势力的矛盾纠纷中占据上风,维护自身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善堂的经营发展,顺利从事善后事宜,也打击了地方的刁恶势力,利于地方社会的秩序稳定。 (二)惟善堂与杭州地方的慈善事业 清代杭州地区各种各样的善会、善堂不断建立,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战祸造成生灵涂炭,尸殍遍野,政府督促、鼓励各种义葬,江南地区更是形成了义葬的高潮,许多诸如新安惟善堂类的善堂积极重建。官方屡次以法令的形式督劝地方积极丧葬,同治六年(1867)御史刘秉厚上奏指出:“被扰地方尸骸未经掩埋,及向来浮厝棺木,并着该地方官广为晓谕,速行埋葬,免致暴露。各该地方官皆当实力奉行,用广皇仁而资感召。”并规范相关事宜,要求各善堂做好收埋工作,规定抬夫工钱,严禁把持勒索行径。新安惟善堂无论是建立之初还是战后重建都积极谋求官府的认可与保护,无形中配合着官方的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依赖性和谦卑。但从实际来看,这种依赖也只限于法令制度上的合法性赋予和保护,善堂在日常的运营管理上自成体系,特别是对善堂类慈善组织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方面,没有官方的拨款,都是由徽州商人自愿捐助累积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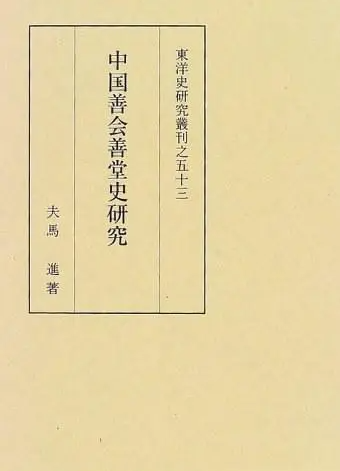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而根据夫马进的研究,在清代后期杭州地区诸如普济堂、同善堂和育婴会等主要的慈善组织,基本上是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他称之为“杭州慈善联合体”,由杭州本地的绅士进行管理,这些善堂绅士大多具有一定的功名和官职。杭州慈善联合体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密切,这不仅表现在联合体管理下各善堂的资金主要依赖业捐,而且善举组织经常会受到来自官方的强力指导和监督,杭州慈善联合体的收支状况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必须向地方官汇报并接受审核。这最终导致一旦善堂资金出现不足,在向官方求助不得的情况下,善堂总董只能自掏腰包,而且经费不足是常态,所以杭州这些善堂所开展的慈善事业带有明显的徭役性质,最主要的是资金不足造成的困境。当时杭州城内诸如山东、安徽和湖南等会馆及同乡会类的慈善组织并未包括在杭州慈善联合体下,与之不存在任何关系,新安惟善堂就是其中之一。新安惟善堂是为徽籍贫苦人士暂时安置亲族友人灵柩,等待归葬故里的设施,是专门为同乡人设置的善堂,也只对同乡人提供善后服务,其资金来自于民间的自愿捐助,完全独立于杭州慈善联合体,所以官方的直接介入很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使得善堂能够最大空间地自由灵活运营,同时官方也乐见徽籍人士能自行妥善处理助葬等事,以稳定社会秩序,所以对其主张予以肯定,对其要求予以应答,给予法令制度的保障和精神层面的嘉奖。 新安惟善堂之所以能服务徽州六邑,维持善堂的正常运营,最主要的是基于经费来源的稳定充足,得益于善堂绅董和司事的用心经营和善堂章程、规条的完善得当及官方的从旁协助。从更深的角度分析,杭州各种商捐能募集成功,完全是奠基于清后期徽商在杭地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正是徽人商业的兴盛,才能保证善堂这个同乡互助组织得以经历时间和战火的考验,良好持续发展下去。徽商个人和各业的积极捐助是基于地缘和血缘纽带的伦理道德情愫,正如倡起者所言,出发点和目的是敦谊乡梓,基本没有功利性。惟善堂的各种活动对于旅外经商和谋生的徽人来说,免了身后之忧,能团结乡谊,也为江浙经商的徽人提供了心灵上的归宿和慰藉。惟善堂虽对政府有依赖,但更多体现的是独立运营,以众帮众的自救自助。新安惟善堂通过建立良好的善后设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准则,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徽商在杭州建立的木商公所等亦具有枢纽作用,形成了多层次的徽商交往、交流与交融网络,既为徽商自我营造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亦在繁荣以杭州为中心辐射更广大的江南经济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