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这部分我们将分析一些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研究渊源,便于更清楚作者观点的来龙去脉,也将会把笔者阅读中不解之处提出来。 上篇讨论唐帝国后期政治问题,虽然只有两篇重要文章,却分别涉及了两大重要问题:藩镇和宦官。其结论也是与一般史学界的认识差异颇大。《西川》一文讨论的问题相对较小,除了方法论方面的较多创新外,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或概念。而《宦官》一文,则引入了“制度化皇权”(包括“制度化宦官系统”)的概念,试图以此为起点来重新理解和评价唐后期的政治格局,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这方面的讨论在本书中除了《序论》有所论述外,并没有太多论证。但在多次讲座中,作者有较为全面的阐述,也可以作为参证。) 作者选择这一主题,其问题意识大概是:唐朝安史之乱后为什么能维持百年之久?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说“唐后期朝廷的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 不过从史实判断的起点开始,作者就走上了与以往史学界不同的路。在作者眼里,唐后期的中央权威是成功的(并非是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坐大),皇帝权威也是极高的(也不存在宦官专权的问题),德宗甚至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总之,作者对唐后期的政治评价十分乐观,顺着这一逻辑推导下去,作者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灭亡是一个意外,是一个偶然事件。(参考作者在北大的讲座《唐帝国的瓦解及遗产——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 
作者回答的关键词是“制度化的皇权”。他认为,以往的学者“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第6页)作者通过引入制度化皇权的概念,重新构建了唐后期政治权力格局的新理解:“在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德宗时代),出现了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代表这一政治秩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总之,作者认为,唐后期是一种内、外廷是皇帝主导下的合作的政治局面。在此,作者认为学者普遍接受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并不对,而且顺势也否认了陈寅恪指出的“内廷阉官主导,外廷士大夫附庸”的观察。 要完成这一构架,关键的节点在于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的一致性。这样的话,唐后期宦官的权力膨胀现象,就相当于皇权在强化,而不是对皇权的削弱。简单的说,唐后期的中央权力格局是三角两方关系,皇帝、宦官、朝臣是三角,皇权(宦官)和朝臣是两方。 但是疑问会随之而来,怎么理解唐后期宦官废立皇帝的事实呢?首先,作者认为在文宗之前,帝位均为按照传统看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在稳定性上可以说超过了前期。 那么,对文宗朝的甘露之变又该怎么解释呢?作者在《序论》中提到了一点解释:“作为皇帝权威的物质性体现的宦官机构,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当性,也逐渐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进而与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皇帝产生冲突。”(第9页),他认为宦官和皇帝产生裂痕是皇帝的原因导致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文宗朝开始的仇士良以后的宦官势力发展如何?文宗朝之后,从梁、刘开始的那套制度化宦官体系,又和皇帝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限于文章内容,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深入探讨,而是提了一下,认为:仇士良等人并不如梁、刘二人,文宗也不如宪宗,所以“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畛域”。以此来看,作者似乎也承认文宗以后的权力格局与德宗、宪宗朝的并不相同。那么,德宗、宪宗朝的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是否依然存在,两者是否依然具有一致性呢?显然,这些史实,都是作者应该正面面对的重大问题,可惜都没有得到阐述。 
作者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以后将此书发展为两部书,一是“讨论8到10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现在这种种疑问,期待会在未来的著作做出更圆满的阐述。 下篇讲清流文化,其问题意识的产生,作者在《序论》中有生动的叙述。首先是从孙国栋先生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阅读中,产生了怀疑。孙国栋此文,显然是以唐宋变革论为理论背景的。作者欲对唐后期政治精英重新做出解释,就不得不对唐宋变革论提出挑战。事实上,如果清流文化的概念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可,那确实是一个新的宏大框架。 作者认为:清流文化是“从9世纪初到10世纪末,这一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代表性群体从根本上支配了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第240页)。他这里的时间跨越了唐宋,这意味着在政治、文化方面,唐宋两代更具有一致性,而非对立性。虽然清流文化并不是讲社会性质的,但是因为其重要性而居于历史核心,所以会给唐宋变革论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唐宋变革论的一个讨论重点是唐代的社会性质,视唐代为贵族社会(大陆学者一般称为士族社会)。但是以胡如雷、吴宗国等先生为代表的大陆学者,认为隋唐帝国是以皇权和官僚政治为基本模式,与宋并无区别,若论变革,则变革应在周隋之际。若是考虑到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观点,大概更加可以明白大陆学者的认同点在哪里。我们认为,作者新思路的前提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 
作者指出,其实清流现象,在此前已被学者关注,不过分散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中讨论: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第12页)这一现象,大概是指唐后期出现的高官世袭现象,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清流群体是“通过科第、援引、仕宦以及婚姻等途径建立起密切的网络”,具有世袭特征。 对此,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就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支持唐宋变革理论的学者看来,这其实不值一提,这本来就是士族社会的正常现象嘛。如毛汉光就通过统计论证唐后期的高官多来自士族,科举成了士族垄断入仕的新途径,一如九品中正制的功能。而反对唐宋变革理论的如吴宗国师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揭示出唐后期(贞元、元和以后),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指出高级官僚世袭现象,也就是进士家族贵族化。在这里,科举则变成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个环节,而与士族无关。可以看到,对于同一历史现象,持士族论的认为是士族垄断科举,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科举塑造官僚家族,其背后的社会认识观大异其趣。显然作者的立论的背景认识是与吴宗国师等学者的观点相近。 但为了要形成新的认识框架,避免一些旧的问题,描述同样这一个群体,作者就引入“文”这一概念。不过,作者对“文”的作用,显然过分夸大了。在作者的观点中,对文的信仰心态和文词的巨大功用,是导致清流阶层有高超地位、独立价值的根本动力。 
唐代社会对文的信仰心态,正如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所指出的:“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上也难有其匹。”毛汉光的《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等有更多阐述。 其次是关于文词的巨大功用,其实要论证的就是“文”如何在皇权中得以体现。作者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圣旨(或奏折)的表达非常关键;二、文人之间互相颂扬和自许的话语(词宗、大手笔等)。有关圣旨撰写的论证不多。而关于文人互相颂扬的那些话语,大量引用的是墓志等资料。且不说这些文字本身是比较空洞的,而且就墓志本身来说,往往有夸大之处,不可完全采信。 另外,作者所指的清流家族的制造和延续现象,完全归功于“文”。但如果我们从科举视角看,这主要是一个官僚(科举和铨选)现象,和文学当然也有关,但似乎不是必然性的。 相反的是,作者的“清”的概念,则显得太过缩小了。清浊观念来自门阀士族时代,不过唐代官制也有继承,如《唐六典》中明确记载了清望官、清官。这个清官完全不挑战皇权,而只是升官的快速通道而已。尽管作者从历官去概括“清流”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引入了“文”,就极大地影响到了作者对“清”的界定,他所指的清流,重心几乎都在词臣,比之唐代朝廷规定的清官范围大大缩减。唐廷规定的清官,包括三省、御史台的所有官员,三品以上所有官员,还有太常寺、国子监、秘书省等文化部门的所有官员,甚至还有部分武官。可以说,中央官中,大部分都被列入到清官范畴。事实上,从张九龄到唐末李振,他们所指的清流,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唐廷规范的“清官”概念,但无疑都远远大于词臣这个概念。 
若从学术资源上看,郝若贝将中国精英的主题“经过门阀到职业精英再到地方精英的转型”;包弼德在《斯文》中提到士的价值系统有三个转变:“南北朝到唐前期是包容性极强的人文传统;唐后期古文倡导者提出的文以载道;宋代二程等强调的以道的修养为主体”等等,恐怕都会是启发作者的学术资源吧。 如果仅把清流群体的时间局限在唐末之前,那么与传统的中古士族等研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个视角。所以,作者观点的最大要害之处,可能并不仅是把清流概念提出来,而在于:清流并没有在唐末,而是继续到五代乃至宋。这是清流文化理论中颠覆性最大的。其论证过程主要在《清流文化》的第三章和《冯道》一文。 清流文化在唐末动乱中活下来,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清流的独立性,二是清流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这个过程。作者的这个思路,和谭凯《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的观点相似,谭凯认为:以首都(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充分利用了科举制维持社会身份与地位,唐代的国家精英(贵族)在黄巢起义中覆亡,而地方精英得以幸存,推动着唐代的国家精英逐渐向两宋的地方精英转变。(书评见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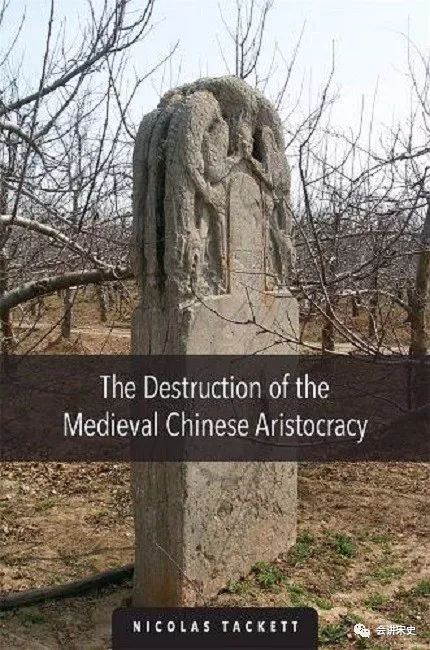
作者认为清流在五代时期,依然很强大,他就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文臣依然占据政治的核心地位。这里作者的论证有些让人不太容易接受。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作者在基于理论的需求而强解史料的现象。这个例子就是《旧唐书•哀帝纪》所载的敕书,其实该敕书乃是朱温为了消灭清流而找的借口,文中说到:“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来看这段史料,其实可以清晰指向的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而非是所谓底层对清流的不满。“蓝衫鱼简”,指的乃是文官,而“拖紫腰金”明显是武官了。邓小南老师《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中,就明确指出“它(诏书)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第109页)文武的矛盾,其实从唐后期就大量展开了,在地方官职系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唐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吏化军职”,押衙等武职称为吏的名号。唐末时期这种冲突尤其突出,白马之祸其实正是朱温篡权的前奏,朱温要在官僚格局上事先布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藩镇系统的武官去代替中央的文官。面对裴枢的不知趣,朱温的愤怒是显然是武官立场的,而非李振式的。当然,冲突中肯定也存在着被清流排斥的李振之流的矛盾,但这不是要害问题。 作者之所以如此理解这段史料,在于从他的研究逻辑出发,不能肯定晚唐五代武人的政治力量是政治主线。他基本没有讨论唐后期五代的武人势力问题,为了强调皇权和清流的成功,对晚唐五代的政治判断过于乐观。实际上,从黄巢起义开始后,北方藩镇几乎所有的文官节帅都被驱逐,武人成为实质的掌权者——这才是地方政治的真相。所以,作者拿唐晚期各地节帅都由文官担任,作为唐王朝权威的稳固的证据,是对唐后期武人势力的轻视和忽视。作者自己也提到了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认为对他启发最大,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从武人势力这个角度去深入和展开,而是换了文的视角,这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问题。实际上,以笔者的观察,唐末五代的政治主流,更应该是“武”,是武人阶层的自觉。这大概才是日野开三郎开辟的研究视角吧。甚至宦官的权力,与其用制度化皇权的角度理解,不如用武人势力的角度去理解更合适。宦官之所以在晚唐具有很大权力,最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神策军,所以宦官权力的实质是武人势力在中央的代表。唐后期,中央和地方都是由武人势力真正把控,我们自可认为这是一个武人势力的时代。如果来观察五代,枢密使甚至凌驾宰相之上,大量刺史都由武人出任这两点,就足以证明五代的武人势力空前绝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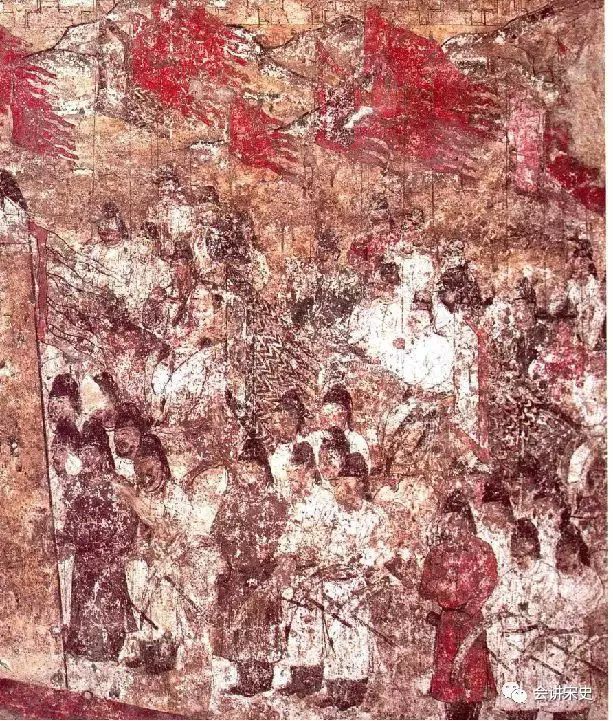
另外,在研究五代文人作用的时候,作者描述了五代十国各政权都对“清流文士”趋之若鹜的现象,吴丽娱老师的《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早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似乎也支持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邓小南老师在《祖宗之法》中指出,文翰之才,在战事扰攘之际,是一种实用性的才能。(第126页)“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第131页)这一判断,显然与作者对冯道以及所有清流文官的地位判断,差别巨大。 四 最后,十分主观地概况一下本书的优缺点。 优点方面,该书体现出作者思路敏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构架宏大,有很大的学术野心;视野广阔,关注的学术成果也中西并包,引入一些新理论如政治书写(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等,让人十分期待。在史料方面,大量使用新材料,特别是墓志,墓志史料的充分运用正是陆扬本人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中的论文,除了早年写的《西川》,及概论性的《清流》之外,其他诸篇无不和墓志材料密切相关,甚至就是围绕着墓志来写。作者曾经强调由于新出墓志中以宦官为传主的大量出现,对于唐史研究都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可能是作者十分重视利用墓志来研究唐史的原因吧。就传世文献而言,也运用娴熟。比如大量使用《册府元龟》资料,而不是简单地仅采用《两唐书》材料,这颇能体现史识。《册府元龟》的史料大量来源于唐代的实录,很多地方比两唐书等更有价值。就细节的表达和描述方面做得非常周到细致,经常能体察入微,给人以深刻印象。另外,作者有对文本和立场的警惕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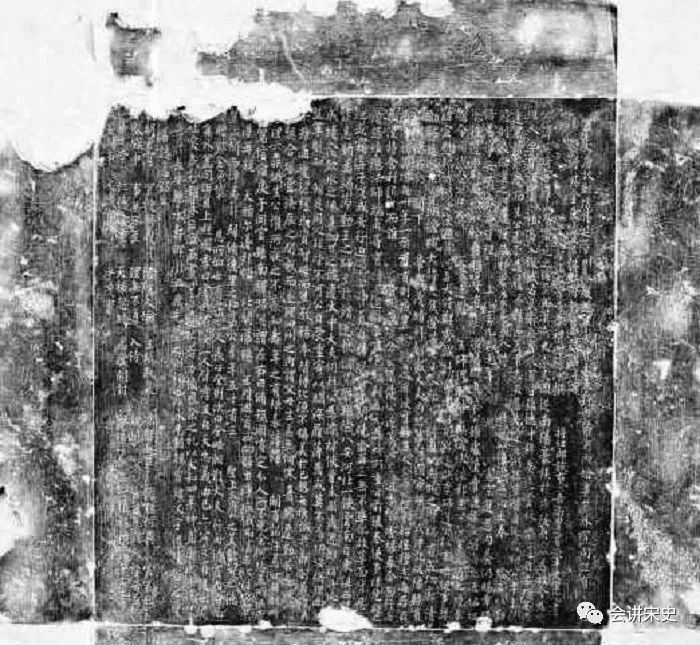
作者的很多问题的视角是针对唐宋变革论而来的,特别是清流文化概念的构建。作者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有更多的海外学术背景,更自然会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巨大影响,所以某种意义上,作者的学术面向更多地是针对海外学术界。针对唐宋变革论开火,就比较好理解。由于近年来大陆学界中,唐宋变革论依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还在持续中,作者的反思和冲击显得十分有价值。就笔者自己的思考,唐宋变革论虽然很宏大,很强的解释力,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是一个应该总体上放弃的理论框架。关键问题在于政治,中国历史的理解中,政治永远应该处于核心的地位,而皇权又是居于首位。按唐宋变革论的逻辑,如竺沙雅章就推出了宋太宗是中国第一个独裁皇帝的说法。(见竺沙雅章著《宋朝的太祖与太宗》,方建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宋太宗和太宗、武后、玄宗等皇帝比,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反思唐宋变革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捆绑,将所有层面的问题都捆绑在所谓的“社会性质”上,一旦社会性质变化了,所有层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其实,从政治层面看,唐宋之间,因袭的东西要大于变革。作者在清流文化的叙述中,虽然具体结论还不够圆满,但这个方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有价值的在于,作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说法。如果没有建立新说予以取代,旧说往往无法退出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枪有其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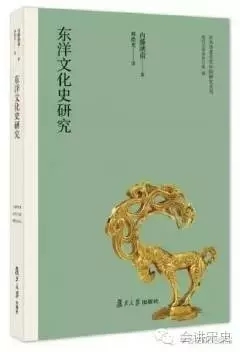
就一些具体问题的颠覆,也是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比如清流概念,就涵盖了新门、旧门,也就本质上取消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就消解了陈寅恪对牛李党争解说的意义。学界已经对陈寅恪的观点展开了各种补正之说,但都是以陈说为框架,而清流一说则另起炉灶。其实作者哪怕就能充分地证实这点,学术贡献也不小了。 还有,本书展现出的新政治史姿态也非常值得期待。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清流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但本质上说,清流及清流文化的讨论,应该属于一部新政治史的范畴。个人认为:政治永远是中国古代史的核心问题。比如用政治视角来观察诏敕的写作,观察词臣这一群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实践。不仅是新的史学题目,更是新的史学方法。 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以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 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感觉生硬和强凑。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的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会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因为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困难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本文发表于《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