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藏书 我大约从小学三年级起至小学毕业的三四年时间里头,读了还珠楼主的大批武侠小说。据已故上海《解放日报》记者许寅在文章中说,还珠氏的全部作品加起来,大约有两千万字以上,是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史上创作最丰的作家。此外我还读了当时流行的北派武侠小说名家王度庐的《宝剑金钗》系列和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有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加起来大约有三千万字之多。邻居送的沈德潜的《古诗源》和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我也时时翻阅,有的诗至今尚能背诵。说句不怕见笑的话,这些小说多数是租的。那时上学父亲每天给我一副烧饼油条的钱,买个烧饼充饥,油条钱则省下来租书,肚皮和精神食粮并重。 武侠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贩夫走卒、卖浆者流爱读,达官贵人、著名学者也喜欢读。据许寅的文章说,他亲耳听到民国年间任立法委员的许宝驹对他的子女说,你们在书店里见到还珠楼主的小说,只要家里没有的统统给我买回来。许先生是有名的杭州横河桥许氏家族的后裔,解放后担任过浙江省人民代表,还是浙江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旧有“许氏五杰”,他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去孤山浙图借书,常见时任馆长的张宗祥先生,每到中午用膳时便一边扒拉饭粒子,一边从抽斗里拿出还珠氏的《蜀山剑侠传》津津有味地读。 不过武侠小说的命运并不好。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是书局不出,断了书源,再是租书摊停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传出邓小平爱看武侠小说,全国各家出版社才又竞相出版,前后正好 30 年。我曾写了一则短文,发表在一家读书报上,题目就是《武侠小说的“禁”与“开禁”》,用了“世事难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 我是十分钦佩和推崇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的,盖因作者的学问实在好,不仅中国的古典诗词歌赋、历史掌故能信手拈来,其学问还涉及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儒道佛三家,诸如写地震海啸,甚或考古(陕西黄帝陵)都妙笔生花。他的文笔也极佳,写蜀山(峨眉山)、黄山(《云海争奇记》)的文字清新可诵,写景状物栩栩如生,虽然这些都是作为背景写的,为满足开展故事的需要。说句可能有人要生气的话,我至今读到的旅游文学作品,敢说没有人超过他的。现在回忆起来,还珠楼主的国学水平绝不在大学教授之下。这样说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天天“听”一位大学教授上课,而且还给我讲了那么多故事。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没教我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书。老老实实说,我最初的根基除了小学高年级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总对我的作文圈圈点点加以鼓励外,就靠走“野路子”读了许多书。 十六岁那年我参加了工作,先是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打杂,后来又当打字员。那时杭州解放路有许多旧书店,每逢星期天我都会去逛书店,上午从路南的书店逛过去,翻书看,有时也买书 ;中午在城站火车站附近胡乱吃点东西果腹,又从路北一家家书店逛回来,到机关食堂吃夜饭,如此持续了几年。平时则在机关图书馆看《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和《新建设》《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杂志,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多种文学杂志。1957 年我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这与我喜欢读书颇有关系。临行之际,机关行政处的一位老木匠用包装速印机的木箱给我做了一个书箱,我就负笈上大学去了。有次整理书籍,一位温州的蔡同学翻了我的书,说了一句:“顾志兴,你还说没读过什么书,你的《古诗源》《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李煜词研究讨论集》,还有这些民国版的鲁迅集子,我们这些上过高中的人,别说读,有些书连听也没听说过。”这是我最早的一批藏书。 大学毕业后到成家,我一直省吃俭用,用省下的钱又购了一些书,藏书有整整一书架了。“文革”中无书可买,记得曾买了一本《汤头歌诀》,想自学中医。现在家里有十一个顶天立地的书架,装得满满的,占了“蜗居”不少空间。这些书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间积聚起来的。我想了个办法,就是“书生书”,买一本书,必浏览一遍,勾出几条资料给报纸、杂志写读书笔记、杂文、文艺随笔之类的短文,写文章赚来的稿费就用来买书,算是“专款专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书多了,文章也多了。初步整理了一下,短文加起来有几十万字,将来有机会可以编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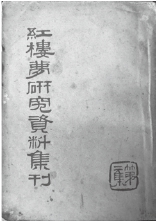
藏书之一《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 21 世纪初,杭州首次评十大藏书人家,我报了名。组委会派专家上门视察,还对我的藏书作了录像,检验是真,最终评为十家之一,发了由市长签发的一块小木牌作为纪念,更为高兴的是得了价值两千多元钱的赠送书籍,对此我引以为无上荣光! 我写的第一本书《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其实此前我还写过一本书,就是《文史常识一百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青年人读书的劲头可真足,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杭州日报》副刊的编辑约我为他们开了一个专栏,叫做“文史百题”,每周周三刊出题目,周日刊出答案,连载了一年多,颇受欢迎。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看到了,上门和我商量把这些内容修改出版,出版后据说印了八万册,这个数字今日看来十分惊人。不过这本书有几篇是我约人写的,所以是合著,不是独著。我真正一人独著的是那本《浙江藏书家藏书楼》,还是与藏书紧密相关的书。 “文革”结束后,全国出现了书荒,杭州也不例外。记得 1978 年 4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顺应读者需要,重版了四大名著,出版了《唐诗选》等读者亟盼的读物。杭州读者漏夜在新华书店排队购书,热情远超在百货公司购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我的一个学生后来告诉我,他先骑自行车在市区书店兜了一圈,感到无望,就径奔近郊的书店才好不容易购到这些书。精神的需要超过物质的需要,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想起杭州在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经太平军两次攻占,文澜阁《四库全书》遭到劫难,藏书家丁丙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全力抢救库书的故事。想到了杭州这个文化之邦、藏书之乡,经此一役,出现了士子无书(课本)可读的情况,当局不得不筹建浙江书局刻书以应急需。我想到了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藏书家节衣缩食收藏典籍使文化不致中断的事迹,而浙江杭州又是历史上藏书名楼迭出的地方。我想应把原来打算研究明清小说的事情放一下,先搞藏书史的研究, 把这些史实记下来,以供后人借鉴和学习。用句藏书家的话来说:自此遂有研究藏书史之志。 当时的客观条件也比较好,我从中学调到杭州教育学院教中文,时间相对宽松,读书时间多了。另外,乐清人蒋德闲兄时主持浙江出版系统的一份报纸《浙江书讯》(后改定期刊物《浙江出版研究》),他知道了我的想法,对我说:你先写些,我给你发,积累多了,慢慢可以成书。”浙报文教组的程组长也对我说:“老顾,你给我们写的关于中学生如何写作文的讨论总结,读者反映不错,听说你在研究藏书方面的课题,浙江是文化之邦,报纸需要这方面的稿子,我给你不定期地发一些,但字数限定500 字到 800 字,你懂的。” 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我认识了胡道静恩师,他不时写信指导,耳提面命,使我学业有所长进。这部书能写成,饮水思源,与道静师的指点和教益是分不开的。 胡道静先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科技史专家。老一辈的学者有个特点,他们的道德、文章都是后生辈的榜样。老先生平时不多言,但一旦谈问题触及痒处,常常是滔滔不绝,额头和眼睛发亮,以至于眉飞色舞。我曾经在四平大楼他的“海隅文库”里多次亲闻謦欬,真是“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老先生除了学问好,腹中江浙两省的藏书故实特别多。自太平军入江浙至抗日战争,江浙两地藏书家为护藏珍籍,纷纷将书转移至上海租界,那里相对安全些,浙江有些藏家多有迁居沪上的。这样民国间上海文化圈内人茶余饭后就多了一个藏书的话题,实为珍贵史料,胡先生当然知道,有的则是他亲身经历,凡所知者,皆娓娓道来,传授给我。 我曾向道静师询及天一阁的失书问题,他告诉我:你写了乾隆征书和咸丰年间太平军入甬的事,民国三年(1914)还有一件大事你可能不知。那时我还是孩提之年,是先人告诉我的。”当时上海有不法书商,勾结巨贼薛继渭潜入天一阁。薛昼伏夜出,白天躲在天花板上,以红枣果腹,夜晚偷盗书籍,捆好后将书用绳子缒出墙外,自有人接应运往上海出售。范氏后人闻知沪上盛传有天一阁书散出,检查书楼发现书少了,在天花板上发现枣核始知其事果真。这样的史料我找遍典籍未见记载,就写入《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略记一二,至 2006年著《浙江藏书史》时较详细地记入,但两处都不忘写上:据胡道静师告我的字样,若不是老人家博闻广记,我懂得什么? 胡道静先生对清末民初浙江的藏书楼特别熟悉,有感情。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湖州陆氏皕宋楼、蒋氏密韵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以及文澜阁的知识。讲后还不忘说一句:我是随便说说的,你写书还得仔细查阅文献史料。” 其实老先生不仅熟悉藏书掌故,对藏书也有真知灼见,见识高人一等。他有篇文章,是为周子美所撰天一阁、嘉业堂书目所作的序言,题目叫做《周子美撰集书目二种序》。当时周书尚未出版,恩师就将打印稿赠我。细读此文,我觉得今日虽有多种关于嘉业堂藏书的专著出版,但对嘉业堂藏书概括最全面,评述最为中肯的还是先生的文章。我的那本书出版后,我将先生的文章列为参考书目之一。 道静师不仅将腹中所知,倾囊相授,还帮助我著书寻找线索,介绍前辈。举个例子,我的祖籍浙江海宁自明清以来藏书就很出名,乾嘉学者吴骞、陈鳣以藏书闻名于世。但道咸时期的海宁“二蒋”资料却不多,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吴晗的《两浙藏书家史略》所述亦极简略,令人难以下笔。我将这个困难情况告知了恩师,道静师对蒋光煦比较熟悉,告我找哪些书读,又向我介绍了蒋氏所刻《别下斋丛书》。谈到蒋光焴,他说:有了,蒋光焴的后人与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是亲戚。你回杭后给陈先生写封信,告知他你著书的情况,他定会复信介绍你与蒋先生认识的,你可向他请教。”我给陈从周教授写了信,不久即接到蒋启霆(雨田)先生来信,详细告诉我,他是蒋光焴(寅昉)的四世孙,蒋光焴与蒋光煦是从兄弟,蒋光煦为二房,蒋光焴是四房。当年蒋光煦的别下斋与从弟蒋光焴的衍芬草堂,这两座有名的藏书楼俱在海宁硖石镇通津桥东河街(旧名南大街),两座藏书楼毗邻而立。雨田先生对我写这本书很支持,信中说他现时不忙,主要给从周先生的研究生上些文史方面的课程,有问题尽管写信给他,他会将自己所知尽数告诉我的。来信并附来从周先生文章《梁启超与王国维题 <西涧草堂图 >》和他自撰的《西涧草堂藏书纪略》一文。这使我知道了蒋光焴除海宁硖石有衍芳草堂之外,在海盐南北湖还有一处藏书楼西涧草堂。 当庚申(1860—1861)之际太平军入海宁,别下斋藏书被毁,蒋光煦痛惜藏书之失,呕血而亡,以身殉书。蒋光焴的藏书要幸运一些,他先期将十万卷珍藏转移至当时比较偏僻的海盐澉浦南北湖的蒋氏丙舍,后随着战事的变化,携书渡海至绍兴、宁波而抵武昌,千方百计护书。在安庆与曾国藩相遇,赠曾扬州诗局本《五韵》及《郝注尔雅》,曾国藩以“虹穿深室藏书在,龙护孤舟渡海来”一联回赠于蒋。共和国成立之初,蒋氏后人将千方百计护藏的十万卷藏书悉数捐给国家,现珍藏于北京、上海、杭州各大图书馆中,使这些珍本古籍历尽战乱而找到了最好的安身之所。 
《浙江藏书史》 前已提及西涧草堂外界知之极少。陈从周先生的夫人是蒋家后人,蒋雨田先生是蒋光焴的四世嫡孙,他们告知我的有关情况在某种程度可以算是第一手材料,这也成了我这本书的一个亮点。改革开放之初,海盐县人民政府规划南北湖风景区,陈从周先生曾为之规划,西涧草堂得到重修保护。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应邀去海盐讲课并参观张元济图书馆,归途专程去参观西涧草堂,曾携去《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册,写了几句话置于草堂书楼原藏书处。十多年后参加在南北湖召开的一个会议时,我一早独自一人再访书楼,看到当年赠于书楼的一册书已然不在。我心中暗喜,书有人看,毕竟是件好事。此次我发现楼下多了一所亭子,亭名“定亭”,守门的人悄悄告诉我:陈从周先生的夫人名蒋定,她的骨灰就安葬在亭下。我是相信的,回归故里(蒋光焴的先人本是海盐吴叙桥蒋家村人,乾隆中迁海宁硖石聚族而居),是最好的归宿。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原来只是想写成一本通俗读物,但在道静师的指导下,最终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我一直以为没有道静老师的指导我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部书的。 书稿成,道静师抱病为作长序,序写好后以至无力执笔写信,只在稿纸上写了几个字“因疲困,不写信了”。书名是请杭大读书时的老师夏承焘先生题写的,老人家当时亦患病,后来我和陆坚师兄委托师母吴无闻先生在夏老健康允许时执笔题写,这提高了这部书的品位。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出版后,道静师特地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将书分寄在上海的蔡尚思、周子美、郑逸梅、陈从周、黄裳等诸位前辈,要我听听他们的意见,为尔后修订做些准备工作,信中还附来了他们寓所的详细地址。我知道老师的深意,是将我这个学生向前辈们引见,让他们多多指导帮助。当然我也不忘给蒋雨田先生寄了书,他不仅和陈从周先生一样提供资料,还在我写蒋光焴那节的原稿上仔细修改过,使史料更为翔实。我知道这几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忍去打扰他们,但除郑逸梅先生外,其他几位都给我写了回信。回信中以蔡尚思先生的信最长,除了鼓励以外,还特别告诉我,将来如果修订要加强藏书楼作用的论述,指出藏书楼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后来我撰《浙江藏书史》,就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内容,专门写了一章。我还因别的事拜访过周子美先生,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十分硬朗,他是华师大的退休教授,还有个身份更使我崇敬,他是湖州嘉业堂藏书楼的第一代编目部主任。谈话结束,老人要我等一下,在书橱里翻了一会儿,找出两页横格十行纸手写的材料,一定要送给我,并说:这是早年写的一份宁波蔡氏墨海楼的材料,现在送给你,将来你写《浙江藏书全史》时可能有用。” 我的这部书初版于 1987 年,当时印了两千册 ,1990 年又重印了两千册,在学术著作印数不多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差足自喜。但我知道这和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的“鼓吹”是分不开的。20 世纪 80 年代起,出现了传统藏书楼研究热,且不断升温,徐雁算是热衷者之一。他的大著《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的著述篇里介绍了我的这本《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其中颇多美言,他说此书是研究地域藏书文化史的第一部,又说什么“考证仔细”等等,可能引起了一些藏书爱好者的兴趣,因而寻觅这本书。我至少收到一二十封来自边远省份的来信,来信人素不相识,托我购买我的那本书,言明只要书购到、寄到,即将书款、邮资寄上云云。我怎么好意思收人家这区区书款?只能赠送,将出版社给我的样书和自己买的一本一本地寄出去,最后只剩下初版本一册和重印本一册,作为自己的收藏。前几年我院历史所的一位研究员打电话告诉我 :《文汇读书周报》的中缝中有人发了求售《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的信息,出价是原书的十倍,你还有吗?”我找来一看,果有此事,本该送他一本,但书已没有了,无奈之下只能“装聋作哑”,感到很对不起那位读者。 还有件事,因为此书的著述,傅璇琮先生主编《中国藏书通史》时,通过我的同事徐吉军先生邀约我撰稿,我认真地完成了明代编的任务,并应傅先生之邀对清代一部分作了修订。我还写了一本《文澜阁与四库全书》的专著,应该说也是这本书的其中一节的延伸,当然是另下了功夫的。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出版后,我特别高兴的是认识了在苏州的徐桢基先生。徐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晚清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五世玄外孙,属长房陆树藩这一支。他受母亲的遗命,整理家族史。研究藏书史的人都知道,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树藩作主将皕宋楼全部藏书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中国文化界、藏书界受到极大的震动,许多老先生痛心疾首,以至伤心落泪,对陆树藩是一片斥骂。这件事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20 世纪 90 年代初浙江省政协的多位委员联署提案,要求有关部门设法与日方联系,赎回这批藏书。提案转到文化部,但未见下文。实际上赎回藏书是不可能的,当年的事情是商业行为。徐先生读到我的那本书,就写信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而我俩建立了联系,对于皕宋楼藏书舶载东去流入日本的事,我是知道的,写那本书的时候也搜集材料,请教老先生,但还是在迷雾之中。当事人陆树藩背负骂名,但从未见有他本人的申辩和说明。收到徐先生的信,我敏锐地感觉到,这重迷雾可能要散去,皕宋楼藏书东去的谜底有望揭开。从 1987 年到 2007 年的这二十年间,徐先生以衰病之身奔走于苏州和上海之间,找到了许多当年的文献(有些文献远在台北),我则在杭州查《申报》,找陆氏谱系,最终在 2007 年他写出了《藏书家陆心源》一书,由我撰了一篇序文公开出版。我那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将这件事的真相逐步、适时地告知国内藏书研究者。到 2007 年,也就是皕宋楼藏书去国一百周年之际,湖州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记得到会的有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海峡两岸的藏书史研究专家,我宣读了一篇论文揭示了真相,基本上廓清了皕宋楼事件的迷雾。至今十年来,对这个问题未闻有什么不同意见。《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的皕宋楼文字约三千左右,到 2006 年我的《浙江藏书史》出版时字数增加了一倍,到 2008 年我修订《浙江藏书史》,字数增加到万字以上。我想这部分内容也是这部书的亮点之一。 记得庄子说过“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话。《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全书不足 24 万字,2006 年我写《浙江藏书史》是 66 万余字,2008 年修订《浙江藏书史》时达到 75 万多字,2006 年此书还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社科成果二等奖,似乎这本书该画上句号了。但这八九年来我在一本自用书上还不断地用红笔涂涂改改,感到还有可增补和修改的地方,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将这本书改得更好些、更有价值些。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年过不惑,但抓住了一个机遇,就是有些有真学问的老先生虽历经劫难,有的人虽身残而志坚(胡先生亲口告诉我,“文革”中被打断了腿发配到里弄倒马桶),对后辈请益总是倾囊相授,彼时有的还身份未明,但也热情地帮助我,胡先生是一位,还有别的几位。这书迟十年也不行,许多老先生太老了,或已作古,随着他们的离去,有些鲜活的材料再也见不到、听不到了。 我是幸运的!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第十五辑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