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陆游的乡村世界》,让包伟民感到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觉得“历史学要回归叙述”,不再执着于社会科学式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还是“放不下分析这一块”,不想完全走向讲故事。此外,从《宋代城市研究》《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到《陆游的乡村世界》,也反映了他“目光向下”的学术过程。 澎湃新闻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新作中的宋代农村社会、他的“目光向下”、分析与叙述间的关系等,以下为访谈正文。
澎湃新闻:您之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代经济史、城市史,是从何时起对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产生兴趣的?为何选取陆游作为研究对象? 包伟民:十多年前,我在研究宋代城市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我们现在对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一些大的认识,基本上都因循着1940年代以来前一辈学者敲定的框架,将他们的认识作为既定事实。但是前辈学者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吗?我觉得很多基础性认识是要重新验证的,这也是我这两年经常提到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天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手段比前辈学者方便得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本来大家以为已经基本定型的一些看法,验证下来其实有很多认识的误差——前辈学者他们毕竟是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当时我准备写宋代城市的时候,有位老朋友到我家里聊天。他说这个题目很老了,能写出东西来吗?我说我也没把握,我先看看。很多人对唐宋城市的认识来自于日本学者加藤繁,如果加藤繁真的把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就不做了,换题目。 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把加藤繁提出“加藤范式”那篇文章——《宋代都市的发展》中的材料一条条去跟原书核对,得出结论,加藤繁的主要问题是他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是长安的,但是他的结论覆盖到了全国。城市和城市是不一样的,这中间肯定有落差。现在小县城怎么跟北京比啊?怎么可以把关于北京的结论用到每一个城市上呢? 比如,受加藤繁影响,很多人觉得唐代城市就是围棋盘那样一块一块的,宋代城市就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但我的研究可以非常清晰地证明,加藤繁所描绘出的城市图景是人工规划出来的城市,是长安、洛阳那样的大城市、都城。唐代长安城的制度渊源来自于北魏平城,北魏的统治民族是鲜卑族,要监管汉人,城市里的坊墙并不是为了防御,恰恰相反,是城市管理者为了监控汉人而设置的,所以坊墙不能太高,差不多就到人的肩头。骑兵在大街上巡逻,坐在马背上能够看得到坊区里面,还规定坊门不能随便开,晚上要宵禁。唐代长安城也是这样,管理是很严格的。 但是像长安、洛阳那样的城市占比是极低的,绝大部分城市是中小城市、州县城市,虽然城内也有坊,相当于现在的社区,但是那是用于行政管理的居民区,坊的外面何必非得筑起围墙,而且这些城市都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并非出于人为设计。但是“加藤范式”影响太大了,我们看见个“坊”字,就觉得一定有围墙,其实南方城市许多连城墙都没有,更不要说城区里面的坊墙了。这是城市史研究给我很大的触动的一个方面,即很多问题要重新验证。 另一方面,我觉得目光应该“向下看”。当然国家总体的政治制度设计、皇帝颁布的诏书等等非常重要,而且很多时候只有高层的历史活动才有资料留下来。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我说你们想想看,各位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读下来,然后就去研究古代的“政治局”怎么开会了,宰相怎么跟皇帝讨论问题,这中间落差太大。当然不是说没有生活体验就不能做研究,但是研究自己有生活体验的领域,尽管我们的体验跟古人会有很大的不同,也总比完全没有生活体验的领域好多了嘛。 所以在2014年《宋代城市研究》出版之后,我就“向下”转向了宋代乡村研究。其实研究宋代乡村的学者也很多,尤其是日本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就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不乏一流学者。这两年研究宋代乡村的人少了,而且结构性的推进更是很少。这种老题目写得慢,要把原来东西解构掉不容易。 我曾经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读陆游的文集和诗集。陆游是“南宋四大家”之一,他留下了9300多首诗,在整个古代中国诗人中数量最多,在这些诗中,有60%甚至70%是写乡村的。因为宋代官太多了,官员们任期都不长,要轮着当嘛,所以陆游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农村的。而且他的诗创作时间编排是准确的,是他去世之前亲自整理的,因此容易被引作历史研究的资料来使用。 我觉得其中很多材料都可以用,但是拿它来讨论国家制度又不是太直接,诗歌的写作总是含含糊糊的,是种情感的抒发。所以做完笔记之后就把这些材料放在电脑里了,但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这些材料肯定会有用。去年我试着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论文,近5万字,发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到了2020年初,因为疫情被关在了舟山,当时手头没有书,只有电脑里的一些笔记,我想干脆就把“陆游的乡村世界”写成一本小册子吧。出版社抓得也比较紧,所以很快就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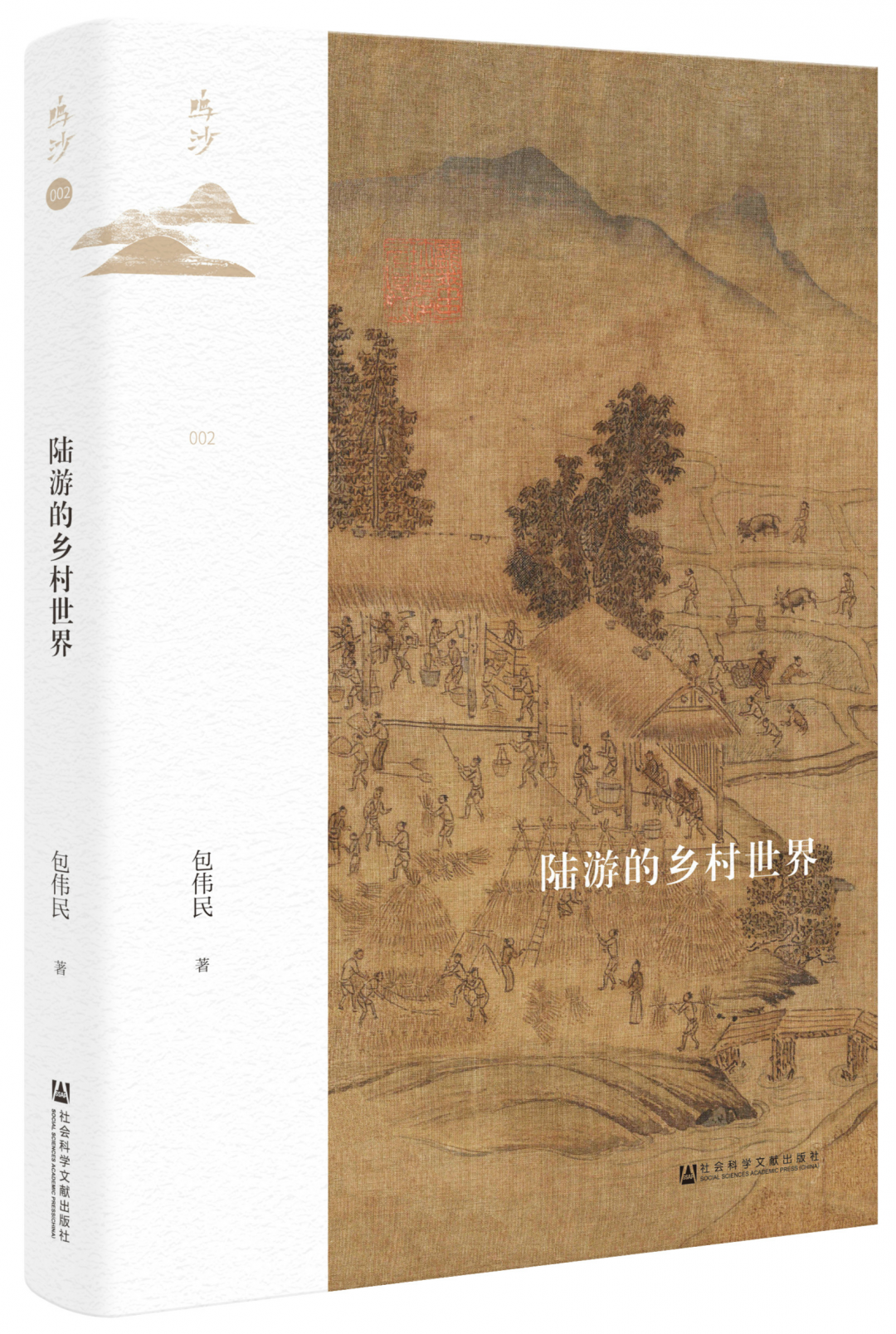
▲包伟民著《陆游的乡村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 澎湃新闻:从城市史到乡村研究,从制度史到日常生活,可否谈谈您近年来“目光向下”的学术思考? 包伟民:我这几年确实是“目光向下”了,但是并不是说高层的东西不值得写,赵冬梅老师的《大宋之变:1063-1086》写的都是皇帝宰相,也很精彩啊。写高层的读者更多,多数读者感兴趣的还是帝王将相。都说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书中只是被人摆布的数字。 我不甘心,我的“目光向下”的确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在里面,是想要尽量用自己的工作去呈现普通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以前体现人民的研究就是农民战争,那是人民实在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舍了命造反的绝望状态,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怎么创造历史?这是我们需要去弥补的。历史著作得把人给写出来,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完全变成要素分析,“人”没有了,那就不是人类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了。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发展,还不都是穷苦的底层民众辛勤劳作一点点干出来的。你去看宋代文人描写的农民的辛劳,我们得给写出来。我是1977级的,还算运气好,没有下过乡,初中毕业到工厂干活,当然也干过一些农活,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想必须要把基层民众对历史的贡献给写出来。 另外,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存着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例如我们说明代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缙绅阶层”,当时对缙绅是有明确定义的,你得有功名,最起码得是个秀才。如果你是缙绅,那么到衙门去打官司,县老爷就不能随便打你的屁股。如果要对你动刑,就得请示学官先把你的功名剥夺掉。这个阶层的人慢慢控制了地方事务。这种格局必然是从宋代开始慢慢演变的,但是演变过程我们现在还没有讲清楚。也就是,具体呈现宋代对后期历史的影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重要领域。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邓广铭先生说,要研究宋代,那必须要懂唐代,宋代很多东西尤其是制度性的东西都是唐代来的,宋代初期只是改一改而已,多数不是重新创立的。老师一辈所强调的“向前了解历史演变的渊源”,至今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现在我同时还跟学生强调要“向后观察历史发展的影响”。目光局限于宋代,有些东西看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走向,你到明代看一看,原来它走向了这里,再反过来看宋代,就更清晰了。 比如说我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一书中写到的关于“市船”的解释,用的就是向后观察的方法。 澎湃新闻:陆游这样一位士人、文坛领袖,在乡村中承担着哪些社会角色?陆游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如何将儒学渗透到乡村? 包伟民:当时大多数读书人希望住到城里去,城市的生活条件比农村好,曾幾的儿子就劝陆游住到城里去。他祖父在城里有房子,但是陆游没有去,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考虑,他没有交代。但士大夫即使人住在城市,一般也都有田产在农村,当时农业是主要经济嘛。所以士大夫在农村其实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角色,但是也有好几种类型,不能拿一个模子去套他们。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研究的刘宰就与陆游不太一样。刘宰是镇江金坛人,他的生活环境跟陆游相近,但官比陆游小。刘宰是比较积极介入地方活动的典型,发生灾荒他出面组织赈灾,地方工程他出面推动,还跟社会上层的高官积极互动,信件往来很多。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强”。以前理解似乎豪强就是大地主,其实从古至今,没有政治背景的人“豪”不起来也“强”不起来,光有钱是不够的,还得有势。即使他自己不当官,也得转弯抹角跟某个官员挂上钩。这类人以往研究比较多。 陆游是比较特别的。他特别低调,“尤避行迹”,当然他也不是一点都不参与地方事务,比如让儿子参与到地方志的编写中,作为史官,他还给地方志写了序言。但是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对地方造成骚扰。还有一点,陆游是个大文人,声望非常之高,这个是其他人没法比的,所以他在诗作中写了不少与文人交游的情况,但在书里我没有写太多,因为文学史领域已经有很多研究了。 另外,中国后来变成儒家社会了,怎么变过去的?儒家本来是高高在上的,民众一般都是热衷于祭祀各种鬼神,跟儒生间是有矛盾的,很多儒生地方官都反对淫祀,把那些跳大神的人给禁了。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深入,我想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宗族。宗族里的族规都是儒家那套东西,一般由族里的读书人主持这件事情,没有读书人的家族也会参考其他有读书人的家族,然后通过宗族这个渠道慢慢向基层渗透。当然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要素就是科举,因为读书有好处,可以做官。我们可以从陆游身上看到读书人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无论是他作为士大夫的榜样作用,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农夫们传达的文字知识,都是如此。这些我都尽可能写在书中了。 
▲放翁先生遗像 澎湃新闻:宋代的乡村社会与城市有哪些差异? 包伟民:古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城乡之别去想象。因为现在的主流是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经济,而当时是农业经济,所以当时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了农业社会的特点,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原则。 当然到宋代,城市进一步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格局和新的特点。我们以前有很多学者沿着加藤繁的思路,觉得宋代以后城市更多就是一个经济中心了。我想这种认识有点极端了,忘了当时城市主要仍然是政治中心,而且行政层级高的都会城市总比一般城市的经济地位要高。虽然也有个别例外,但绝大部分都是行政层级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地位的。 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就是帝制国家的统治据点,它们必然位于交通要道的某个节点,同时必然也会变成一个商业交流中心,更何况这种城市人口密集,官员、军队以及其他为他们服务的人构成了城市的主要人口。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困惑。例如南宋时期的临安城里六七十万人,官员、军队及其他一些服务人员之外的城市产业是什么?他们拿什么产业来支撑自己的经济?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我觉得商业肯定占很大一部分,但是我们古代的城市不像欧洲,手工业比例不高,我们的手工业主要在农村,这个去看清时期的市镇就很明确了,市镇主要作为商品交换的据点而存在,只是集中了一些个体家庭没法做的少量行业。所以市镇的主要产业不是手工业,而是商业。当时的临安城也有手工业,但不是经济的主体。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背景下,从宋代开始,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开始慢慢有了一定差别,“乡下人”这个称呼已经有了瞧不起人的味道了。但还是要强调,不能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宋代的城乡差别,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太愿意用“市民文化”这个概念,因为中文词汇中“市民”一词特指欧洲历史上处于封建结构之外的、不受封建领主管辖的那批人,如果再用它来描述中国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概念混淆。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概念——“市井文化”,把二者区分开来。 从宋代开始,城市确实显示出以商业为中心的某种新的文化现象,不少士大夫写过在农村生活不方便,东西也买不到,城市里方便很多,所以他们就从农村搬到城里去。这种流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科举。跟现在“学区房”一个道理,城市里信息灵通,有好的老师,肯定比在农村考科举方便。其实这在某种程度反映了城市是政治中心的特点,因为科举是政府举办的。有人说宋代以后的经济要素越来越厉害,但这种认识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认识到,与此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强了,通过科举等把各种的有利要素攥在了自己手上,这不是一个你强我弱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那么谁是城市文化的主导者?其实是很清楚的。表面上看是商人奢侈的生活,他们出钱创造出来很多东西,但是商人的背后还是政府势力,他们的后代还是要去考科举,这样他们的财产才能稳定下来。早先的研究说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但其实没有把主从关系给讲清楚,主体还是政治强权,这也是城市的文化特征。 澎湃新闻:陆游所在的山会平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包伟民:写了陆游这本书之后,我有个之前没有清晰的认识,现在慢慢明确了。所谓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从黄河中下游到了苏南浙北长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浙江地区原来的中心在会稽山北麓,江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鉴湖造就了山会平原的发达,那么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绍兴地区是否完全被比下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前回答是语焉不详的,或者自然而然地觉得肯定是落后了,而且之后浙江的中心城市也是杭州了。其实这里面有个发展过程,在陆游的时代,山会平原和苏南浙北地区最起码是并驾齐驱的,有些方面恐怕还要更发达一些。 山会平原是已经发达的地区,鉴湖修建于东汉,带来了农业的持久发展,在陆游的诗文中,能够体会到其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长三角的太湖东岸地区,它当时还处在一个开发的过程中,围田不是一下子解决区域开发问题的,对土地的改造是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到明代中叶才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开发程度加深了,速度加快了,而山会平原相比之下就有点落后了,所以浙江的中心城市才从越州(绍兴)转移到了杭州。尽管这一点我在书里没有展开讨论,但在结论里讲到了,山会平原一直是江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之所以强调这句话,是因为后来到明清时期,所谓“江南”并不包括山会平原,好像大家都觉得浙东地区一直就是比较落后的。其实产生这种误解,原因在于许多人研究中用的材料都是浙东丘陵地带的,但是浙东地区的丘陵地带跟平原地区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耕获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