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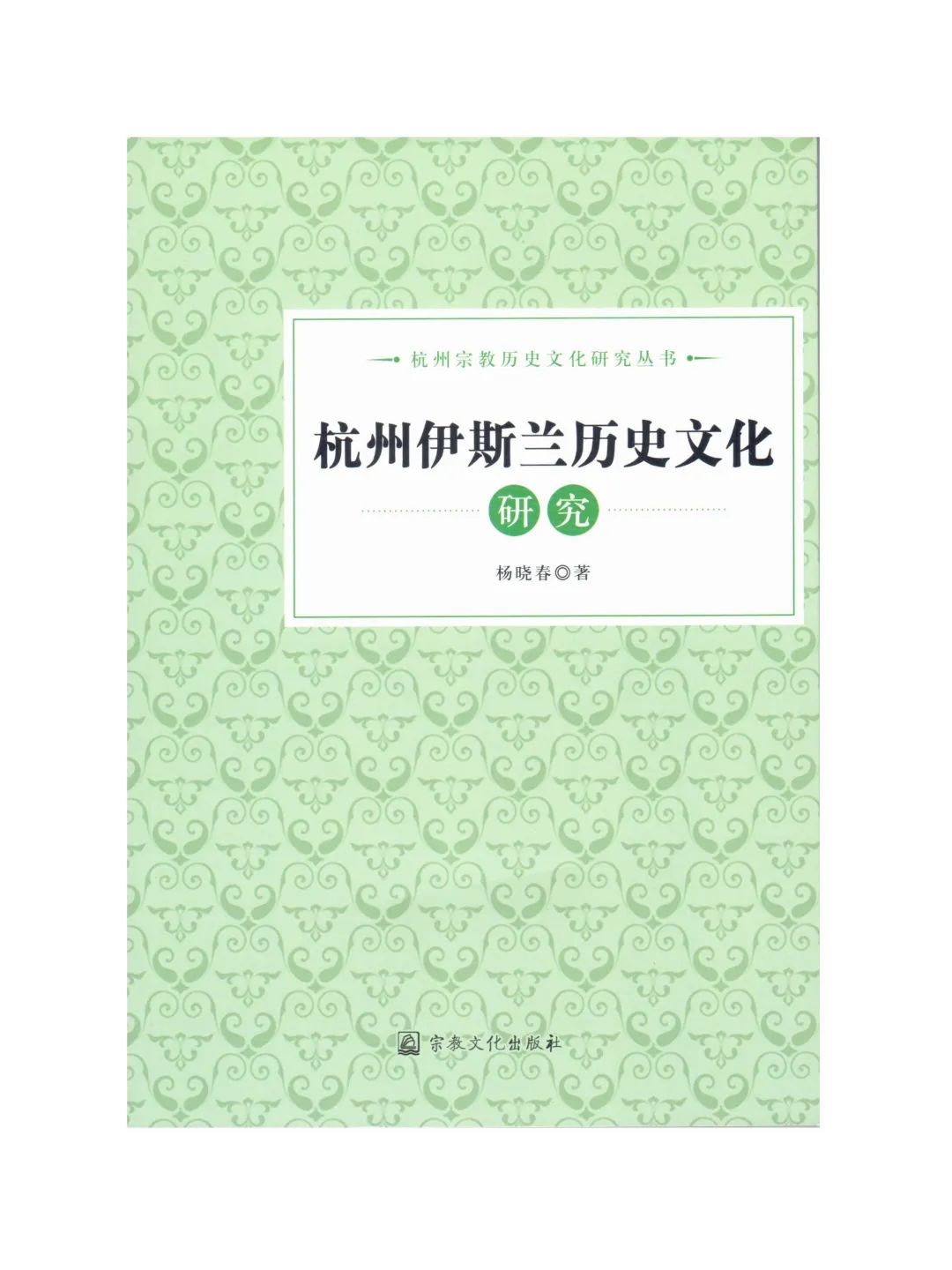
作者:杨晓春
出版时间: 2022-12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ISBN: 9787518812578 壹 作者简介 杨晓春,男,浙江湖州人,1974年出生。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本科(1996年)、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1999年)、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2004年)。现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史、中国民族史(回族史)、中外关系史(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石刻等学术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贰 内容摘要 《杭州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主要从穆斯林在杭州的活动和伊斯兰教在杭州的发展两个方面,展现杭州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关于前者,大致按照时间先后进行叙述,并重点讨论有较多史料支撑的元代杭州回回与明末清初杭州回回士人丁澎家族两个问题。关于后者,除了集中探讨杭州伊斯兰文化遗存的代表——凤凰寺的历史。还从有限的史料中爬梳出杭州其他的清真寺以及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宗教典籍、对外的宗教联系、教派等零星的信息,尽量复原一幅比较完整的宗教文化图景。 叁 目录 绪言 上部 杭州回族史研究 第一章 回族在杭州的聚居与繁衍——人口、社区、墓地与风俗 第一节 唐宋时期有无穆斯林在杭州定居 第二节 元代回回在杭州的聚居 第三节 元代西方旅行家笔下的杭州穆斯林状况辨析第四节 明清杭州回回的一般状况 第二章 明末清初杭州回族士人家族——丁澎家族考析 第一节 有关丁澎家族的基本史料 第二节 丁澎家族系谱重构 第三节 丁澎家族与汉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第四节 略论跨文化关系中的回回士人——以丁澎家族为例 下部 杭州伊斯兰教史研究 第三章 杭州伊斯兰教历史钩沉——清真寺、宗教人士、著作与教派 第一节 杭州清真寺历史概况 第二节 元明清杭州伊斯兰教宗教人士辑存 第三节 清代杭州伊斯兰教界的对外联系 第四节 杭州伊斯兰史上的两部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教款微论》与《五功必要》 第四章 凤凰寺——杭州伊斯兰历史的一个缩影 第一节 凤凰寺的名称问题与始建时代的讨论 第二节 元代凤凰寺的创建事实与明代凤凰寺的延续和重修 第三节 清代凤凰寺的四次重修 第四节 清末民初凤凰寺之实况 附录 附录一 凤凰寺现存明清时期汉文碑刻录文与拓片 附录二 杭州相关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序跋 附录三 明清方志等地方文献有关杭州清真寺的条目 附录四 民国以来杭州回回墓碑的发现与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肆 绪言 一、“天城”杭州的开放、包容与伊斯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句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谚语,将杭州城定格在了理想城市的位置上。有意思的是,13-14世纪以创作了东方行纪而知名的几位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2]、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3],也都把杭州(西方人一般用“行在”一词的各种译音称杭州[4])称为“天堂之城(the City of Heaven)”。[5] 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东方学家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的名著《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在注释鄂多立克的游记时,就猜测“天堂之城”的说法来自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Above is Paradise, but Su-chau and Hang-chau are here below)”,并注明出自迪阿尔德和戴维斯(Duhalde and Davis)。[6]五十年后法国东方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年)的修订本中,也保留了这一意见,但是把谚语出处写作“迪阿尔德、戴维斯及其他人(Duhalde,Davis, and others)”。[7]根据修订本的索引,可以查得Duhalde就是Du Halde,此人即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Davis就是Sir J. F. Davis,此人即英国外交家、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年)。修订本第四卷有一份部分参考文献的目录,可以查得引用的Davis的著作为《中国人》(The Chinese)。按此书全称《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览》(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8]不知何故,参考文献目录中没有看到Duhalde的著作条目。不过杜赫德的汉学名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la Chineet dela TartarieChinoise)是非常知名的,查检此书第一卷有关中国各省的介绍,其中关于浙江省省会杭州府(Hang Tcheou Fou)的描述中,有如下的一句话:“根据中国的谚语,这是地上的天堂(A en croire le proverbe Chinois, c’est le Paradis dela Terre)”。[9]此书的英译本称《中国通史》,这句话则译作“If we believe the Chinese Proverb, it is the Terrestrial Paradise.”[10]比杜赫德更早,明代后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中就提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谚语。[11]“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谚,最早起于何时,不易说清,但至少在两宋之际就已经广为流传了。南宋初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曹勋称:“臣在敌寨时,具闻敌人言:‘金国择利,便谋江南。’又曰:‘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其势欲往浙江。”[12]知名的文学家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也说到:“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13]此书写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作为谚语,此后的文献中也多有记载,一直到较晚的时候,“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才变为今天通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么看来,西方旅行家的用词,也确实是有所本的。 怎么样才能称得上是理想城市呢?我想有三个方面是需要考虑到的:第一,自然与宜居;第二,繁荣与富庶;第三,开放与包容。西子湖、钱塘江,更有城市西部、南部数不清的高山低岭,杭州占尽山水之美。自宋代以来,杭州也一直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而著称。而开放与包容,则有待于一个城市在接纳外来人口、外来宗教、外来文化等方面的考验。 杭州的清真古寺——凤凰寺,历经八百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矗立在杭州城市中心最为繁华的御街(今称中山路)西侧。多少年来,每日唤拜之声从寺内传出,引导穆斯林(回回人)进寺礼拜,这不正是杭州之开放与包容的鲜明体现吗?凤凰寺的背后,是一幅杭州吸引着回回人入居、生息、繁衍,参与杭州的建设、也创造着自己美好生活的生动而又绚丽的历史画卷。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的“导论”的开篇提到一个观点: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的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感情,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出的魅力。[14] 比附史景迁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在中国的城市中,杭州就是少数几个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城市之一。自蒙元时代以来,杭州一直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并保有着这种吸引力。现在,我们需要回顾、分析的是杭州对于世界的吸引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西湖、钱塘江、人口众多、繁华富庶、数不清的桥……,这些方面固然是要考虑到的,而独具特征的杭州伊斯兰的状况也是焦点之一吧,不然,何以在从蒙古时代的世界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ṭṭtūṭa)[15]到近代美国传教士、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校长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4年),那么多的外国人士的记载中都会写下杭州伊斯兰的点点滴滴呢? 二、杭州伊斯兰在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上的位置 回族是今天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广泛、影响较大的一个。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国少数民族,回族是唐宋以来特别是元明时期由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迁居中国的诸穆斯林民族融合并吸收汉族、蒙古族等中国本地民族因素融汇而成的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历史上入华的诸穆斯林民族,一般通称为回回,经过分合传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回族。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迁居地的自然、社会、居民、文化等状况,对于迁居此处的回回人也势必带来影响。入居中国的回回侨民群体,往往优先聚居于大江南北一些交通便利、政治经济地位突出的重要城市。杭州地处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一度也是重要的港口(或者靠近海港),且五代以来一直是江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时期为都城所在,元代为江浙行省治所,明清以来为浙江省省会),也便成为吸引回回人入居的重要城市。杭州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回回聚居地之一,[16]杭州的地理、社会、文化条件也给予了杭州回回人深刻的影响。例如立足于杭州乃至江南的社会、文化环境,回回士人家族在杭州得到充分的发展,以知名诗人丁澎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丁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杭州回族史最为突出的历史阶段是元代。元代不但是奠定杭州回族-伊斯兰教格局的重要时期,还是回回社区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相应地也留下比较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文物遗存。而在中国回族形成的关键时期——明代,[17]则很少有新的域外回回人的迁入杭州;特别是在明代后期中国回回社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期,杭州在回族-伊斯兰教方面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认为明代杭州回族-伊斯兰教,主体是一种平稳的延续状况。清代的状况,和明代基本相仿。因此,直到今天,以杭州为主的浙江省回族人口一直是比较少的。不过,正如前面所述,杭州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回回聚居地,所以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在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ère)[18]、桑田六郎[19]、马以愚[20]等中外人士进行的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清真寺的考察中,杭州仍是重要的对象。 总体而言,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难得的伊斯兰文化遗存——凤凰寺,有其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的探讨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史料和前人研究的简要状况 正如一般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的史料总的说来是比较缺乏的那样,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史料总体而言并不太丰富,特别是回族自身的记载更为有限。 传世文献资料类型多样,既有被称作“一地之史”的地方志的记载,比较重要的如成化《杭州府志》、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康熙《杭州府志》、康熙《仁和县志》等明清方志;也有元代周密《癸辛杂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21]、清代姚礼《郭西小志》、范祖述《杭俗遗风》等有关杭州地方的私人笔记一类的记载;还有元代意大利天主教士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伊本·拔图塔游记》、明代末年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清末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Frederick D. Cloud)《天城杭州》(Hangchow, the “City of Heaven”)、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教育家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杭州行纪》(HangchowItineraries)[22]等不同时期外国旅行家、宗教徒有关杭州的见闻录。既有汉人文士、官僚的记述,也有回族自己的一些零星的记载,回族方面零星的记载主要出自《教款微论》、《修真蒙引》、《经学系传谱》、《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性理》、《清真释疑》、《五功必要》等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特别是这些典籍的序跋部分,可谓吉光片羽。就时代而言,则基本上都是元代及此后的明代和清代的,唐、宋时期的直接记载几近阙如。上述各类历史文献,最系统的当属地方志等地方文献中有关杭州清真寺的记载。 考古文物资料则集中在凤凰寺。除了凤凰寺古建筑本身,还有保存在碑廊的珍贵的碑刻。凤凰寺古建筑,以颇具特征的三个攒尖顶砖砌大殿为主体,是中国伊斯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深为中外建筑史家所瞩目。可惜同样颇具特征的大门和宣礼楼在20世纪前期被拆除了,遗憾之中使人略感欣慰的是,大门和宣礼楼的图像资料还多有保存。现有的大门是照着原先大门的样子于近年重修的。凤凰寺现存碑刻分为两类:一类是20方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元代穆斯林墓碑,是从杭州的回回墓地移至凤凰寺的;一类是反映明代以来凤凰寺重修的四方汉文碑刻(一方为明代,三方为清代)和一方波斯文-阿拉伯文碑刻(为明代的制作),一直放置在凤凰寺内。还有一种清代卧碑,分为两块碑石,原来也是立在凤凰寺的,但是现在碑石似乎已佚,幸好拓片尚存,并不影响作为史料来利用。对于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凤凰寺的后一类碑刻资料还非常关键。这些碑刻资料不仅仅内涵比较丰富,且比较系统,展现出数百年间凤凰寺的历史;更是回族自身的资料,可以体现出当时回回人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的认识,难能可贵。碑刻资料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是其中细节的讨论尚不够充分、综合的研究也有待深化。 两类史料,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结合以上两类史料开展讨论,则是现阶段深化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必要途径。 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专门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不管是专题研究还是跨时代的通贯的叙述,都有不少。早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末光绪年间杭州人丁丙所编纂的《武林坊巷志》,书中专列有“回回堂”一目,收罗了有关凤凰寺的历史文献达18种之多,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3]而深入的现代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年的西方学者。1911年,英国学者安格内·史密斯·路易斯(Agnes Smith Lewis)出版《记载杭州一座清真寺重修的一方1452年的石碑》一书,公布了凤凰寺明代波斯文-阿拉伯文碑的拓片和录文,并予英文翻译。[24]1913年,法国汉学家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ère)在《穆斯林世界评论》期刊上发表了名为《杭州伊斯兰教》的长文(共84页)。[25]此文汇编了有关杭州伊斯兰教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杭州伊斯兰教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一种重要的早期研究文献。全文包括六个部分:1、回回桥,2、八间楼,3、马薛里吉思,4、大清真寺及其碑刻,5、其他的清真寺,6、穆斯林公墓。以“大清真寺及其碑刻”这一部分为主,占据了文章的主要篇幅。其中详细介绍了凤凰寺的现状,并翻译了凤凰寺的全部碑文;所附凤凰寺的平面图和照片,则反映了凤凰寺在清末的保持状况,还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每一部分之后的注释和文献则是由慕阿德(Arthur C. Moule)提供的。总之,此文可以视作杭州伊斯兰历史研究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微席叶(1858-1930年),全名Arnold Jacques Antoine Vissière。精通汉语,1882-1899年间长期驻在中国,从事翻译工作。1899年回到法国,开始在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主持汉语讲座,直到1929年。同时还兼任法国外交部汉文总翻译。[26]1906-1909年,微席叶参加了由法国多隆(d’Ollone)少校带领的调查团(Mission d’Ollone)对中国西部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回族的调查。后来出版了四卷本《多隆调查团报告》,微席叶承担了其中第二卷《中国穆斯林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Paris: Ernest Leroux, 1911.)的主要撰写工作。同时,他还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伊斯兰教论集》(Études Sino-Mahométanes, Paris: Ernest Leroux, 1911, 1913)。[27]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年)则出自一个知名的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传教士家族。而慕氏家族与杭州有着极大的因缘,慕阿德的父亲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年)和叔叔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1836-1918年),都在杭州等地传教,也都有关于杭州以及浙江的著作。慕阿德就出生在杭州,本人也是一位传教士,同时还是一位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学者。[28]慕阿德和伯希和(Paul Pelliot)共同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29]他还为此书作过一些零星的注释,后收集在一起以《行在:有关马可波罗的几个注释》一名出版。[30] 此后的近一百年中,有关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凤凰寺,包括凤凰寺的历史和建筑,凤凰寺保存的与凤凰寺相关的碑刻和与凤凰寺不直接相关的穆斯林墓碑两大部分。关于凤凰寺的建筑,刘致平先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31]中的叙述影响比较大,但是其中可议之处亦复不少。只是有关建筑时代、风格等具体的认识,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同时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杭州、凤凰寺建于何时等问题的分歧也一直存在。其次,则对于元代杭州伊斯兰教、杭州清真寺、杭州回回人物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多。特别是元代杭州回回人物,如江浙行省的回回高官沙不丁、乌马儿,回回文士萨都剌、赛景初、丁鹤年等,元史学者多有探讨。早在1923年陈垣先生在《国学季刊》、《燕京学报》首次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便利用大量的元人文集资料,深入讨论过寓居杭州的回回官僚舍剌甫丁、回回文士高克恭、萨都剌、丁野夫、丁鹤年等人的族属、生平、汉文化水平等问题。[32]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对元代各地伊斯兰教的研究中,也予杭州回回以及伊斯兰教一定的篇幅,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33]刘迎胜老师也对元代杭州回回人相关的多个问题作过深入的分析。[34]此外,白寿彝先生在早年发表的《两浙旧事》一文,对杭州伊斯兰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元末明初回回诗人丁鹤年、清初回回进士丁澎、八间楼和聚景园,发掘了不少史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35]郭成美先生对包括杭州在内的浙江清真寺的研究,发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并进行了合理推论。[36]不过,总的看来,以杭州伊斯兰史为主题,进行的系统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而最近几年,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表现之一,李兴华、马建春两位先生先后撰写了通论杭州伊斯兰教史的长篇文章和专著。李兴华先生的长篇文章《杭州伊斯兰教研究》除了对杭州历史沿革的简单介绍,主要从杭州伊斯兰教的地位、伊斯兰教的传入杭州、杭州伊斯兰教的历史概述、杭州凤凰寺、回回伊斯兰教墓地石刻与石亭五个方面进行叙述与讨论。[37]马建春先生的专著《杭州伊斯兰教史》主要以时间为纲,分为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展开,列为全书的主体五章,前附“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入传中国”一章,末置“杭州伊斯兰教的社会文化特征”一章,还有附录一篇——“杭州伊斯兰教碑铭与文献”。[38]表现之二,在杭州文史研究会的组织下,凤凰寺所藏元代穆斯林墓碑得到全面的整理,资料得以完整公布,2015年出版了《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一书。[39]碑文的释读,主要由英国学者莫尔顿(A. H. Morton)完成。[40]刘迎胜老师在此书序言中从国际伊斯兰碑铭学研究通例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书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我觉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元代杭州回回人及伊斯兰教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可靠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则为其他类似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碑刻的整理提供了典范。[41]而刘迎胜老师为此书所作序言,涉及到元代杭州回回人的一些重要的方面,在不少地方提出了他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一种有关杭州伊斯兰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凤凰寺所藏元代杭州穆斯林墓碑为线索,刘老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就元代杭州回回人的历史作了更为全面的回顾和分析。[42]表现之三,英国学者兰天浪(George Lane)[43]所编《凤凰寺与中世纪杭州的波斯人》一书于2018年出版。[44]全书正文由“简介:杭州和中世纪行在的波斯人社区”、第一章“早起伊斯兰和中国”、第二章“杭州和波斯人的行在的出现”、第三章“凤凰寺:礼拜寺或者说礼仪和致敬之寺庙”、第四章“聚景园”、第五章“行在的生活”、第六章“文化之都”构成,除了第一章为Chen Qing撰写外,其余均为兰天浪所撰。此书出版前,兰天浪所撰部分相关的文字已经翻译为汉文。[45]此外,还有两篇附录:附录一“墓碑:翻译和撰写”关于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出自莫尔顿之手;附录二“杭州伊斯兰碑刻”则主要是凤凰寺现存的一种阿拉伯-波斯文碑刻和四种汉文碑刻(另有杭州其他地方的三种碑刻[46]),由兰天浪撰写介绍、由Florence Hodous翻译。此书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元代杭州伊斯兰史的研究状况。 总之,杭州伊斯兰史在资料发掘和研究两方面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很多基本问题尚存争议,不少问题的细节也有待进一步丰富。 四、本研究的基本目标与研究框架 考虑到杭州回族-伊斯兰教史的史料总体而言并不太丰富,而前人研究成果则比较多,本研究确立了两方面的主要目标:一是以个人对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的通盘理解为基本的思考背景,立足可靠的基本史料,完整而又简要地勾勒杭州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同时展现杭州伊斯兰历史的特色;二是进一步发掘史料,并在基本史料的解读和不同史料的综合分析方面多下功夫,尽量在某些专题方面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也基于史料尽量给出自己的意见,希望相较以往的研究能够有所突破,至少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看法或者新的解释。 关于可靠的基本史料。我认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凤凰寺碑刻,一类是以地方志为主的杭州地方史料。这两类史料除了可靠之外,还具有时间、人物等明确的历史信息,适合历史研究之用。所以本研究在多数的方面是以这两类史料来组织成文的。 关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我设想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有针对性地收集回族方面的史料,发现了清代后期的一部杭州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五功必要》和其他一些零星的信息;一是就一般的传世文献再加以收集,比较多地利用了方志文献和晚清民国初年的一些调查资料。 关于史料的综合利用。我选择的是数量比较可观、内涵比较丰富的三类史料:其一是凤凰寺现存的一批元代穆斯林墓碑,其二是有关凤凰寺重修的数种汉文碑刻,其三是历代方志有关杭州清真寺的记载。综合之后可以得出远较单一史料所得更为丰富的认识。 关于杭州伊斯兰历史的特色。我考虑到的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元代杭州回回人的活动比较多,留下比较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第二方面是元代以来凤凰寺大约八百年的发展历史,非常系统;第三方面是明末清初丁澎家族充分展现了回回士人家族的丰富内涵和特色。 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我将全书的基本结构设想为两部、四章。上部针对杭州回回人的历史,分为第一章、第二章两章,主要展现定居于杭州的回回人的历史状况,这是杭州伊斯兰教发展的基础;并选择史料比较丰富的明末清初丁澎家族作为专题进行讨论,列作一章。下部针对杭州伊斯兰教的历史,分为第三章、第四章两章,以清真寺、伊斯兰教宗教人士、伊斯兰教著作等要素为主;并单辟有关凤凰寺历史的一章,集中讨论凤凰寺本身的相关问题。从而设计全书四章的章题为:第一章《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与繁衍——人口、社区、墓地与风俗》,第二章《明末清初杭州回回士人家族——丁澎家族考析》,第三章《杭州伊斯兰教历史钩沉——清真寺、宗教人士、著作与教派》,第四章《凤凰寺——杭州伊斯兰历史的一个缩影》。四章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区分又有所联系。第一章、第四章以时间为纲进行叙述和讨论,第二章按照专题本身从资料到相关问题的辨析再到核心问题的归纳和讨论来开展,第三章则按不同的宗教内涵要素来分别讨论。 此外,本书还设计了四种附录:其一是凤凰寺汉文碑刻,提供拓片、原碑格式的录文(尽量按照原碑字形)、分段标点的录文(简体字)三种形式的原始资料,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避免本书行文中反复引用的麻烦;其二是有关杭州伊斯兰历史的一些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序跋文字;其三是明清方志等地方史料有关杭州清真寺的直接记载,按时代先后汇编在一起,条理比较清晰,容易发现问题;其四是杭州元代穆斯林墓碑发现和研究史的介绍。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