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毅生: 今天的沙龙题目是“瀛涯星槎,览胜杭州”,出自郑和下西洋时两位随从所写的书,即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和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瀛涯”指海外,“星槎”指远航,“瀛涯星槎”比喻中国对外交流。之所以说“览胜杭州”,是因为杭州在中外交流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较之于2016年举办的G20杭州峰会,亚运会的参与群体更多,它既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次人文交流盛会。谈到亚洲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各位老师都学有专长,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在亚洲,其中,中国可以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当代学者龚缨晏写过《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上,均有过中外交流,但中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对外交流标志性事件应该是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称之为“凿空”。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过程当中日益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他国家的文明也同样如此,只有交流才能使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丰富。举一个显著的例子,佛教原本产生于南亚,后来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并成为其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近代学者黎锦熙先生就曾以“吃饭”来形容中国本土文化消化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千余年的吸收,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现在向外国人介绍杭州的灵隐寺、飞来峰石刻,肯定会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但实际上这原本是外来文化。 
▲飞来峰石刻 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对外来文明有着开放、包容的特性与传统,在中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杭州的区位优势。杭州濒临大海,与海外各国交往具有先天优势。同时,杭州是大运河南端城市,并连通浙东运河,其水运系统四通八达。在中国古代,与陆路交通相比,水运具有很大优势。 其次,杭州在经济、文化方面具备优势。西汉时期,司马迁描述南方地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还是一番落后面貌,但此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杭州的兴起、发展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基本同步。隋朝时,正式立杭州;从唐朝中期开始,杭州逐渐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唐代白居易曾写下名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使杭州成为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到了北宋,宋仁宗赞扬杭州是“东南第一州”。新疆吐鲁番曾出土元代杭州崔家巷一家商铺的裹贴纸,这纯粹是一个商业广告,用来宣传其金箔业务,可见当时杭州的贸易范围非常广阔,商业非常发达。除雄厚的经济实力外,以西湖为代表的景观文化也是杭州吸引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唐朝中期开始,西湖经过整治,名气越来越大,来到杭州的琉球使者、日本使者以及欧洲传教士们游览西湖后都要写诗赞美。 说到文明交流互鉴,一般会分为两大部分,精神文明交流和物质文明交流。精神文明方面,宗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很多人对宗教的理解比较狭窄,其实宗教是古代中世纪文明主要和集中的表现形态,宗教教义、仪轨之外,还包含语言、文字、风俗、文学、艺术,以及科技、工艺等,而宗教教义也应属于哲学范畴。如印度佛教有五明之说,五明即5个学科,分别是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这是一个合格佛教徒必备的5种知识。工巧明,指的是工艺等技术知识;医方明,指印度的医药学,在唐代对中国颇有影响;声明,指语言、文体方面,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这篇文章中讲到汉语有四声,这在客观上是一直存在的,但中国人把声调正式确立为四声,是“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而创立此学说的人则以南朝齐时的周颙、沈约为代表,南朝齐时,士人受佛教影响很大;因明,指古印度的逻辑学,宋代之前,中国哲学深受印度佛教思辨性的影响,玄奘对此作出很大贡献;内明,主要指佛学教育。总之,世界三大宗教在杭州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从亚洲来说,起源于南亚的佛教,代表中亚、西亚文明的伊斯兰教,均在古代杭州有遗迹可寻。元代时,打通了欧亚大陆,疆域空前,欧洲的基督教徒也大量进入杭州。这些都是精神文明领域的交流。 物质文明领域的交流互鉴主要是经济贸易往来。在商品方面,世界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中国的三大贸易产品,即丝、茶、瓷就已经非常出名,广受欧亚各国喜爱,而杭州在这三大产品贸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人员往来方面,唐代往来杭州的胡商数量众多,甚至有很多胡商常居杭州。杜甫曾写过一首《解闷十二首》(其二)反映了这一状况:“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胡商从扬州出发,可以沿大运河到达杭州西陵(今西兴)。西陵是浙东运河的起点。很显然,在当时,大运河与浙东运河连通,而浙东运河的出海口在明州(今宁波),明州是中国三大对外交流的海港之一,通过明州可以到达海外。由此可见,在中国对外交流中,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杭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尤其是宋元及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逐渐超越陆上丝绸之路,杭州的优势更加明显。南宋时,因杭州是都城,外国使者来中国,目的之一就是到杭州。元代杭州延续了南宋时的繁盛,不仅有大家熟悉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像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他本身是一个旅行家,也在其游记中大赞杭州。还有一些外国使者是在其行程中路过杭州,比如清代乾隆时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明清时期的琉球使者北上京城,杭州是其必经之地。杭州和亚洲其他国家物质文明交流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杭州贴沙河上原先有椤木营、椤木桥,据记载,椤木是吴越国时期从日本进口的,说明日本与吴越国曾经有过木材贸易。直至明清,我国也有很多名贵木材和香料等都是从东南亚国家进口。 古代杭州与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也有很多例子,古代文献中对这方面的记载还是挺多的。《宋史》中曾提到中南半岛的交趾和真腊等都曾向南宋进贡。中国古代接受的外国朝贡物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珍禽异兽,从当代学者姜青青复原的南宋《咸淳临安志》京城图来看,当时的杭州城里有一个象院,豢养着一些交趾或真腊进贡的大象,主要作为朝廷的仪仗队使用,这在当时是非常稀奇的,引起了杭州百姓的围观。除了大象外,古代中国接受的贡物中还有狮子。狮子的中国化非常有趣,它原本是外来物种,在中国文化中逐渐演变为卷毛形象,而且有子母狮,比喻为太师少师,还有狮子滚绣球等。现在如果在外国看到一家商店门口放置一对狮子,挂着两个灯笼,大家肯定会下意识认为这是中国餐馆,因为门口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元素”,但狮子其实是在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才传入中原的。 所谓互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各种文明互相借鉴。古代中国对外来文明的借鉴,是在差异当中求一统。现在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满天星斗说”“多元一体说”,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再由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明和其他各地文明不断融合,然后进入夏商周统一时代。与此类似,中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似乎也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杨雨蕾: 我们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可能强调更多的是包容和理解,因为双方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也产生过冲突。但在亚洲地区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多呈现出一种融合的状态。尤其是东亚各国文明的互鉴,其实更是一种融合。正如楼老师刚才所说的,体现在佛教领域更明显。我上课时经常讲到《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归纳了唐代18种外来物品比如葡萄、葡萄酒等食物,樟脑等香料,还有植物、家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会下意识地认为它们原本就属于中国,但学习中外文明交流史之后,才了解这些其实都是外来物。
我个人认为,东亚文化圈的文明交流互鉴涉及到共性与个性的话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曾提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这是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些共性。“四大支柱”中,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汉字,汉字不光在朝鲜半岛、日本有很大影响,对越南的影响也非常大。我曾经去过越南首都河内,河内有一座规模很大的文庙,非常壮观。这是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也是汉字文化圈呈现出的共性。 楼毅生: 对,一般认为越南北方脱离中国,是从宋代开始的。这在《宋史·交趾传》中有记载。宋代中国人还把越南北方称为交趾,元明清则统称为安南。古代百越之地,秦汉时期设立郡县,被纳入中原王朝管辖,中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 杨雨蕾: 古代中国文化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就朝鲜半岛而言,古代官方文献,包括文人写作长期使用汉字,直到20世纪初日韩合并,朝鲜王朝覆灭以后,才逐步发生变化,文人越来越多使用现在的谚文。在汉字文化圈中,朝鲜半岛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这是中国文化东传的结果,与此同时,朝鲜也呈现出共性之下的一些本民族文化的个性。以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为例,中国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清,都尊崇朱熹的学说,尤其强调朱熹学说中的等级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而《资治通鉴纲目》传到朝鲜半岛后,朝鲜士人则非常重视朱熹学说中“正君心”这部分内容。其实朱熹本人也很重视这些内容,但他的这部分学说在宋代之后的发展中,逐渐隐没了,却反而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加强。 宋元时期,有大量使臣、商人等通过海上交通来往杭州、明州等地,宋朝在明州还专门设置了高丽使馆。明清时期,因为规定朝鲜使臣主要通过辽东半岛的陆上交通路线朝贡,再加上海禁,较少有朝鲜半岛文人来杭州,留下记录的则更少。崔溥、崔斗灿是因为遭遇海难,意外漂至杭州,并留下记录的朝鲜文人。根据崔溥的《漂海录》记载,他初到杭州时,中国正防备倭寇,对外来人员比较警惕,官方要先对他进行严格的审查与监视,在此期间他是不能随便出门的。他在杭州时,有些文人登门拜访他,虽然语言不通,但都会写汉字,双方可以通过笔谈的形式聊天。崔溥之前并没有到过杭州,但是他对西湖景观很了解,除了进出杭州城的见闻,还提到了没有亲眼见到的苏堤、白堤、涌金门等地。他当时住在杭州仙林寺一带,对周围的山川景物都做了描述。据统计,现存韩国的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的别集大概超过4500多种,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的《(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以及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的《韩国文集丛书》已经出版了不少,都是用汉字来记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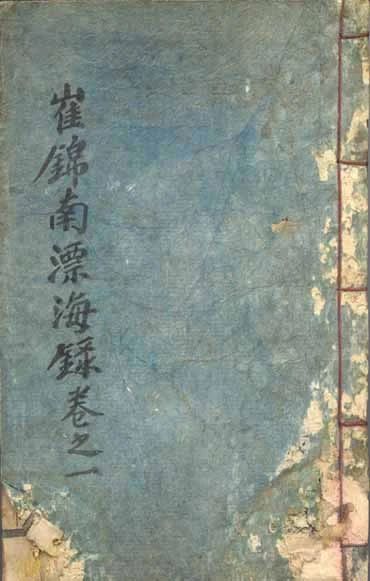
▲《漂海录》 楼毅生: 韩国有学问的人多多少少认识一些汉字,否则无法开展研究。 杨雨蕾: 是的,这些朝鲜王朝时代的别集中涉及到杭州的资料也有很多。虽然大多数作者其实并没有亲身到过杭州,但是其中有不少描述到有关杭州的诗词以及杭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景观,如林和靖与放鹤亭、梅妻鹤子的典故等等。 楼毅生: 以西湖为代表的景观文化在亚洲是比较有名的,尤其是在汉字文化圈。 杨雨蕾: 明代田汝成的著作《西湖游览志》传到朝鲜半岛后,朝鲜人就更加了解杭州,对西湖周边的灵隐寺、岳飞墓、林和靖墓等景点非常熟悉。以西湖为代表的景观文化除了自然之美,对朝鲜半岛士人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韩国有一位著名儒学大家李滉,就是退溪先生,他很喜欢梅花,就是受到林和靖梅妻鹤子典故的影响。再比如,朝鲜人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杭州的钱江潮,但对此却很熟悉,我们知道,钱江潮不属于西湖十景。他们尤其把钱江潮与伍子胥传说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钱江潮所具有的伍子胥忠义品格的意象。 杭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江南还包括江苏南部的苏锡常等地。除了江南文化,杭州其实还有浙东文化的特性。浙东文化在朝鲜半岛也产生过影响。 楼毅生: 对,截然分开肯定是不行。尤其是杭州作为省会,肯定会有各个地域文化的交集。 杨雨蕾: 崔溥从海上漂至浙江后,先到了台州临海,然后才沿着浙东运河来到杭州;崔斗灿漂流到定海,也是沿着浙东运河到杭州。崔溥、崔斗灿的作品中也有关于浙东文化的一些记载。 楼毅生: 在中国对外交流中,日本和朝鲜半岛与浙东海上交通频繁。除了朝鲜,浙东文化在日本也有影响。明清之际,中国学者朱舜水东渡日本讲学,在日本的影响很大,他就是浙东余姚人。 杨雨蕾: 杭州与朝鲜半岛文明交流互鉴的实例中,慧因高丽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北宋时期高丽王子义天到杭州慧因寺求法净源法师,对其所讲华严大义领受颇深,双方建立了深厚友情。义天回国后,双方多有书信往来,在净源法师建置慧因寺华严教藏时,把中国失传的华严经重新运回了杭州,这对华严宗典籍的整理保存和阐扬都起到关键作用,义天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慧因寺因为义天曾在此求法,被俗称为“高丽寺”,后来重修后名为“慧因高丽寺”。义天在杭州时还和上天竺寺的从谏大师交往颇深,向他学习天台教,回国后也有书信往来。杭州有两个著名的地方与朝鲜半岛是有关系的,除了慧因高丽寺,还有韩国临时政府遗址。 楼毅生: 是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进攻上海,在金九的策划下,韩国志士尹奉吉携带炸弹在上海虹口暗杀日军要员,引起日军大肆搜捕,金九等人被迫逃亡杭州,在杭州避难。此后还在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的帮助下辗转嘉兴平湖等地。所以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如果有韩国运动员来杭州思鑫坊、长生路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参观,应该会感到很亲切,就像我们中国人参观越南河内的文庙一样。 陈江明: 今天沙龙的关键词是“互鉴”,不同的文明之间当然是互鉴的,这是文明的属性之一。坚厚的长城、高峻的山脉、宽阔的海洋、人为的严刑峻法都阻挡不了异质文明之间的互鉴。历史上互鉴的途径很多,贸易、战争、外交、移民、传教、留学,等等。在近代以前,除了传教、东方主义的编码等刻意的文明输出行为之外,文明互鉴似乎都是无意为之、潜移默化的,像海绵吸水一样。如今全球史很热门,全球史探讨的就是各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早期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都是小人物、默默无名的人物,他们在无意中、偶然间推动文明之间的互鉴。如渴望发财的水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由此带来地理大发现。玄奘求法,也是偷渡去的印度。乾隆年间的东印度公司偷偷招募中国匠人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为关在那里的拿破仑服务。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中尽有这样的例子。文明互鉴的内容主要有两种:一是物质层面的,比如驯养的动物、家畜,植物种子,农产品、工艺品等。二是精神层面的,这又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技术性的,如工艺,实用性知识;第二类文化知识,如语言文字、文学、风俗习惯等;第三类是最高等级的,涉及价值,如宗教的传播、近代阶级斗争、革命思想的传播,等等。 以洲来命名文明,在学理上讲,并不合适。应该不存在“亚洲文明”这样的文明。奥斯曼帝国横跨三洲,算什么洲的文明?俄罗斯传统上属于欧洲国家,它的文明或文化,在欧洲却一直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但若泛泛地讲,亚洲文明、欧洲文明之类的说法似乎也讲得过去,也的确有许多人这样讲,姑妄言之吧。亚洲文明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世界意义,那当然要提丝绸之路对于欧洲的影响,蒙古成吉思汗和此后帖木儿的大征服对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世界的震动,还有古印度佛教的传播、西亚伊斯兰教的传播等。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文明,一直对周边民族、文明辐射影响着。但中国地域宽广,周边民族、国家众多,他者的文明也众多,有草原民族的文明、山地民族的文明、海洋民族的文明等,还有人将女真、满洲称为森林帝国的,如果是,那便是森林文明了。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互鉴很复杂,从中国中心观去看,且不说“中国”的概念变动不居,中国到底给周边文明带去了什么,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的。汉字、风俗、名物、政治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给予周边文明影响的内容。所谓的汉文化圈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的部分地区,至于对西南的印度,以及中亚、西亚的文明影响可能就显得模糊,这个说法不一定对,但至少可说,中华文化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与对西部民族文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如果从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对周边文明的影响,则更复杂。多年来,葛兆光先生致力于“从周边看中国”,茅海建先生近年来也着意考察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出发点也是如此。举个茅海建先生所说的例子。乾隆十五年(1750),缅甸贡使向乾隆皇帝进献一件写在银片上的表文(银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无人释读,所以没有人知道表文上写了些什么,直到法国学者白诗薇将之识读出来。缅甸是清王朝的朝贡国,是臣属之国,但这件银表文中缅甸国王对乾隆皇帝说话的口气令人惊奇。他自称“统治所有张伞盖的西方大国国王”,称乾隆皇帝是“皇兄日东王”,自己是“日出王”“皇弟”,彼此间是一种平等关系。这就颠覆了以往我们对朝贡国的认识。这种他者的视角不但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对周边文明影响的复杂性,由此也更能看出中华文明圈内他者文明的个性。 关于杭州在不同时期的亚洲文明交流中的角色与影响,楼老师及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专家。对清以前杭州的对外交流,我没有研究,了解也不多。我稍有了解的是琉球与杭州的关系。以前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时,我写过一篇《琉球使臣咏杭州》,因此接触了一些琉球朝贡中国的史料。前几年,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的学生就明清时期浙江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做过学位论文,研究得比较全面,史料挖掘也很深入,其中多有涉及杭州。自明代洪武年间起,琉球成为中国朝廷的朝贡国。朝廷规定琉球使臣从福州入境(最先是厦门),北上从蒲城县过仙霞关进入浙江江山境,然后经水路到杭州,再沿运河北上京城。杭州因为位于琉球贡道之上而与琉球建立了关系。琉球每两年一贡,明清五百年,可想而知有多少琉球王国的人经停杭州。琉球与杭州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琉球使臣写了许多咏杭州名胜古迹的诗,如康熙年间的程顺则《雪堂燕游草》,光绪初年的蔡大鼎《北燕游草》,其他还如《东国兴诗集》、蔡铎《观光堂游草》,等等,诗的数量很大,如蔡大鼎就写了数十首,一路走一路写。复旦大学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收录的琉球使节、随从等人的使华诗文集就有24种之多。他们写杭州风景名胜、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的诗文,与中国文人所写的没有两样,纯是中国味道。有了诗文的传播,杭州在琉球的形象自然是非常之好。道光十八年(1838),朝贡使团有个都通事魏学源撰《福建进京水陆路程》,其中说:“杭州府风俗,珍异所聚,秀美人文,商贾并辏,儒术为盛。土产:绫罗绸纱、黄精、布棉、龙井茶、杭扇、茯苓、昌化石、书石、锻丝、棉绸、藕粉、羊皮靴、杭纬、麦冬、铅。”一句话概括,杭州人文秀美、特产丰富,这是杭州在琉球国的形象。 二是琉球使臣与杭州官绅的交往。除“例谒各衙门”,参加欢迎宴会外,琉球使臣还与杭州文人多有交往。有几个杭州人曾作为随员、从客去过琉球,在出使期间收了一些当地学生,如道光年间的陈观酉,后来琉球贡使经过杭州还专门去拜访他,还有琉球人请陈观酉的儿子为他的诗集作序。康熙二十五年(1686),琉球使臣在返程经过杭州时,拜访著名学者毛奇龄,向他求书。毛奇龄在其《西河诗话》中记载:“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贡于还京时,护送官福建侯官县五县寨巡检胡奉至杭州,为使者买丝布什器兼觅《毛初晴论释西厢记》及《濑中集诗》于书林不得,有言予寓杭州盐桥,遂访予,予答之。见使者通姓氏,正使为耳目官魏俞,副使为正议大夫曾承都,其译字官蔡铛则谈议风生,俨然一吴门人,盛言其国多书籍,有五经四书镂板并子史诸集,即近代名人诗文新旧俱备,其搜初晴诗有以也。且道汪春坊舟次册使时,文采风雅至今国人皆思之,为勒石中山王府前。其从人十许中,有少年黝发被颊皙白似幼妇,远立而睇子曰:‘闺中有渡海者乎?’曰:‘无有。’即回指其人曰:‘此牡也。’盖逆知予所询在此人矣,其敏如此。又曰:‘中山妇渡海不利,即中国妇亦无渡海至中山者。’”琉球使臣与杭州文人的这种交往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三是杭州人作为册封使或使节的随员、从客出使琉球。杭州与琉球的交流是双向的,不止琉球人来杭州,杭州人也去琉球。道光十八年(1838)翰林院编修、钱塘人高人鉴作为副使,与正使林鸿年,持节捧诏至琉球,写有奉使日记。有清一代,有4位杭州人作为册封使的随员或从客前往琉球。这几个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如康熙三年(1664)的吴燕时,是一名太医;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徐傅舟是琴艺大师;嘉庆五年(1800)的王文诰擅长诗画、长于考订;道光十八年(1838)的陈观酉,诗画都很有名。这几个人到琉球后,当地人纷纷前来求教。他们的弟子中有人成为官学生,到北京国子监就读。中山王专门请徐傅舟弹琴,徐氏与琉球贵公子相互唱和,传授琴艺,法司蔡温为之写下一篇《琴艺》。 杭州与琉球的关系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研究资料基本具备,如《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高津孝、陈捷主编,共3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30册,鹭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2辑20册,鹭江出版社2015年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等,琉球王国的家谱在日本也已出版,获阅也不难。 马娟: 元朝时,由于打通了中西之间的海、陆通道,所以当时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是非常多的,而且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期到达中国,他在书中把杭州称为“行在”,对杭州的记载非常详细。继马可·波罗之后,14世纪40年代,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环游世界,他从摩洛哥出发,到达德里,然后从德里通过海路经广州、泉州、杭州到达北京,之后又去了非洲、西班牙,他对去过的这些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杭州的状况,书中提到杭州城里的居民都是分区居住,有犹太区、汉人区、穆斯林区、军人区、行政区等。穆斯林聚居区中的布置与伊斯兰国家是一样的,这些穆斯林对伊本·白图泰十分热情,请他吃饭,并赠送礼物和金钱,这使伊本·白图泰非常富有,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杭州的穆斯林财力较为雄厚。游记中还记录了一个叫奥斯曼的埃及人,在杭州开了一家医院,当时伊斯兰的医学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除了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元朝时还有一位传教士、旅行家鄂多立克也来过杭州。鄂多立克记载了杭州的一些情况,他说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客栈,他还提到杭州的管理方式,并且以此作为交纳赋税的依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阿伯尔费达(1273—1331)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地理书》中提到杭州西湖。波斯地理学家穆斯塔菲·加兹维尼(1281—1349)写过一本《心之喜悦》,书中也有对杭州的记载,有意思的是,他也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书中提到了杭州,他这本书目前只有英译本,没有汉译本。他在书中记载了杭州的民俗,提到杭州居民吃米、鱼较多,吃面和羊肉较少,而且羊肉很贵,这些记载比较符合当时杭州的实际情况。 关于杭州的域外文献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叫裴哥罗梯(Pegolotti),他写过一本商业小册子,译成汉语就是《通商指南》。这本小册子其实是从佛罗伦萨到中国经商的路线指南,他从未来过杭州,但却在小册子中提到了杭州。他还提到中国每个商业发达的城市都有仓库,方便商人存放货物。总之,中世纪的一些西方人,不管有没有来过中国,都对杭州有一些比较准确的记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杭州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大都、泉州一样,是中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杨雨蕾: 这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包括“飞马亚洲”地图中杭州被称为“行在”,也对后人的记载有影响?黄时鉴先生曾在《飞马尾上的杭州》一文中提到过。 马娟: 我觉得不一定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因为要考虑《马可·波罗游记》的成书年代。另一方面,波斯文对杭州的称呼是波斯语根据汉语的音节音译的,比如阿拉伯语中把杭州拼成类似于“杭府”的发音,广州就是“广府”。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因为穆斯林与中国的关系比欧洲更近、更密切。 在杭州的穆斯林是很多的,他们在杭州有自己的聚居区,而且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段。杭州现今保留下来的穆斯林建筑,以凤凰寺最为有名,凤凰寺的建造年代无法准确判断,但元代回回大师阿老丁重修凤凰寺是有明确记载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提到过此事。而凤凰寺所在的杭州御街,在当时是非常繁华的地方。 楼毅生: 据说凤凰寺礼拜堂的屋顶是元代的,其他大部分建筑都是后来修建的。元代穆斯林在杭州的遗迹还有一处是聚景园,即现在的“柳浪闻莺”景点,位于清波门外,南宋时期是皇家园林,至宋末元初已经荒芜了。在古代杭州,西湖属于城外,所以聚景园就在城墙边。20世纪20年代拆除城墙、建造环湖马路时,在聚景园遗址发现了很多穆斯林墓碑,其中最考究的就是卜合提亚尔墓,墓葬最初出土时,上海《申报》报道过,后来政府把墓葬保护了起来。为了释读碑文,请了一位阿訇,他判断卜合提亚尔应该是唐宋时期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先贤。现在经过重新释读,可以判断出应该是元代来到杭州的穆斯林官长,其坟墓已重修。 马娟: 元朝时,这片区域被杭州比较富裕的穆斯林买下来作为墓地,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在此发现的碑刻很多遗失、破损了,现在只有20多块保留在凤凰寺。后来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些碑刻进行释读,出版了《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最近出版的《波斯湾航海家在中国港口的遗迹(广州 泉州 杭州)》一书的作者乌苏吉也是当时整理释读杭州凤凰寺墓碑的学者之一,他的这本新作中写到了杭州,对在杭州发现的阿拉伯和波斯碑刻又进行了一次释读。除了这些域外文献,中国的汉文史料对杭州的穆斯林也有记载,大家熟悉的就是陶宗仪的著作,其中曾记载杭州城里有穆斯林举行婚礼,汉人觉得很新奇,爬到屋顶上去看,结果把屋顶压塌了。可见当时的杭州有很多外来人口居住,杭州在域外的知名度也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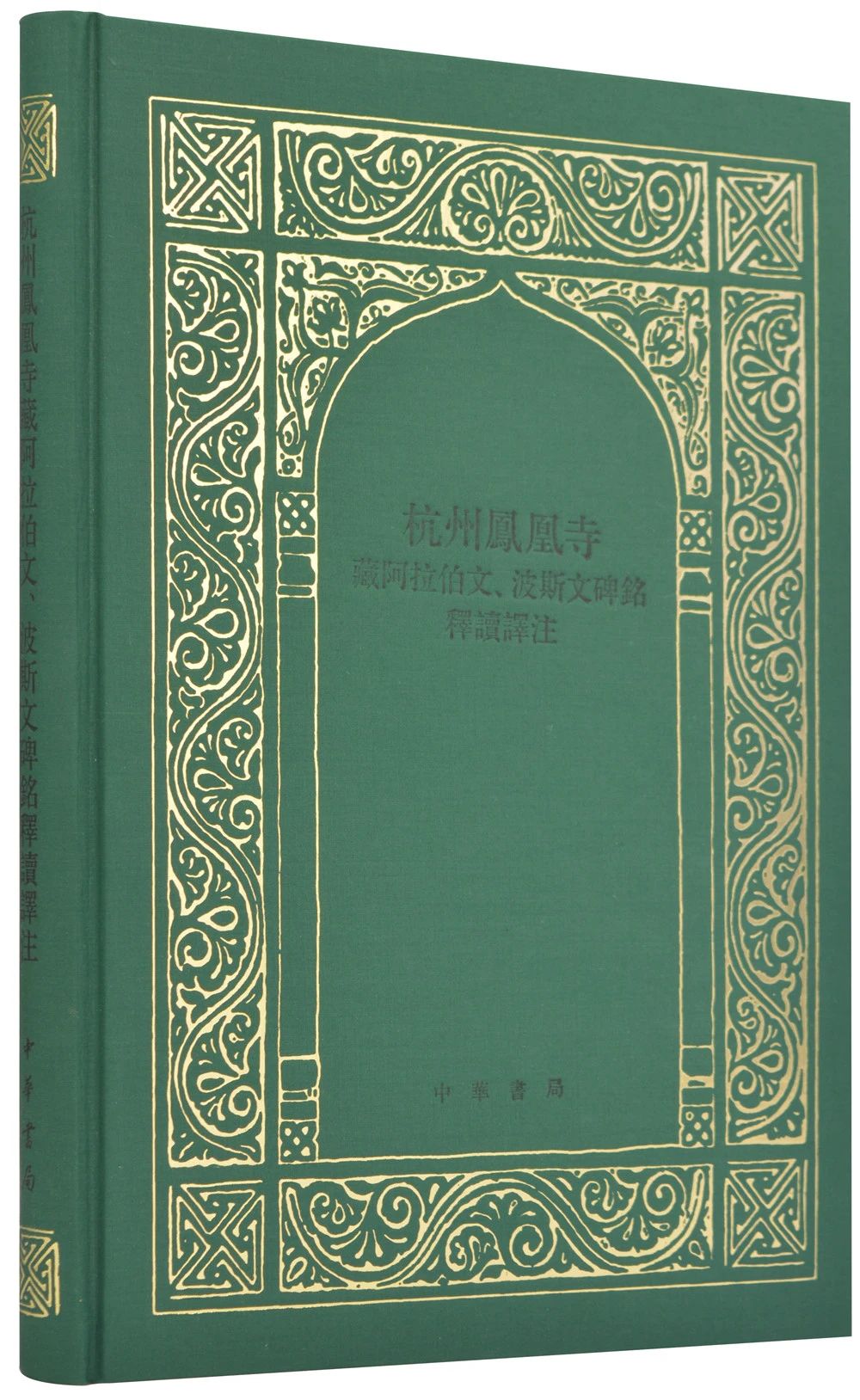
▲《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 江静: 一种说法认为,亚洲文明有三个文明圈,分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圈、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文明圈和以阿拉伯为代表的西亚文明圈,我个人对东亚文明圈相对比较了解。我认为东亚文明圈有几个特点: 一是相对于物质文化的交流,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影响更为深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韩三国共用汉字,也因为此,三国间的书籍交流非常频繁,形成了所谓的“书籍之路”,不仅是中国的书籍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直接影响了后者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建设,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籍也曾回流到中国并产生影响,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二是东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精神。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例,隋唐开始,直到明朝晚期,有大量的日本僧人来华求法。对于这些前来求学的异国僧人,当时的中国僧人是以一种十分开放和平等的态度对待的。例如,来华的日本僧人中,有不少就在元朝的禅寺担任首座、书记、藏主等僧职,甚至还有升到住持位置的。中国传统禅寺内,首座主管修行,可以代替大和尚说法;首座下面是书记,管寺院文书;再往下是藏主,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这一现象说明了元朝政府和佛教界对异域僧人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同时也说明当时日本僧人的修行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还体现在,即使是元朝与日本战争期间,日本商船还可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忽必烈并没有因为战争而驱逐日本商船,而且,宋元两朝,日本僧人来到中国,还时常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 三是东亚各国的交流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互动性,彼此学习,互相借鉴。以中日交流为例,早期以日本学习中国为主,之后两国双向学习。比如诗文的交流,元天历二年(1329),应日方邀请,径山寺首座明极楚俊偕弟子等人东渡扶桑,同行的还有归国日僧数人。途中,一行人吟诗唱和,留下诗作数首。这些诗,描绘了大洋“万里无山天水横”“烟波浩荡碧沉沉”的壮丽景色及海舶“截破洪涛万叠横”的恢弘气势;记录了海船出港的时间、路线、航行时间及沿途经历;表达了作者们漂泊大洋时的孤独、船舶停滞不前时的焦急、遭遇惊涛骇浪时的惊恐、即将到岸时的欣喜等心情;反映了当时中日禅僧以诗文唱酬为风尚的交游方式,以及日本僧人对汉诗创作的自信。抵日后,明极楚俊将这些唱和诗抄录为一卷,制作成卷轴。该卷轴一度为京都大德寺所藏,江户时代散落至各处。这些唱和诗文,是中日僧人文化交流的见证。当时还有不少日本人创作的诗文也传到了中国,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就收录了日本人创作的《咏西湖》诗,并称日本人擅长作诗。这是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在技术层面也有,比如螺钿制作技术的交流。到了近代,则以中国学习日本为主。 楼毅生: 还有折扇,是宋代从日本传入的。 江静: 在东亚文化圈的共性和个性方面,关于共性,除了杨老师提到西嶋定生的四大要素,汉字、儒教、律令制度和佛教,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又提出了两点,教育和技术,但日本没有采用科举制。而汉字、儒教、律令制度和佛教这四大要素对不同国家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比如儒学对朝鲜半岛影响更多一些,而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更大。同样是儒学,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中国的儒学比较重视“仁”,日本比较重视“忠”,朝鲜半岛比较重视“义”。所以同样的要素在东亚各国也体现出了共性和个性。 关于杭州在不同时期的亚洲文明交流中的角色和影响,我记得20年前去日本的时候,有人问我来自哪里,我用日语说来自杭州(こうしゅう),他们以为我来自广州,因为广州和杭州在日语中发音是一样的。然后我说是上海旁边的城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湖叫西湖,很多日本人就明白了,这说明日本人对于杭州城市本身的认识可能还是比较晚的,但对于杭州的很多景物,比如西湖,是很了解的,这可能受到白居易、苏东坡的影响。 《白氏文集》在白居易在世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对于杭州的认识可能来自于钱塘江、西湖,之后可能是白堤、苏堤、六和塔、保俶塔。为什么《白氏文集》在日本很受欢迎?除了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等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浙江大学学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陈翀),作者提出在日本,白居易被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而《白氏文集》也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和《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白居易被视为文殊菩萨的说法在今天的日本还有,相关研究也不少。 白居易在杭州待了近两年,留下了150首左右的诗,不少与杭州有关,所以日本人对杭州有特殊的感情。此外,日本的五山文学等日本人创作的汉诗也多有提到江南,这里的“江南”包括杭州、宁波等地,所以杭州风物在日本文献中出现是比较早的。此外,杭州也是来华日本人途经或活动的重要场所。从后期遣唐使开始,日本人来华采用的一条主要线路就是横渡东海,从明州上岸,经杭州到长安,遣明使也要先到宁波,然后通过浙东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沿京杭运河到北京。杭州除了是北上途经之地外,也是日本人在中国活动的重要场所,尤其是求学。最典型的是两个时期,一是吴越国时期,五代时中日之间的交流就是在吴越国和日本之间。我在《日延与吴越国时期的中日交流》一文中提到,在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中,日本僧人日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受朝廷派遣,护送中土散佚的天台宗典籍来到吴越国,并在四年后携带钱弘俶造阿育王塔、唐代新修《符天历》以及千余卷内外典籍回到日本,并向朝廷上呈了在华日记。五代之后的宋元时期,特别是南宋时,中日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僧人和商人进行的。当时中国到日本的商人中,杭州商人很多,比较著名的是谢国明,他在日本被奉为神明。还有林和靖的后代林净因在元朝末年到了日本,成为日本馒头业的祖先。南宋时期,日本人到中国主要是在杭州和宁波两地活动,在杭州的活动更频繁一些,因为杭州有五山十刹中“五山”的三座寺庙,即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可见杭州既是日本人到中国的途经地,也是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杭州对日本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关于域外文献中的杭州,我认为域外文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写的、后来传到域外的文献,这类文献日本有很多,我曾编过一本《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里面收录的是现藏日本的我国宋元高僧的墨迹,内容包括法语、偈颂、赞语、序跋、书简、印可状、匾额题字等,这样的文献至少有一千多件,我只收录了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的160余件;另外一种就是域外人创作的文献,比如日本的五山文学。五山文学种类很丰富,作者主要是禅僧,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知识阶层就是僧侣,即五山僧侣,所以他们留下大量的诗文。五山诗文集里有大量关于杭州的记载,这方面可以挖掘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西湖诗。另外,还有日本人来到中国后留下的很多记载,其中有大量关于杭州的内容,比如宋代有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明代有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等入明记。 楼毅生: 《西湖游览志余》里讲到一位日本使者路过杭州写了一首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著功夫!”有机会可以把日本文献中关于杭州的内容辑录下来,汇编成书,这会非常有意义。 江静: 这首诗也收录在前面提到的《殊域周咨录》中,作者虽然不甚明确,但应该是入明僧,日本遣明使中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入明僧担任的,因为那时日本的知识阶层就是僧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图片型文献,如西湖图,西湖图也不只有绘在纸上的,还有绘在屏风上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以后可以继续挖掘的。 楼毅生: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改革和开放,我觉得改革和开放是成正比的,深入改革必须扩大开放,扩大开放必然要深入改革,文明互鉴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在杭州的对外交流史上,G20峰会绝对是一个里程碑,但就普及性而言,亚运会则是全体亚洲人民的大联欢。从杭州的对外交流、文明互鉴角度讲,亚运会也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相信各位老师谈到的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对杭州对外交流史的进一步研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