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唐代的“村正”制度以後,趙宋國家未再推行過以“村”作為某一層級名稱的全國通行之鄉村基層管理制度。存世宋元地方志對鄉野之“村”多有著錄,其書寫方式有不同的類型。其中有些地方志常見在一鄉之下僅著錄寥寥數“村”,完全不符合當時自然聚落之常情。若從地域性的鄉村基層治安組織耆分在北宋前期的具體展開去觀察,可以發現,那些寥寥數“村”者,應該就是作為每一耆分“主村”的鄉野聚落。由此可知,耆分就是趙宋國家繼承前代村制,為了管理鄉村聚落所設置的基層組織。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古代鄉村聚落形態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自從唐初推行在鄉村聚落中設立村正的制度以後,儘管歷代各地實際的聚落名稱仍不免名目繁多,不過“村”從此成為了最通用的名稱,無論南北都是如此。[1]與此同時,儘管自唐以後,及至清末,歷代未再推行過以“村”作為某一層級名稱的全國通行之鄉村基層管理制度,但官府的行政管理中,“村”也無疑成為了指稱鄉村聚落的通用詞。 唐代以後不再設置村正,並不意味著帝制國家放棄了對鄉村聚落的管理。有論者指出:“唐代的村是一级以地域为基础的正式的乡村行政组织,地位非常重要,设有村正和村长。……然而到了宋代,遍览史籍,却不见任何关于宋代设有村正或村长的记载,村不再是一级行政组织。”[2]如果說這是指未見宋代有直接以“村”為名的正式行政組織,此論甚是。但如果以為宋代不再設置以鄉村聚落為基點的管理制度,則此論或可再議。 事實上,聯戶組織與鄉村聚落各自相對獨立、相輔相成,應該是秦漢帝制成立以來的傳統。[3]《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載: 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4] 對於此條文字,仁井田陞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集中考訂。他認為前條當分別出自武德令、開元七年(719)令與開元二十五年(737)等令。其中“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一條,當出自開元二十五年令。“在田野者為村……不須別置村正”,自然也與坊正條一樣,出於同一令文。[5]實際上,這一則文本包含不同時期的令文,其所反映的制度細節的前後演變,不必细論,但唐廷構畫鄉村基層組織的制度框架當形成于王朝的前期,應該可以肯定。關於坊正、村正這一條,存世文本雖出於開元二十五年令,或當有更早的制度依據,似亦可以推斷。 細讀前引令文,顯見的是,鄉里與坊村之正長的設置,立制原則是有差別的。前者完全依據人戶數而設,其職責雖有“檢察非違”等語,要點無疑在於“催驅賦役”。所以無論在組織架構,還是在職責義務,都屬於聯戶組織,其編排也常因人戶數量增減而變動。這也是後世文獻所載“編戶××里”[6]、或者“圖即里也……戶有增減,則圖隨之為多少”[7]現象的原因。 而後者,“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甚至沒有提到其人戶的數量規模。很顯然,城區不同地塊之間人戶疏密相差極大,很難以戶數多寡來劃分。城區裏同時也有鄉里組織來聯比人戶,因此坊區屬於地域性組織,坊正作為這種地域性組織的頭目,職在負責地方治安,“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與職在“催驅賦役”的鄉里組織頭目各有側重。 與邑居者的坊及其頭目坊正相同,唐廷對於鄉居者同類組織的人戶數量,雖然也有規定,但可以在十戶到百戶之間浮動,相當寬泛。若超過百戶,增置村正一人;聚落過小,不到十戶,則附入大村,不再單獨設置村正。這顯見是為了適應不同的聚落規模,與鄉里聯戶組織一概以人戶數量來組建的原則明顯不同。總之,唐廷關於村正的制度設計,以聚落為基點,是相當清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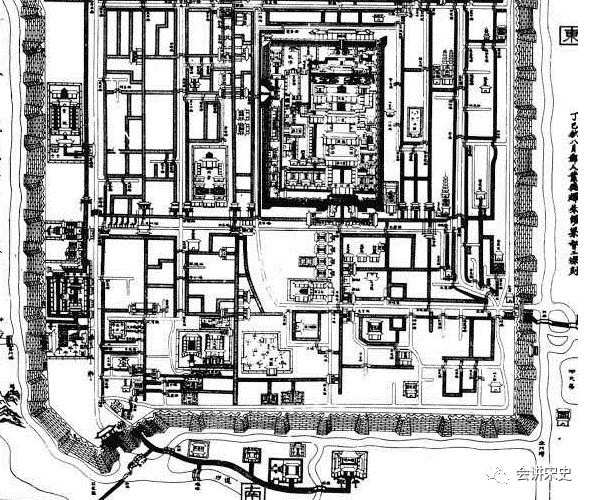
由此可見,唐廷關於社會基層管理組織的設計,有著聯戶與地域兩種相對獨立的組織架構。其一是主要負責“催驅賦役”的鄉里,由於其職責負擔與人戶規模密切相關,考慮到負擔與效率之間的平衡,鄉與里必須基本上依據人戶數量來組建。所以我們稱它為聯戶組織。儘管各地在落實中不免遷就聚落的具體情況而有所調整,但從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來看,鄉里是一種懸浮於聚落之上、以人戶數量為依據的組織。坊與村則不同,為了履行“督察姦非”的治安職責,就必須明確它的地域性。而且,由於地域、民風有異,治安事務也當有閒劇之別。相對而言,人戶規模倒反不一定是首要考慮的要素。在鄉村,落腳於人戶的聚居之所也就是順理成章了。在具體落實中,尤其是在一些聚落規模普遍較小的地區,由村正管理的“村”,不少可能都是由數個小村落隸附於某個大村落組成的“行政村”,也是可以想象的。[8] 那麼,如果我們略為拓寬思路,不一定糾結於是否直接以“村”為名,而是將觀察點聚焦於一般意義的鄉村聚落,由唐入宋以後,是否還存在某種與聯戶組織並行、以聚落為設置基點的地域性基層組織呢? 長期以來,學界討論鄉村基層管理制度,多聚焦於鄉里都保等聯戶組織。[9]聯戶組織是歷代專制政府從鄉村征賦調役的基礎性管理框架,因而無論是對於時人,還是今人觀察史事,往往都會將其置於首要位置。存世文獻所反映的,也聚焦於聯戶組織。不過,與聯戶組織並行的地域組織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而且,地域組織常常還是我們觀察聯戶組織演變蛻化過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另有其獨特的意義。 在中文文獻中,專文研究由唐入宋以後的聚落管理制度者,似尚未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東洋史學界曾对此有深入討論。代表性的論著有佐竹靖彥《宋代鄉村制度之形成過程》[10],以及柳田節子《鄉村制の展開——宋から元へ》等文。[11]佐竹靖彥認為唐代的村落制度至五代後周演變成為村團制,基本規模為一團設三個耆長,每個耆長管理一個村落。至宋初太平興國五年鄉管體系成立,耆長管理區域的範圍擴大,成為隸屬於鄉管的基層組織。他稱之為“鄉管耆制”的村落行政由此確立。柳田節子觀察的重點放在戶等、職役等要素制約之下鄉村制度的演變,她認為北宋中期以後,隨著鄉里制瓦解,鄉都制取代鄉里制,鄉村基層管理形成鄉——都——村逐級隸轄的層級關係,即所謂“鄉都村制”[12]。後來她又撰《宋代の村》一文,補充論證前文的觀點。[13] 不過前賢的這些討論也給後人留下了明顯可供深入的餘地。首先是他們似未能分辨聯戶與地域兩種組織架構的差異性與相對獨立性,總是試圖將它們納入同一系統,無論是佐竹氏的“鄉管耆制”,還是柳田氏的“鄉都村制”,都是如此;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歷史文本與其所反映的歷史事實之間微妙關係,辨析或有不足,例如常將地方志書中所載鄉、里、村等等名稱直接視同現實的制度設置,疏於揭示其背後歷史現象的複雜性。因此,他們的敘述不免與史實存在某些扞格之處。 也有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同一縣內,耆長的轄區和戶長的轄區範圍並不重合”[14]。但他們只是含糊地稱“耆是縣之下的專項行政區劃單位,凡歸耆長負責的各項事務均以耆為單位來開展”[15],或者“耆是一種獨立的專項行政組織”[16],並未能厘清耆的基本屬性,也就無法明確一些與之相關的史實。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試圖從地域性基層組織的視角,重新梳理宋代關於“村”的制度,也就是帶有某種行政管理功能的鄉村聚落。由於存世文獻的地域特征,文中涉及的主要是宋代的東南地區。 
二、自然村落的分布與規模 首先,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兩宋時期自然村落的概況。 人們聚居於鄉野,“應當追溯到文明的初生” [17]。學界對先秦以來鄉村聚落的產生與演變,已有相當豐富的學術積累。及至唐代,早期由“廬”“聚”“丘”等不同形式源起的、各地名目多樣而以“村”為通行名稱的鄉村聚落,已經遍布中原大地。進入宋代以後,隨著人口增長,村落的數量與規模則一步擴展。傅俊對南宋村落已有深入討論,[18]下文根據她的研究,主要對有關自然村落分布及其規模的情況,略作歸納,並稍予補充。 傅俊歸納歷史時期村落演變四個方面的基本規律:其一、村落演變蘊含著長期以來人類適應外在環境因時因地制宜的智慧,也蘊含著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的影響;其二、村落的形成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三、村落不僅是居住空間,也是一種歷史現象,不論緣起如何,其形態、結構、規模等等都不會一成不變、其四、村落數量的增多,即預示著空間分佈的密集化。所謂村落“空間分佈的密集化”,主要指它們人口增長等因素的推動下分化與擴散。她在上田信等人前期研究的基礎之上,主要利用民國《忠義鄉志》[19],具體展示了唐五代以後東南沿海地區鄉村聚落逐步開發的過程,認為唐五代多集中於山川的河谷地帶,至宋元時期則開始通過建造海塘向沿海地區拓展,到了明代,大多是在從前已有發展的、初具規模的地域內進一步推進開發。總之,無論是從幑觀、還是宏觀的視角看來,及至宋代,傳統中國聚落分佈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並奠定了後世發展的基礎。[20] 因此,尤其在東南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兩宋時人的一些觀察,就給後人留下了鄉村聚落繁密的印象。葉適(1150-1223)描述溫州瑞安縣,稱“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產,複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遊其鄰,村落若在市廛”[21]。若就當時的人口密度與經濟發展水平而言,位於東南沿海一隅的瑞安縣的確算不上“大邑”,葉適的文字或有為鄰邦延譽之嫌。儘管如此,“聚尤多”、“夜行若遊其鄰,村落若在市廛”這樣的說法,還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時人的觀感。相對而言,宋末元初人氏方回(1227-1305)描述浙西平原“吳儂之野,茅屋炊煙,無窮無極”[22],可能更接近白描。所以傅俊根據南宋後期的人口密度數據,推測“在平江府,幾乎每一平方公里上即有一個村落,村落——田地——村落,幾近相接;而在溫、臺地區,約每二、三平方公里亦有一村落”[23],當可以成立。她又分析對比東南常熟縣與西南瀘州的瀘川、江安與合江三縣村落分佈狀況,認為常熟縣東部、東南部的低地平原農業資源豐富,人口承載能力強於西部、西北部高地岡身地帶。同樣的,在西南瀘川縣的核心地區,開發相對成熟,村落分布狀況與常熟比較接近。但也有一些例證表明,漢戎雜居的複雜環境,可能造就大規模聚居的局面。[24] 
與此相反,在一些邊緣、或開發相對遲滯的地區,無論是村落的規模還是分佈密度,都與發達地區存在著較大差距。北宋時,即有如史書記載“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莾者十八九”[25],村落分布自然疏朗。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秋七月辛亥,有官僚上言,抱怨戶部責令諸路出賣官田期限太急,指出:“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疃之間,人户彫疎,彌望皆黄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産?”[26]反映了江東西、二廣地區農村聚落分布與二浙等地的明顯差異。兩年後,陸遊(1125-1210)從山陰縣出發,赴夔州通判之任,記其於九月十九日出嘉州後的景況,“自出城即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疃數家而已”[27],就可與江東西、二廣的記載相印證。 在這樣宏觀分布的格局之下,若具體到不同地區,或者某一地區村落的幑觀分布,又無疑更是疏密有別、差別巨大的。由於存世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對兩宋時期不同地區間村落分布狀況作全面具體的比較分析。關於北方地區,約略可作印證的有河東與河北地區兩例。 北宋至道二年(996)五月,知懷州許袞應命與使臣“相度開畎河水,澆溉人戶田苗並官竹園”事項,上言提到:“今據河內縣里正申超等分析到,緣河兩岸使水二十二村,二百二十五戶、澆得田土約六百八十餘頃,並屬省竹園在內。”[28] 按懷州位於黃河北岸,今河南平原的西北部,北依太行山,是傳統中原農業核心區,儘管這則文本記載的河內縣緣河兩岸22個使水村落,共計225個農戶,可能並未能包括各村所有的人戶,但當佔其大多數,可以想見。平均每村僅10.2戶,即便略作數據修正,其規模也不可能太大。北宋慶歷五年(1047),在與懷州相近的晉州,趙城、洪洞兩縣百姓爭奪霍泉河水源,據載當時“兩縣分析到霍泉河水共澆漑一百三十村㽵,計一千七百四十七戶”[29]。按霍泉河流域當屬河谷階地,開發也較早,但可能受水資源不足的制約,灌溉面積僅“計水田九百六十四頃一十七畝八分”,承載人口能力有限,村落平均規模僅13.4戶,與河內縣緣河兩岸22個使水村落的人戶規模相近。總之這兩個例證,對於當時中原西部河谷地區村落規模的一般狀況,是具有一定指示意義的。 在東南地區,尤其是丘陵地帶,文獻記載更多強調的往往是村落的差異性。例如建昌軍南城縣(今江西黎川縣)人呂南公(約1047-1086)有這樣的描述: 今之民居無常定也,有團落之間,雜數十百家者,有五里三里寂無一家者,有東西相望而阻以山川者,有懸絕之聚止於三兩家者……[30] 在呂南公看來,“數十百家”應該是村落規模的上限了。據洪邁(1123-1202)所載,“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地名上弓彎,……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31]。洪邁是否為了強調怪異事件之可怕而誇大了村落的規模,難以斷言。紹興末年,王之望(1102-1170)為四川總領,向尚書省上札子處置坑冶事宜,提到郪縣“于打銅村鑄造之家亦百餘戶……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農隙一二十戶相糾入窟”,一村的“鑄造之家”即達百餘戶,可知這應該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集村。吳江縣八赤村,“殆且百家”[32];南宋乾道三年(1167),周必大(1126-1204)閒居家鄉廬陵(今江西吉安)期間,所撰《泛舟遊山録》,記錄各地風光村落。他某次至蕪湖,“晚過西梁山,泊大信口,二百餘戶”[33],這個大信口當屬長江沿岸的巨村了。臨安府仁和縣泰村,居民“可三百户”,規模更大。[34] 中等規模的村落估計當在三五十戶之間。北宋元祐七年(1092),宋廷君臣討論保甲法,關於壯丁的差派之法,三省上言提到:“如一村有四十户合差壮丁之人,本村壮丁二人處,每一年輪四户,祗應十年輪遍,周而復始。”[35]這雖然出於假設之語,據此卻也不妨認為在時人的感觀中,“一村有四十户”大概是一般鄉村聚落常見的規模了。南宋孝宗初年仲並知蘄州回朝,其陛對劄子提到淮南地區“縣邑至為蕭條者僅有四五十家,大槩如江浙一小小聚落爾”[36],雖說稱之為“小小聚落”,其實應該是仲並感觀中江浙鄉村聚落的常規情況。特指性的記載當然更多。如乾道八年(1172),周必大從臨安由水路回廬陵,在池州境內,“(四月)戊辰早發池陽……十五里至何村,亦有數十家”[37]。陸遊長年閒居山陰鄉間,他描述自己的三山村“村北村南數十家”[38],也是一個中等規模的村落。[39]洪咨䕫(1176-1236)稱其家族聚居的於潛縣東洪村“無慮六七十家”[40],顯然是因為族眾的人丁興旺,自豪之情躍然紙上。 如果村落僅及十來人戶,時人的記述就不免強調其規模之小了。詩賦行文多以“三家村”之類詞彙來指稱它們,这當然並非指這些聚落一定只有三戶人家,意象而已。總之戶數若在十來戶之間,就是不起眼的小村落了。例如陸遊三山別業往西十餘里的湖桑棣村,在他的詩文中常被提及,徑稱“西村”,也稱“三家村”[41]。如《西村》“湖塘西去兩三家,杖履經行日欲斜”[42];又《乍晴風日已和泛舟至扶桑埭徘徊西村久之》“數家茅屋門晝掩,不聞人聲聞碓聲”[43]。實際西村“村村陂足分秧水,户户门通入郭船。亭障盗消常息鼓,坊场酒贱不论钱”,有售官酒的村店,所以陸遊得以從西村“醉歸”[44],還可以“今年四月天初暑,买蓑曾向西村去”[45]。所以西村儘管是個小村落,肯定不止三家而已。他又記述某村“北起成孤峯,東蟠作幽谷”,自注:“中有十餘家。”[46]這應該是與西村同一規模的村落。當時地方志描述廣寧橋旁小聚落,“居民鮮少,獨士人數家在焉”。因為只有數家,就直言其“居民鮮少”了。[47] 
在這樣的差序格局之下,籠統觀察,前文提及傅俊的估計,東南地區每一、或每二、三平方公里有一個村落,系就其密度而言;若就人戶數量而言,不同地區鄉村聚落的平均規模究竟如何?存世文獻所能夠提供的信息相當不足。
注释 [1]參見劉再聰:《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譚景玉:《宋代鄉村組織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9頁。 [3]參見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第328頁。他認為,“村”首見於三國,一般認為是漢代的“里”破壞後出現的,新出土的長沙三國吳簡發現大量與“里”並存的“丘”,證明在漢代也應是“里名”與聚落的地方性名稱並存。漢代的“里”大部分應是行政編制,不是行政村與自然村的合一,“村”的出現不能視為社會結構的時代性變化。 [4]杜佑《通典》卷三《食貨典三•鄉黨》,中華書局,1988年,第63-64頁。 [5]參見仁井田陞著,池田溫等編《唐令拾遺補》第二部《唐令拾遺補訂·戶令第九》,東京大演出版會,1997<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