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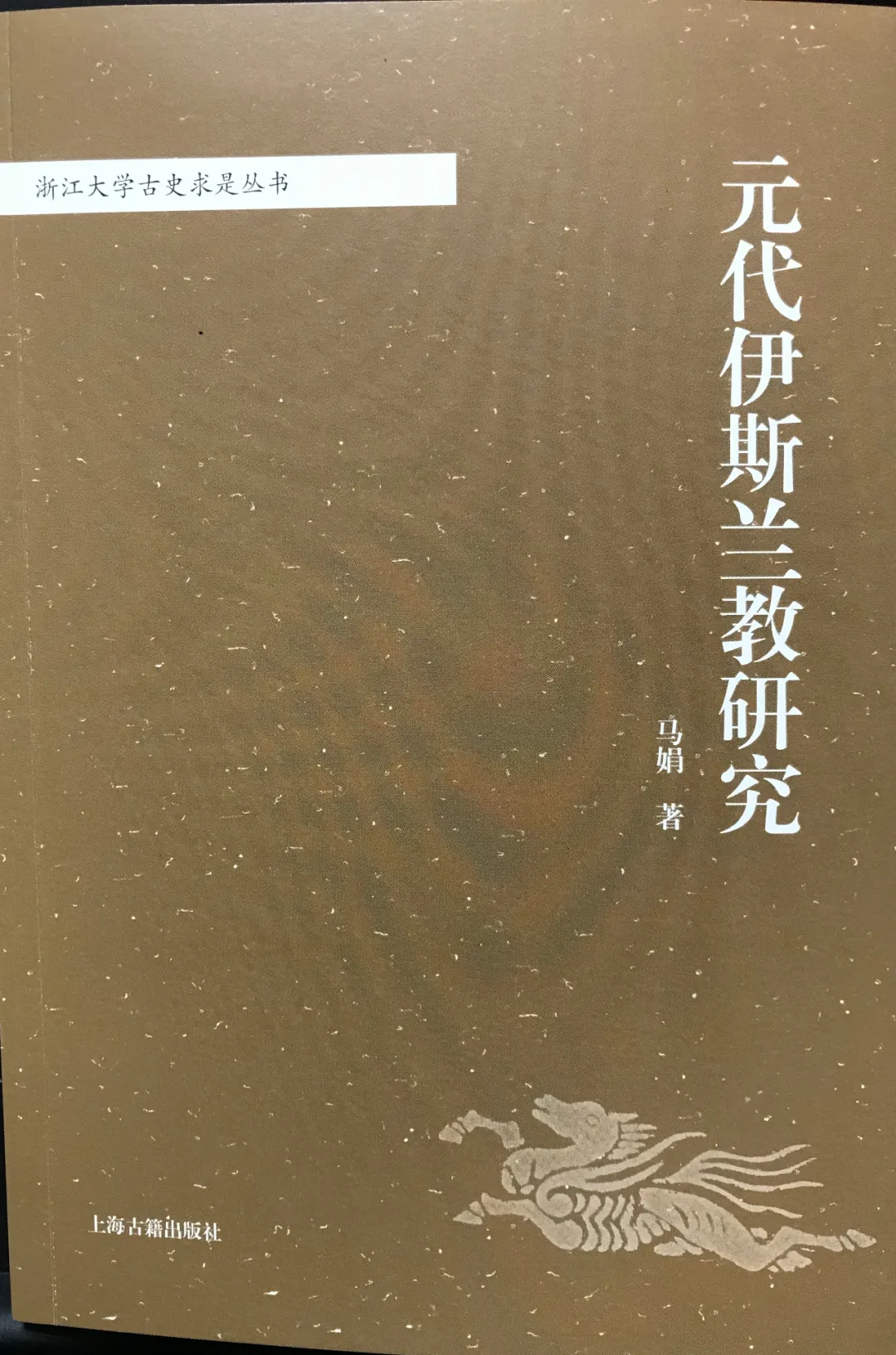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20-10 页数:254 定价:42.00元 装帧:平装 系列:浙江大学古史求是丛书 ISBN:9787532597574 作者简介 马娟,祖籍宁夏平罗,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求学于西北、东南、华北,访学于美利坚。师从马通、刘迎胜、李治安诸先生学习伊斯兰教、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元史等领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在《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元史论丛》、《回族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译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现供职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内容简介 本书从矛盾与调适的角度出发,在诸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专题研究,以期探明元代伊斯兰教在与他种文化,如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特别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矛盾中如何不断调适自身,从而与之相适应,最终完成中国化的过程。 目次 《浙江大学古史求是丛书》前言 序一 刘迎胜 序二 李治安 绪论 一、选题目的及其意义 二、文献介绍与前人研究述评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伊斯兰教的入华及其传播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入华 第二节 蒙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 第三节 汉文史籍对伊斯兰教与清真寺的称呼 第二章 伊斯兰法与蒙古法之间的冲突与调适 第一节 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之对比研究 第二节 主奴观念:矛盾产生的直接因素 第三节 调适:矛盾的消解方式及其社会影响 第三章 伊斯兰教与“汉法”的摩擦与调适 第一节 关于“汉法”概念的说明 第二节 耶律楚材与奥都剌合蛮 第三节 阿合马与汉人士大夫的关系 第四节 “天历之变”中汉人士大夫与倒剌沙之关系 第五节 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 第六节 回回人对“汉法”的态度 第七节小结 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佛道之关系 第一节 佛教僧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第二节 伊斯兰教与佛教之关系 第三节 道教文献对伊斯兰教的记载 第四节 伊斯兰教与道教之关系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 第一节 由来已久的矛盾传统 第二节 漠北汗庭时期的冲突与短暂的联合 第三节 摩擦中彼此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 结语 附录一 重立清净寺碑 附录二 重建怀圣寺记 附录三 元代回回人与汉人通婚一览表 附录四 蒙古诸汗后裔取穆斯林名一览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一 刘迎胜 桌前马娟副教授的这部《元代伊斯兰教研究》书稿,是她在当年在南京大学攻读学位时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书中所聚焦的课题涉及的时代,是“大航海”时代之前,来自异域的伊斯兰文明在中国落脚生根,逐渐成为中国本土文明一部分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元代。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中心区,其东面对浩瀚的西太平洋,南邻东南亚多山地带,西南为青藏高原,北临大漠,地理上自成单元。因而叙述中国历史,以中国本土为视角中心一直是学界主流。 虽然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往来不便,但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既没有自外于世界,也没有与其他文明相隔绝。亚、欧、非三大陆习称“旧大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中古时期,人们所讲的“世界”主要就是指“旧大陆”。从文明间差异的角度来看,“旧大陆”从东向西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大的文化圈: 1.“汉字文化圈”。主要指东亚的东部。分处东亚东北与东南的朝鲜、安南,以及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日本、琉球,都长期模仿中国,以汉文为书面语。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民族虽各有国家,但可以称“书同文”。 2.印度文化圈。主要指南亚次大陆。这里由于人口多,面积辽阔,历史悠久,影响越出其境,成为东南亚(包括大陆东南亚与海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文化母体,先后输出了佛教与印度教,梵文与巴利文。至今缅、泰、柬、老各国还使用“天城体”变形字母拼写其语言。 3.伊斯兰文化圈。包括内陆亚洲、次大陆北部、东南亚、西亚和北非。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这些地方有些被纳入版图,有些则深受影响,伊斯兰教取代当地原有宗教,成为居民的主要信仰。 4.拉丁文化圈。主要指近东和中、西欧。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之后,西罗马帝国影响下的中、西欧人民信奉天主教,主要以拉丁文为书面语。十字军东征后,基督教在近东重新生根。 在上述四个文化圈内,或文化圈之间,还有次文化圈,如东亚北部与西北部的草原地区,有突厥-蒙古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之内,又可大致以波斯湾为中心粗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受波斯的强烈影响,扩及次大陆北部与海洋东南亚;而西部则以阿拉伯文化为主,甚至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复盖比利牛斯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在伊斯兰文化圈的中近东,有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和信奉亚美尼亚教派的大小亚美尼亚,以及从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叙利亚教会,即聂思脱里教。 伊斯兰文化入华的问题,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讲,实质上是汉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圈的东部的跨文化交往。文明间的交往中,人员的往来一直是最重要和最引起注意的因素。不仅中国人民自古对世界其他文明有着高度的好奇心,他国人民也向往着东方文明,所以历史上梯山航海,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入华的外蕃人不绝如缕。 在中国,承载伊斯兰文化的主体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十余个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回族为最重要者之一。回族旧称回回,其主源是历史上入华的西域人后裔。如果将回回人的入华,置于东西交流史的大框架下观察,我们会发现,近代以前东西文化交往的主流曾有过三次巨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张骞之后,因西域被纳入中国版图,中印之间开启了以佛教和印度文化传播为中心的文化交流,这次潮流一直延续至唐代。第三次是郑和下西洋结束后,随着欧洲航海家、传教士的东来而开始的东亚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高潮。而居于两者之间的,则是宋元至明中期。 过去一些研究回族史的论著,沿袭明代部分回回学者的意见,将伊斯兰文化的入华上推至公元7世纪上半叶唐与大食帝国建立联系的时代。其实大食使臣的入唐,与伊斯兰教传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正如不能把张骞出西域视为汉文化传播到中亚一样。唐至宋前期,由于西亚和印度商人主导了印度洋贸易,开始有蕃商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聚居。但第一,这些入华蕃人并非全是穆斯林,第二,其人数很少。如果没有特殊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定居东南沿海的蕃客,会像历史上入华的祆教、犹太教、摩尼教徒一样,逐渐融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实际上,从存留至今的文献与回族家谱看,回回人在上溯家族历史时,极少能上溯至唐代的。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发动了征服中亚新兴强国花剌子模的军事远征,把北起宽定吉思海(Köl Dengisi,按今里海)、太和岭(按今高加索山脉)以北钦察草原(Dašt-i Qïpčaγ),南至波斯的广大地域并入大蒙古国的版图。成吉思汗回师时,大批臣服了蒙古的西域官僚、军队、工匠、学者、神职人员和商贾,也同蒙古军一道长途跋涉,来到中原汉地定居下来,又随着西夏、金、大理和南宋的征服,逐渐散布到中国全境。 成吉思汗逝世后,其后裔又陆续发动了几次军事远征,建立了地跨欧亚,疆域空前的世界帝国,不但汉地与与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处同处蒙古统治之下,中亚与西亚的穆斯林民众成为国家编民,且蒙古四大汗国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汉地与西域,分属于同出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忽必烈统治的蒙元直辖区(大漠南北、汉地、辽阳、云南与吐蕃等地),与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故而在蒙元帝国范围内,汉地与波斯的往来最为频密。而伊利汗国,则是元朝与地中海周边地区乃至欧洲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地理位置,使蒙古控制下的西域和东部伊斯兰东部,成为中国与欧洲往来的媒介。 这一时代,是回回人入华的主要时期。因而凡中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论著,莫不将重点置于元代。马娟的这部著作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研究中国与伊斯兰文化圈的交往,离不开考察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与大食有关的人物。唐代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往来的重要时期,也是汉文与非汉文文献所记内容与术语可资对照比定的起始时代。宋王欽若等編纂《册府元龟》几次记录了天宝初年一位与唐交往的大食重要人物屈底波: 1.(天宝三年)三月,安国王屈底波遣大首领来朝,幷献方物。 (天宝四年)七月,石国王特勤、安国王屈底波,并遣使来朝贡。……七月,安国王屈底波遣使朝贡。 2. (天宝七年二月)其月庚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上表曰:“臣乌勒伽言:臣是从天主普天皇帝下百万里马蹄下草土类。奴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事。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处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谨献好马一、波斯骆驼一、䮫二。如天恩慈泽,将赐臣物,请付臣下使人,将来冀无侵夺。 上述“异密屈底波”,即大食征服中亚之大将Qutaybah。张星烺先生多年前已指出: 异密屈底波即Emir Kutaiba之译音。异密者,阿拉伯语大首领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三0《大食传考证》作库退拔。洪氏不知西文,仅凭舌人口译,且未见《册府元龟》此节,故译作库退拔。中国古书对此人已有相当准确译名,吾人不宜新造名也。 此人即《旧唐书》卷148《西戎传·大食国》所记之“并波悉林”。“并波悉林”,不少学者释为“阿布·穆苏里姆”(Abū Muslīm),皆误。“阿布·穆苏里姆”(Abū Muslīm)为阿拉伯语,意谓“穆苏里姆之父”。张广达先生已指出,“并波悉林”乃阿拉伯语Ibn Muslīm之音。此名意为“穆苏里姆之子”,就是屈底波,缘因屈底波全名Qutaybah Ibn Muslīm,意为“穆苏里姆之子屈底波”。《通典》记其名前半,而《旧唐书》乃录其名后半。他驻守呼罗珊木鹿城(Merv,今土库曼斯坦谋夫遗址),杜环在其《经行纪》中称受命呼罗珊总督者为“大食东道使”。 汉文文献中提及不少宋代的自伊斯兰世界的入华商使,如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占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住海南之儋州(今儋县)”。这位占城人名蒲罗遏的首字“蒲”,日本学者田坂兴道认为乃是阿拉伯语Abū之(父亲)宋代音译,不少学者从其说,见回回人冠姓“蒲”者,辄以Abū当之。田坂氏的意见在多数情况下,应当是成立的。《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大食》提到“大食陀婆离慈”,这里的“陀婆离慈”,当为Tabrizī之音译,意为Tabriz人。Tabriz,元代音译作“桃里寺”等,今伊朗之“大不里士”。其子被记为“蒲麻勿”,当可还原为阿拉伯语Abū Mahmmūd,今译为阿布·穆罕默德,意为“穆罕默德之父”。但如一以贯之,有时也不一定适宜。如《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大食》所记:“上言大食蕃国蒲啰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诏蒲啰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这里的蒲啰辛当为阿拉伯男子名‘Ibrahim之音译(今译伊卜拉欣,相当于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亚伯拉罕),也即其音译名称中的“蒲”字应是其原名第一音节‘Ib-之音译。同样,《宋史》所记淳化四年(993)广州蕃长招来入华的大食舶主蒲希密的名字,可能也是‘Ibrahim之音译,即译名中的“蒲”字对应于原名第一音节‘Ib-。而回到前面提及的移居海南的占城回回人的名字“蒲罗遏”,其实,考虑还原为‘Abd al-Allāh,“真主之奴”(今通译为阿卜杜拉)似更合适一些。故而“蒲”字所对应的蕃人的原名,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文献中记录的宋时入华回回人的名字和术语,值得研究回回人历史的学者逐一推敲。如《宋史·占城传》提到的端拱元年(988)“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中的“忽宣”,当还原为Ḥusain,是什叶派穆斯林男子常用名,元代又译称忽辛,今译候赛因。周去非撰《岭外代答》提到“有吉慈尼国……其国有礼拜堂百余所,内一所方十里。国人七日一赴堂礼拜,谓之除幭”。除幭即Juma ‘的音译,今音译为“主麻”,意谓“聚会”,指周五穆斯林赴清真大寺聚礼。 元代由于许多回回人入居汉地,13-14世纪文献中出现的回回专名及术语大增,如理解译名背后之实义,有补于治史,例如《元史·成宗纪》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条下记载,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实录》、《宪宗实录》、《世祖实录》,成宗指出上述各《实录》中若干错误后,曰:“又别马里思丹炮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别马里思丹”与“炮手”间未点断,标点者似以为“别马里思丹”为“炮手亦思马因”之定语。且“思丹”对应于波斯语-stān,意为XXX地方,常作地名后缀,如Moghūlistān“蒙古之地”、Turkistān“突厥斯坦”,以及今之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亚几个国家的国名,故而这里似可理解为“炮手亦思马因”之故乡。实则大谬。其实“别马里思丹”应为波斯语bimāristān之音译,意为医院,应指回回汤药馆。这样,“别马里思丹”与后面的“炮手”之间应点断,整句文字应为“又别马里思丹、炮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成宗在这里是说,除了上面几处错误之外,回回汤药馆、回回炮手亦思马因与泉府司这种“小事”,无足挂齿,不应写入《实录》。 所以,伊斯兰文化入华研究,如置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探究,是大有可为的。 刘迎胜 2020年6月30日写于南京仙鹤山庄 序 二 李 治 安 马娟副教授的大作《元代伊斯兰教研究》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面世,嘱我作序。我虽然对伊斯兰教没有研究,但因杨志玖师的研究专长而耳濡目染,比较喜欢阅读包括马娟在内的相关论著,所以不假思索地应允下来。 我和马娟初次认识,是在2002年南京大学主办的“纪念韩儒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元代政治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这位来自宁夏的回族姑娘,已是刘迎胜教授的高足,正攻读蒙元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她参与会务组工作,非常热情周到地为与会学者提供帮助,还提交一篇有关禁止“抹杀羊”的蒙回文化冲突的论文,给人印象颇深。翌年,她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来南开从事博士后研究。杨志玖师上个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论文题目又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晚年曾全力撰写《元代回族史稿》。她原本希望来南开得到杨志玖师亲自指导帮助,更好地钻研探讨元代回回人和伊斯兰教问题。不幸的是杨师刚刚仙逝,留下了些许遗憾。出站后的十多年,她先后在兰州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也曾到美国等大学访问交流,锲而不舍地探讨这一课题。拜读这部字数不算多却是凝结作者近二十年心血和智慧的论著,看到杨师毕生致力的元代回族研究在作者笔下能够再创高质量的著作,颇觉欣慰与振奋。兹略叙感言,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元王朝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割据,还在于首次将塞外草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广袤地域纳入国家版图,首次实现了由华夏一统向华夷大一统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时期,多民族之间的杂处融汇,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都是规模空前的。时至元末,伊斯兰教普遍传播于中国,“回回之人遍天下”,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基本形成,这无疑是元代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马娟著《元代伊斯兰教研究》,恰恰专题探讨元代伊斯兰教与蒙古文化、汉地儒释道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异质文化间的矛盾与调适,以及在上述过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化。书稿的学术价值和“挑战”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作者所云,《元典章·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是元代伊斯兰法与蒙古法关系的最为集中的反映。还从文化宗教层面首次敏锐指出,回回使臣不食死肉的行为不同于其他使臣的骚扰行为,当是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使然。而“导致世祖颁布圣旨从而引起伊斯兰法与蒙古法之间矛盾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其思想深处的‘主奴观念’”。这是高屋建瓴的分析与揭示。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此种“主奴观念”在蒙元王朝的功用和历史影响,并在此补充阐明一二。尽管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人数众多的汉人、西域人过程中不得不允许“各依本俗”,不得不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但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背负的草原本位和“祖宗之法”等历史包袱颇沉重,有元一代“主奴观念”和 “普天率土皆是皇帝之怯怜口”俗,在蒙古贵族乃至蒙汉民众中根深蒂固,且大量潜移默化地积淀在诸色户计当差、游牧君主专制与汉地皇帝专制“纲常”交融等政治文化及社会关系范畴内。鉴于此,我们对蒙汉政治文化二元和忽必烈等行汉法似乎不宜估价过高,郝经 “附会汉法”之说,倒是值得足够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诸色户计当差及其相关联的臣民奴化等,或许是蒙古文化对汉地深层次或内在核心的社会影响,其效用又是服饰、语言、名字等外在部分无法比拟的。唐宋“与士大夫治天下“为代表的开明君主专制让渡于元明清极端君主独裁专制,或许恰是植根于此种社会文化土壤之中。换言之,作者有关“抹杀羊”背后“主奴观念”的揭示,也能够以小见大地透视蒙元社会。 作者还认为,元代回回人对伊斯兰教与“汉法”等异质文化的态度,存在世俗化、非世俗化和“中间派”三种类型。部分回回官吏、文人和平民饮酒与《古兰经》教义相悖,表明其宗教约束力降低,宗教色彩淡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此乃从饮酒切入,以展现伊斯兰教在汉文化占主导的国度传播之际的世俗化。又以乌伯都剌家族为例,从家族姓氏取名及供职翰林院教习亦思替非文字、使用波斯语、四代皆是回回族内婚姻等方面,阐明部分回回人与汉文化保持相当距离或隔膜的非世俗化。以哈只哈心之孙凯霖兄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有选择地吸收汉地文化的同时又保持其自身文化特质,“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这三种调适,当是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生根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向中国化迈进的重要步骤。关于元代回回人的华化和儒化,陈垣先生和杨志玖师等已有精深的研究,但毕竟都是侧重汉地文化及儒学等外部吸纳影响。作者首次从如何对待伊斯兰教和汉文化的碰撞以及回回人内部分化为三个“圈子”的层面予以阐释,可谓别开生面的真知灼见,从而将前人的相关探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碑》是现存传世的3种元代清真寺汉文碑志之一,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早的汉文碑。碑文所载的“吾回回人拜天”,“回回之人遍天下”,“惟回回人之为教,寺内无像,惟空一殿”等,提供了元代伊斯兰教传播的大量珍贵信息,故引起孙贯文、马生祥、姚大力、杨晓春等学者的重视和较多研究。杨晓春还依据寺记有关《古兰经》卷数常识性错误、书体四法和回回人名特色等可疑点,认为该碑记出自明人之手,假托元代之物。作者对此提出新的不同见解。指出卷数常识性错误主要是撰碑者非教内人所致,“真草篆隶之法”是以汉字的书写风格比附阿拉伯文书体。至于碑阴题名取汉姓者和取蒙古名者偏多,则是因为元后期回回人华化引起的汉名汉姓增多,以及元代不乏见回回人用蒙古名。进而主张《重建礼拜寺碑》实乃元代清真寺记,系元人所撰。此类争鸣与考辨,同样是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对元末伊斯兰教普遍传播和汉人语境解读等前沿问题,贡献颇多。 与一般研究元代色目人、回回人的学者略有不同的是,作者既可以从文化碰撞、调适等宏观层面开展出色的论证,又能够较多运用伊斯兰教教义和波斯文等语言学知识对一些较重要情节进行阐释或比勘,解决疑难,收到令人佩服的成效。譬如,考订《史集》中巴哈丁、失哈不丁和《元史》等汉文史书中的沙不丁实为一人;对元杂剧《回回迎僧》“咹啰和”与现西北穆斯林“安拉乎”,皆Allāh的音译;藉还原乌伯都剌四代人名波斯文对音,印证其家族之回回族属,首次对该碑“别谙拔尔”词汇作出新的语源解释,认为是由两个波斯语词汇构成,前者意为“使者”,后者为构词后缀,等等。所有这些工作,委实相当艰难,具有较强挑战性,体现了作者出类拔萃的史学功力和为此付出的甚多辛劳。 顺便说说此类高水平著作的评价问题。完成此类宏观论证与历史语言勘同并茂的著作,需要耗费超量的才智精力,其产出时间肯定比一般著作要多出数倍。按照目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以核心刊物论文计量等评价标准,诸如《元代伊斯兰教研究》肯定是落后吃亏的。然而,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辩证和实事求是地看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像《元代伊斯兰教研究》这样二十年磨一剑,高水平的宏观论证与缜密的历史语言勘同并茂,其学术价值往往是以一当三,甚至是以一当五,理应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肯定赞赏。如此,才不至于埋没或枉对真正的精品力作! 2020年7月30写于天津
李治安 后 记 古尔邦节那天,徐乐帅老师告诉我书稿的校样已印出。一时间,思绪如潮水般涌动,过往的岁月顿时鲜活地在脑海中闪动起来,仿佛早就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我曾经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自己“天生驽钝”。经过这些年对自己的审视,如今看来,这似乎是自谦过了头。平心而论,我并不愚钝,但懒散一定是真的。正因如此,这本书的问世才迁延至今。 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我在心底多少次感叹自己的幸运。硕士阶段投师著名学者马通先生门下,初窥学术门径。先生言语不多,却自有威严,以他的人格与学术魅力悄然影响着我,感染着我。先生对学生,对学术满怀热忱。如今先生虽已九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这与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的个性息息相关。在这里,我要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给我的鼓励,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硕士毕业后,我负笈南下,追随刘迎胜师学习。在这之前,我就听闻刘师通晓多种外语,是国际知名学者。我一方面为自己有这样的导师而骄傲、自豪,另一方面又非常忐忑不安,诚惶诚恐。但这种情绪在见到刘师本人后烟消云散。刘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我想象中的“名人”完全不同。记得我刚入校时,刘师告诉我说河海大学有家很好的穆斯林餐馆。寥寥数语,使那份温暖永远定格于心底。刘师不仅在生活上对学生关心有加,在学业上更是严加督促。他要求我定期阅读英文期刊,以扩大视野,同时了解国际学术动态。读书期间,刘师每周举行一次见面会,提问交流,践行“授道解惑”的神圣职责。刘师对于学生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他还带领我们走向远方的田野,走向民间,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教我们以“活”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刘师吃苦耐劳与艰苦朴素的精神。毕业后,刘师依然关心着我的学习与工作,每次有问题求助,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给予回答。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关于刘师见义勇为的报导。当时刘师参加完外事活动,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几个人殴打一人的事件,刘师见状上前制止,眼镜被打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再次感受到刘师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书稿修改之后,我请刘师作序。时值刘师赴德领取“洪堡研究奖”(Humboldt Research Award)。他在德国期间又认真通读了电子稿,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我避免了不少错误。如果说我在学业上有点滴进步的话,都与老师的悉心教导密不可分。这份恩情,永远铭刻在心。 我是何其幸运,在求学道路上又遇到了李治安师。李师不以我学识浅陋而欣然接受我跟随他从事博士后工作。在南开的两年,李师将我看作入室弟子,处处提携,使我感受了另一种不同的学术风格。李师在学术上对我鼓励有加,让我更加自信。书稿完成后,我给李师寄去一本,请他拨冗作序,老师很愉悦地应允,并在序言中肯定我的研究。这种肯定于我而言意义重大,是对我今后研究工作莫大的鼓舞,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此深深感谢老师的鼓励与信任。 去年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可谓损失惨重,多位史学前辈驾鹤西去,其中有敬爱的杨怀中先生、邱树森先生、洪金富先生、余振贵先生。杨怀中先生一直以来对我鼓励有加,本想请他为小书作序,未想这却成为永远的遗憾。邱树森先生是元史学界前辈,我初识先生还是在博二的时候,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先生对我的鼓励。洪金富先生走得很突然,我们本来约定秋天请他来杭讲座,却也成为难以实现的遗憾。我与余振贵先生虽未曾谋面,但余先生的著作给过我很多启迪。不能将小书面呈先生,何其憾也!谨在此致敬各位先生! 2013年是我人生中遭遇重大变故的一年。我亲爱的母亲金莲女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之家,一生饱尝人间疾苦,但她凭借她的坚韧、宽容与信心扛起了这一切,即使在病中,我也从未听她有过一句抱怨之言;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坚持自己上没有电梯的9楼;即使在病中,她仍然鼓励我克服工作上碰到的不顺。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普通的伟大女性。她离去后,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自传《路》,处处体现着她对工作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每读一遍,都会心生敬意。遗憾的是,母亲无法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否则,她该会有多欣喜呢? 人的一生中,注定会有许多人陪伴你走过。我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可爱的小精灵——赛赛。从他出生,我几乎花了十年的时光专心陪伴他。也许我因此失去了晋升职称的机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没有错失小精灵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今,小精灵已长大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伙伴,并时时激发我的学术灵感。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姐马秀花、大姐夫郝文和、三姐马晓燕对我的关爱,你们的亲情时刻温暖着我的心灵。 我的好友乌云高娃、范晓宇、祁菁、李涓、李煊、杨敏、包晓玲在我处于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给予我极大的温暖与支持,使我得以安然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好友杨春华、余月琴贤伉俪,华农、张小平贤伉俪的友谊亦弥足珍贵,谢谢你们给予我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使身处异乡的日子美好而又温馨。很幸运与王春霞、李玉红、陈妙峰等好友共处一城,可以与你们分享研究与生活中的兴奋与苦恼,聆听你们充满智慧的分析与建议。 由于我的懒散,这本书迟至今日才问世,但我并不后悔。这些年中,随着阅历与眼界的开阔,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深入,这一点都体现在小书各章节中,相信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体会到。本书的写作与修改得到了很多师友在资料上的帮助,他们是王安琪博士、刘海威博士、魏曙光博士、宋翔博士、大西磨西子教授、吴小红教授,Michael Brose教授、John Chaffee教授等,在此向你们致谢。 这本书能够问世,与浙江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刘进宝教授的鼓励密不可分,感谢亦师亦友的刘进宝教授;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波老师在出版不易的情况下接受拙著,这份勇气令人钦佩;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徐乐师老师的认真工作与辛劳付出。 我把这本书作为新的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扬帆远航,用心工作,用心生活!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