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临安还有面向皇族群体的专门性学校教育,即所谓宫学和宗学。特别是宗学,可谓南宋皇族教育的一大创举,并影响及后来的明清社会。严格来说,宗学和宫学是面向宗室群体的不同教育形式,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宫学源于王府官学体系,故它至始至终都以诸王宫院为单位开展教育,学官、宗室尊长以及相关宗司机构对教学过程共同负责;宗学则于诸王宫之外别创专门学校,开放式地统招宗室子弟进行集中教育,并不以某一王府宫院的本宫子孙为限,其管理也更近于太学体系。宋代宫学始于太宗朝,至仁宗时已趋于常规化,其后各项制度日趋完备,至徽宗朝蔚为大观,宫学规模宏大臻于巅峰。宗学之议虽首倡于神宗朝,但前后历经反复,此种新的宗室教育模式,一直要迟至南宋中后期才在临安真正成功创设。 
△ 南宋宗学遗址 绍兴五年(1135),临安始恢复宗室宫学教育,睦亲宅修盖了大、小学舍,然只有散落居所区区5间。朝廷本打算在睦亲宅附近勘察空闲之地,增广学舍,扩大招生规模。然而,数十年后,宫学凋敝的现状并没有多大改观。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宗正丞吴景偲上奏说:“宫学兴复既已历年,止有敝屋数间,萧然环堵,释菜无殿,讲说无堂。逼近通衢,又无廊庑。师儒斋几,卑隘浅陋。生徒讲读游息之地,抑又可知。”此前,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陈棠也批评道,自南渡宫学恢复二十余年,睦亲宅南班官及其子弟所授只是《论语》、《孟子》,“唯讲此二书,周而复始。学官失于申明,无有以六经讲授者”。而当时朝廷科举取士以经术为先,宫学完全摒弃六经,无疑对宗室进取十分不利。 孝宗隆兴年间,裁减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自此以后,“月朔止一人上讲,所教惟南班宗室十余人,往往华皓。每教授初除及朔望,则赴堂一揖而退”。宁宗庆元五年(1199),这时距高宗恢复宫学已过去60余年,但时任诸王宫教授的谯令宪仍然喟叹道:“中兴虽创学宫,然无斋舍以居,无廪给以养,课试之法不立,行艺之习亡闻。”可见,高宗以后历朝,宫学在规模、制度等方面都未见任何发展。朝廷一次次下令要扩建、重整宫学,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南宋宫学只能勉强以一种衰败面貌聊备形式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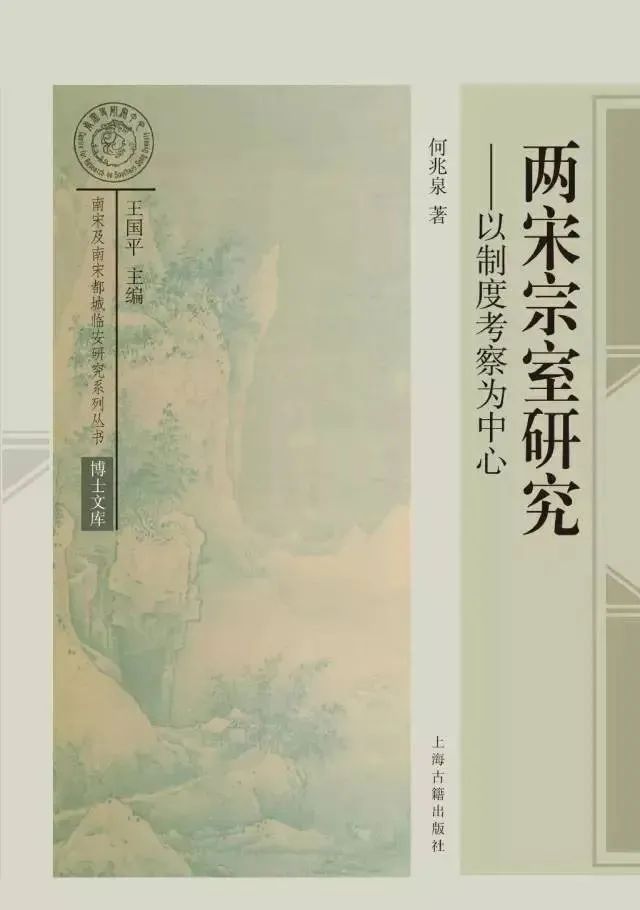
考察南宋宫学衰落的原因,并非因为南宋皇帝忽视宫教,而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一是靖康之难中大量宗室近属被俘,旧有宫宅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时先后在开封兴建睦亲、广亲、北宅、亲贤、棣华、蕃衍等宫宅,分别安置三祖下子孙、英宗子孙、神宗子孙和徽宗子孙。但经过靖康离乱,南宋临安只有睦亲一宅,“自绍兴以来,天属鲜少,故不复赐宅名”。加上南宋高宗、宁宗、理宗都无子嗣,加剧了近属凋零的局面,其余宗室又散处四方,已不可能再像北宋那样集中聚居一处,因此宫学赖以产生的土壤即庞大的聚居宫宅体系已不复存在,这应该是南宋宫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二是南宋宫学教育对象发生转变,专门面向极少近属。南宋曾有意通过兴复宫教来吸引地方宗室英材汇集京师,但在实际重建宫学的过程中,却是诸事苟简敷衍,导致的结果就是宫学教育对象囿于人数甚少的睦亲宅南班尊属,服属疏远者基本无缘附学。孝宗朝所谓宫学在读人员即只有10余位白发苍苍的南班宗室,根本没有讲授、考课之实。南宋宫学对象的转变给自身发展带来了极大损害。南宋时期宗室近属不兴、宫宅不完,宫学教育又将大量疏属摒弃于外,这两重因素交相影响,必然造成宫学衰颓不振。 于是,嘉定年间,朝廷终于下定决心另起炉灶创置宗学。嘉定八年(1215)四月五日,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危稹言: 窃惟宫庠乃国家亲睦教养之地,伏自绍兴复置以来,因陋就弊,阙典甚多。尝阅按牍,检会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都省札子,范择能申请乞将本学殿堂后睦亲宅空闲位子一所,量加修葺,展入宫学,以充讲堂斋舍。已札下临安府,差官相视地段,打量画成图本,检计工费外,欲乞检照临安府已申事理,早赐施行。 这一次,宋宁宗马上诏令封桩库特支官会三千贯,付临安府,“委官同官学计置,如法修盖”。临安城人多地狭,故宗学兴修主要利用睦亲宅空闲余地,将其与原来的宫学贯通起来。因为宗学选址与睦亲宅宫学相接,加上南宋宫学日渐式微,于是在嘉定九年十二月,宁宗亲自下诏令宫学改作宗学,并以宗学隶宗正寺。其后,有宗学谕范楷奏曰: 兹遇陛下加惠同姓,增广黉宇,经始不日,幸已落成。桥门显敞,堂庑深邃,规模鼎新,群日增焕。甚盛举也……臣闻五学之建,上亲为首;同姓之蕃,近属尤亲。国家始立宫学,所以训诸王之近属;继创宗庠,所以徕四方之宗亲。因其初意而增崇之,非固欲使新间旧、疏踰戚也。今睦亲之宅,广为学宫;教授之官,转为博谕。曩之宫学,一变而为宗庠矣。 从“堂庑深邃,规模鼎新”等描写来看,宗学较之原来衰败不堪的宫学,已是焕然一新。宫学既变身宗学,原来宫学学生一二十人也都转入宗学听读。依照国子监、太学、武学等各学成熟体制,宗学迅速建立起包括学官选拔、补试招生、月书季考等在内的一整套嘉定学制。宗学因为其开放性,加上又能与当时的取士制度相衔接,因此很快吸引了一批宗室子弟入学。嘉定十年(1217)三月,时任通判临安军府事的赵汝适(即《诸蕃志》作者)就遣送其子赵崇缜、赵崇徇参加了宗学补试。《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宫学、宗学俱在睦亲坊,且谓: 嘉定九年,始改宫学为宗学,即其地更创。凡在属籍者,皆以三载一试补弟子员,如太学法。改教授为博士,又置谕一员。隶宗正寺。十四年四月,因臣僚之请,复存教授一员,与博士、谕轮莅讲课。若沂府诸近属,则别置教授为清望官兼职,不在此列。 因为宗学选址睦亲坊,临安士兵又俗称睦亲坊为宗学巷。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学校》也记载,宗学有关学廪、膳供、舍选、释褐等制度皆仿太学规制,其内建有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六斋亦各有匾额,分别题作“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可见,南宋宫学转变为宗学,整个的学校隶属关系、日常管理、选试制度,都更多地向太学体系靠拢,也正因为这样,宗学对南宋后期的宗室教育、人才培养举足轻重,甚至对南宋后期的政治生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南宋宗学位置,来自《咸淳临安志·京城图》
事实上,正是在宁宗创设临安宗学之后,南宋宗学和太学、武学始被人并称“三学”。原来封闭宫院中默默无闻的宗室子弟,借助宗学这个新的平台日渐活跃,在南宋的政治中心发出更多的声音。临安宗学处京师之便,宗学生常和太学、武学诸生同声相和,匡论朝廷政事,甚至直接抗言上书,“激扬名声,以求胜于小人”,颇有东汉太学生参政余风。如嘉定十二年(1219),金军大举攻宋,当时工部尚书胡榘等人力主求和,太学生何处恬等人伏阙上书,“请诛之以谢天下”。其时,宗学成立才不过三年,但紧随太学生之后,宗学生赵公玘等十二人、武学生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相继伏閤上书,胡榘论罢后,叶寘还专门为此次抗议事件作《三学义举颂》。淳祐四年(1244),丞相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去世,前者本该主动离职守孝,但理宗却下令对史嵩之夺情起复。史氏久踞相位,积怨颇深,此举更是激起京城舆论的强烈不满。太学生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等九十四人、宗学生赵与寰等三十四人纷纷上书抨击史氏,宗学生至以“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相讥。尽管皇帝再三挽留,但在强大的公议压力下,史嵩之最终被迫解除了职务,并在丁忧期满后不久即正式致仕,从此退出了南宋的政治舞台。监察御史洪天锡屡次抨击宦官、外戚,触怒权贵。宝祐三年(1255)洪氏去职时,舆论哗然,“三学”纷纷上书挽留天锡,并指陈执政之过。宝祐四年(1256年)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又伏阙抗议,最后理宗不得不“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并判处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赵与麿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宗室子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临安的政治活动,与他们在宗学接受良好教育,并受到京师太学、武学风气的熏陶,培养了儒家士大夫的入世情怀与政治意识密不可分。在两宋历史上,宗室子弟竟是第一次以如此鲜明的集体面目站在王朝政治中心的公议舞台。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以郊祀大礼,宗学、太学诸官各进一秩,“诸斋长谕及起居学生,推恩有差”。这表明临安宗学教育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