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1937 年至 1949 年,由学生、助教到讲师,“我的前半生”主要部分是生活在浙江大学。这正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8年,也是伟大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12年,也是我“豆蔻年华”、学习成长的时期。我们追随这所“流亡”大学,辗转搬迁祖国西南山区近3000公里。在《竺可桢日记》里,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述。在浙江大学和史地系培养的成千名学生中,我是幸存者之一。在拙作《地学的探索》6卷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概括记述史地系对我教养的恩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注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则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1937 年我以同等学历考进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地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严格地给予野外基本功训练,把我们一大批同学引进了地球科学的殿堂。当时,我们就像闯进了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洞穴,感到光怪陆离,目不暇接。同学们毕业之后,分道扬镳,多有建树;我则被留在学校,当了8年助教和研究生,在老师们的指引和督促下,蹒跚学步,从此开始了探索地学的生涯。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我接受地学启蒙教育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是,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的经典的地学知识,学生则如饥似渴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的训练。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我们展示出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诱导我们专心致志去钻研,忘我地去探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从而树立起地球科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竺可桢校长(右一)与浙大部分教授合影 本文再就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联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琐事,像是醒来的梦境。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大学生活相比,的确是反差强烈,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然而,却是中国近代曾经发生过的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顽强的幸存者 1937年,我在湖南省长沙高级中学上二年级。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学校搬迁到宁乡花明楼。暑假,我路过长沙去上学的途中,在岳麓山以同等学历报考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由杭州内迁到泰和,距离井冈山不远,我想,要是能够就近在家门口上大学读书,既省钱,又安全。而且报考师范学院,既“司饭”,又发制服,免交学杂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真是双重保险的上策,何乐而不为呢?以同等学历报考,门槛更高,必须进入全国统考中前20%的名次,自知把握不大,报考不过是为明年探路而已,回到学校再读完三年级,毕业联考获第一名。再经过长沙时,长沙已经一片瓦砾灰烬。张贴在教育厅墙上的大学招生榜也早被日晒雨淋,模糊不清。有同学看到过我的名字,但也搞不清该上哪所大学。我自己也没有挂在心上,回老家白竺山村里去教小学。忽然接到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录取了我,家乡父老为我这个破天荒的大学生送行。我扛上一口柳条箱上火车,千里迢迢,一直追到广西宜山报到。孑然一身,开始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闯荡于黔桂“瘴山恶水”之间,去经受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广西宜山,师范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殿里。教室在远离城区的东郊,搭起整齐的茅草竹棚,在三个木椿上钉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著名的大教授穿着一件白大褂上课,带着我们朗诵着雪莱的十四行爱情诗,洋洋自得,出口成章。每天几乎都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看到山上挂起空袭警报的红灯笼。我就躺在水渠边或岩洞里去看红楼梦。老师甚至带我们到小泷江去练习游泳,或者去远郊野外实习,悠哉游哉!有一天,日本飞机果然在东郊教室投下了120多枚炸弹,男生宿舍起火,衣被都烧光了。女同学把五颜六色的衣服都捐赠给男同学御寒,男扮女装,教室里煞是好看!即使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依然充满着浪漫情趣和乐观精神。 随着学校内迁的,还有大帮浙江同来的难民群,他们为老师和学生包伙食,为学校搬运图书、仪器,他们介绍学生当“黄鱼”,由宜山搭便车去贵阳、遵义和湄潭。彼此如鱼得水,相依为命。老闾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加菜,吃当地的“豆花饭”,偶尔吃点蛇肉和狗肉,名曰“龙虎斗”。房东和师母们经常端上香喷喷的“粉蒸肉”或北方馒头,为无家可归的学生解馋。这所流亡大学就这样在整个社会的支持和簇拥下,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到娄山关下的遵义古城。 仅有的一次,师范学院的学生每人发放了27尺蓝色双面卡“救济布”。矮个子同学就自己设计一种最省布的上装和两条裤子,前后可以替换着穿,减少膝盖被磨损。男同学自力更生,钉制木屐、修补套鞋,互助理发;女同学针织毛衣,缝补修改衣服,这类的“蓝领”服务工作,更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到校外去当家教、做广告,去中学兼课,提供“白领”服务,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差。甚至个别助教、讲师也一起参加。我在遵义就干过为酱油厂做广告的工作,每星期日工作一天,工资5元,足够支付我和同学晚上的茶馆费和夜宵钱了。 
遵义何家巷校舍 何家巷是一座进深三栋的破院落,也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各院、各系混杂居住在一起,其嘈杂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中午时分,拉胡琴,唱京剧,似乎“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学会学社非常活跃,墙报,画刊五彩缤纷,救国救亡的文艺宣传,纷纷登场。晚上,在黯淡的桐油灯下,何家巷却是鸦雀无声,大家伏在桌子上静静地做功课。费巩教授捐出他的全部工资,为桐油灯加上了玻璃罩,灯光明亮多了,鼻孔不再被熏黑了。但是大宿舍里的自习桌总是不够的,同学们就只好去蹲茶馆,泡上一壶浓茶,占着一角方桌,就着茶馆明亮的煤气灯读书,比宿舍里的桐油灯更亮堂。好在茶馆里贴上了“莫谈国事”的禁令,干预也就不多,茶馆老闾对不谈国事,埋头读书的学生,似乎分外关照和欢迎。竺可桢校长能够在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在遵义山城、在何家巷宿舍,给学生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我们学生来说,更是多么幸运呵! 后来当上了助教,在遵义古城西南角的山坡上,租赁了一间民房,每天到山下的食堂去吃仓饭和打开水。过着箪食壶饮的隐士生活。没有吃饱,星期天自己开小灶,却不慎把桐油当菜油,落得个上吐下泻好几天!病了,也并没有医疗保健。1947年夏天,我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尿血,不得不去医院切除右肾。向亲友们借贷了8两黄金,直到1954年才还清。养病的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全是同学们送来的。史地系老师们非常照顾,让我躺在床上汇编《遵义新志》,不用上班。竺校长还亲自来助教宿舍看望,手里捧着一本名人传记,鼓励我说:德国有位大科学家也切除了肾脏,活到了70多岁,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是继续在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和指导下,从29岁至今,又快乐地工作了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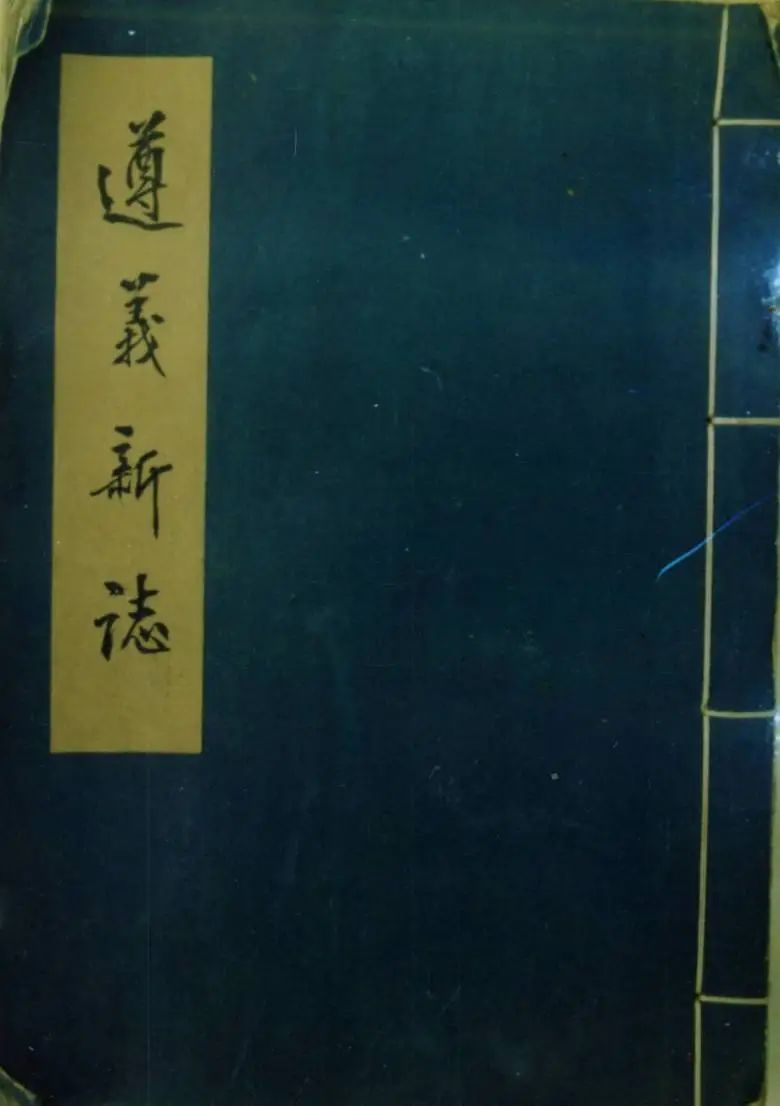
《遵义新志》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期间,多次用顾炎武的箴言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拂乱其所作为”。回顾血与火的岁月,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8年抗战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流亡的浙江大学,也是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弦歌不辍,为祖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 (本文原载于《浙大校友》2005(上),未完待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