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杭州新闻事业比较发达。当时杭州的新闻界不仅各种媒体数量较多,不少媒体质量也较高,而且与海内外的名人学者关系密切,文人郁达夫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换言之,在与杭州新闻界有密切关系的众多文人中,郁达夫是与之关系最深、影响最深的一个,而郁达夫与报社人员或交情深厚,或怨恨层生,故事多多。在这方面作一番梳理,或许有助于纠正坊间一些不确之传,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01. 郁达夫与新闻界的交往 郁达夫刚登上文坛,就与新闻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后,不仅寝食不宁,就连上课也无心听讲了,下课铃一响,“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狂奔而去。当投稿被采用后,他心情更是激动无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洪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象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圈起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求非但旧稿无存,就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 1933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移居杭州后,与新闻界发生的关系越发频繁了。郁达夫与东南日报社人员的来往,由来已久。在杭州定居后无论是最初住在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一所旧房子里,还是后来移居到住宅“风雨茅庐”里,两者都与东南日报社旧址和新厦不太远,交往更密切了,比如1935年9月4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午小睡,大雨后,向晚倒晴了。夜膳前,刘湘女来谈。”刘湘女是《东南日报》的总编辑。 在东南日报社的人员中,郁达夫与社长胡健中的友谊尤深,前后交往的时间也最长。1926年,胡健中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新闻,经人介绍,与郁达夫相识。郁达夫长胡健中六七岁,但两人都热爱文学,都学识深厚,因此相谈甚欢,一见如故。由于投机,有聊不完的话题,后来两人便干脆搬到一起居住,而且两人经常在地板上书堆中睡觉。这样既省钱又节省两人的时间。当时,郁达夫正在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一同工作的还有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郁达夫曾带胡健中去访问郭沫若一家。在郭沫若家中,他们见到了孤傲冷漠的成仿吾,两人还悄悄议论了一番。 郁达夫是杭州富阳人,而胡健中则是新杭州人。同在杭州工作和生活,郁达夫和胡健中自然十分高兴。胡健中以“子”为名,作了《采桑子·赠达夫》和《虞美人·赠达夫》送给郁达夫,其中,《采桑子·赠达夫》说道:“与郁达夫君一别十年,消息梗断,近忽于无意中枉顾,惊喜唱叙之余,赋此为赠:十年离乱音尘断,忽漫相逢,往事重重犹在鲜明记忆中。人生踪迹知何在?似梗如蓬,酒烟浓,且染今宵醉颊红。”郁达夫随即以一首《和蘅子先生》回赠:“当年同是天涯客,故里来逢,奇事成重,乍见真疑在梦中。谱翻白石清心句,爱说飘蓬,意淡情浓,可惜今时没小红。”郁达夫词中的“小红”,原是南宋词人姜白石的侍妾。对此,晚年的胡健中把“小红”与他们夫妇的结局联系起来了 :“达夫一辈子离开不了‘妇人醇酒’,这未尝不是他们伉俪隙末最终的肇因。”胡健中与郁达夫唱和的诗词后来均在《东南日报》的前身《杭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出来。 郁达夫时常言词激烈,表现“左”倾,引人注目。郁达夫在杭州期间浙江的政府当局对他不无疑虑,怀疑他与共产党有关系。胡健中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重要干部,自然知道这些情况,他不动声色地为朋友做了一些开脱和保护工作。20世纪80年代,胡健中说起此事:“我在这时也为达夫暗中费了不少唇舌,达夫恐始终昧于此中经过。”胡健中一生保护过不少人,郁达夫大概是他保护的第一个人。 不仅郁达夫与胡健中是好朋友,王映霞与胡健中的妻子王味秋也有同学关系,她俩是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先后同学。由于两家既是朋友,又有同学情谊,所以往来也比较多。晚年胡健中回忆当时情景时说:“中国名文学家郁达夫是我在大学肄业时的朋友,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他们夫妇是我家常在的佳宾,我也是他们在杭州建筑的‘风雨茅庐’座上的不速之客。他们夫妇的悲欢离合,至今仍不免于文艺界人士的悠悠之口。”王映霞对这个“不速之客”却很有好感:“记得他的言谈极为风趣幽默,常常是由于他的笑话而引得全场捧腹,而他自己却又能不动声色。”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也经常到胡健中家里做客。除了相互到对方家中,他们还经常同去游湖、到西溪赏花、逛旧书店、外出吃饭。1933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胡健中在西湖孤山南麓的“楼外楼”为来杭州休假的陈立夫洗尘。胡健中特邀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作陪。陈、郁、胡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面对桂子飘香的西湖,品尝西湖醋鱼,谈诗又论道。 郁达夫和王映霞仅仅在杭州生活了约3年的时间。1936年1月郁达夫离开杭州,到福州去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随着日本军队的步步入侵,王映霞也携老母亲及儿女离开杭州,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胡、郁两家虽然从此很难再像以前在杭州时经常聚会、游玩,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联系,只要有机会也要相聚。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在郁达夫朋友的帮助下,王映霞扶老携幼,先在金华后在丽水碧湖落脚。有一次,胡健中被邀至碧湖演讲没有旅馆可以住,便寄宿在王映霞家中。王映霞的老母亲对胡健中十分客气。胡健中日后回忆说:“映霞的老母亲对我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难忘。”1938年11月,王映霞绕道长沙前往福州,适值长沙告急而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焚城的大火中,她的衣服文件尽失。无奈之下,王映霞只好狼狈地经由浙赣铁路线返浙去金华找胡健中夫妻。一见他们,王映霞倾诉了一路上的坎坷经历,声泪俱下。胡健中夫妇一边安慰她,一边也深感难过和同情。兵荒马乱,生活实在不容易。王映霞在胡健中家留了一宿,第二天依依离别。 1940年,胡健中由金华到重庆探视父亲的病情时,又与王映霞不期而遇。对于当时相见的情景,胡健中晚年还历历在目:“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映霞。”两人相约次日见面深谈。在第二天及后来的几次交谈中胡建中得知她刚从新加坡回国,已经和郁达夫离婚。胡健中对王映霞说:“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哪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惟恐旁人不跌倒!”胡健中劝王映霞“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 02. 郁达夫是新闻界关注的明星 郁达夫举家来杭州,原本是想在杭州过“隐居”生活,但是事实上难以做到。在胡健中指派下,记者黄萍荪去采访郁达夫,并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题为《郁达夫望子飞腾》的访问特写,给郁达夫作了广告,也给郁达夫一家招去了很多粉丝。在杭州期间,郁达夫与胡健中、陈大慈(《东南日报》副刊《沙发》主编)等人一起担任了杭州作者协会理事和常务理事,还担任东南日报社当时正在编辑的《东南揽胜》的编委。郁达夫是杭州文坛和上层社会中的活跃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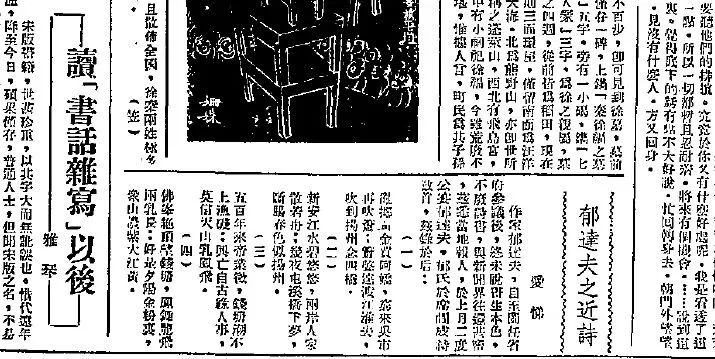
▲《东南日报》刊登的郁达夫诗文 1935年4月间,胡健中与王世颖出访日本。临行之前,杭州作者协会假座“聚丰园”为他俩饯行。郁达夫夫妇也受邀出席。请看当时报道的描写片段:“为大家所注目的我们的老作家郁达夫,偕着他‘日记九种’中的主角王映霞女士来了。这老作家倒是一位标准丈夫,替太太脱外套,接手提箧,招呼得周周到到。我们的老作家倒不是道貌岸然的,一个地方有了他,大家都会高兴起来,笑声也会不断的充满了一屋子。”“老作家郁达夫穿着蓝洋布长衫,一手捧着酒壶,一手捏着纸烟,一口酒,一口烟,兴致之豪,为举座冠,惜乎太太随护于左,闺中约法三章,第一条便是吃酒以二壶为限,故而未能喝到十分。” 郁达夫的名人效应也确实很大,他来到杭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举一动,杭州和上海的新闻界就会有反应,真真假假,莫衷一是。 郁达夫有时也买买诸如航空券之类的彩票,比如1935年7月4日“中午又买航空奖券一条,实在近来真穷不过了,事后想起,自家也觉得可笑”。因此,有关郁达夫买彩票得奖的消息也时在《东南日报》上刊登出来。1936年年初,“上海各小报,盛传郁达夫着了航空券,最近又有人说,达夫得了他阿哥的五万元遗产,所以书也不要教了,文章也不愿写了”。上海新闻界刮风,杭州新闻界也要下雨,有人写文章分析上海新闻界传说的原因:“至于发生这种说话的原因,是为了他在杭州,造了一所房子。造房子,固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造房子而出于文人,出于该应命穷的文人,这就值得社会上的惊愕了。”不过,这篇文章出来的第二天,就有人出来反驳了,说郁达夫确曾中过奖:“昨本刊《郁达夫并没有发财》文中,述达夫不但没有得到遗产,亦不曾中过航空奖。但据本人所知,达夫在不久之前,确曾中过航空奖券。唯所中者为末尾两条,计大洋两元之巨,而非头二三奖耳。特寄本刊,兼为达夫发发利市。” 1936年1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去福建省政府任省参议。郁达夫人在福州,但他的一举一动,仍不断地在报纸上反映出来:“郁达夫于本年一月间应福建省政府之聘,赴闽任参议,曾一度返杭,未几又南下福州,仍寓居于南台万寿桥边之四层楼上,时与福州文艺作家,诗酒往还,有时逛逛名山,有时写写随笔,在省政府大门内外,殊鲜见其足迹也,闻二百法币之月俸,亦须会计处差人送去云。郁尝谓福州有三绝,一为山水好,二为温泉好,三为姑娘好,其断句诗云:‘他年归隐西湖去,应对春风忆建溪!’”世人,尤其是新闻界关注和炒作郁达夫,几达挖空心思的地步了,连他的外表也编个故事出来给读者乐乐: 郁氏富阳人,乳名荫生,当他在富阳小学读书的时候,邑中一般青年无不爱说“起码”。譬如:“我这次作文起码得一百分”;“我毕业起码考个第一”;“我将来起码做个文学家”;“我将来起码做个省长”;……诸如此类,随口乱说,“起码”之声,几不绝耳。郁氏不能例外,亦常说起“起码”。 一天课余,几位天高地厚的同学,聚在自修室里,大谈其“起码”。于各人的“起码”中,郁氏突然从座位里跳起,翘起右手的大拇指,向众高声道:“我将来起码做个大总统!”说罢,回顾案头,揽镜自照不禁紧蹙眉头,频指镜中影,摇首颓然道:“不像!不像!你这副尊容,那里是总统相!”惹得哄堂大笑。 而今郁氏虽不是个政治上的元首,但早成就了个全国文学界的权威者:且近已荣任闽省政府参议,亦大可自豪了! 当然,郁达夫在杭州期间,更多的是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文章。从1934年7月起,郁达夫陆续在《杭州民国日报》副刊《越国春秋》和副刊《东南日报·沙发》《东南日报·小筑》《东南日报·吴越春秋》上发表了不少题材广泛、内容多样的作品。郁达夫发表的作品很多是对杭州人和事的描绘、议论,经常在杭州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如1935年在《沙发》上的《说(勖)杭州人》,写出了郁达夫对杭州人风气的希冀:“杭州人先要养成一种爱正义,能团结,肯牺牲的风气;然后才可以言反抗,谋独立,杀恶人。否则,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挣扎到底,也无成效。外患日殷,生活也日难,杭州人当思所以自拔,也当思所以能度过世界大战的危机。越王勾践的深谋远虑,钱武肃王的勇略奇智,且不必去说他们,至少至少,我想也要学学西泠桥畔,那一座假坟下的武都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生死可以不问,冤辱可不能不报。”《说(勖)杭州人》发表后,引人注目和争议。一个笔名叫孙用的人也曾先后在《沙发》上刊发《我是杭州人》和《理想家的理想》,对《说(勖)杭州人》不满,他在给《沙发》主编陈大慈的信中说:“读《沙发》上《勖杭州人》之后,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今寄奉反响一篇,不敬之语已去了不少,以为可以在沙发登载。副刊上能登些相反的文字,可以使得更有生气,老兄以为如何?文中忍不免有逆耳之处,郁老先生或不以此见怪吧。” 郁达夫是个以卖文为生的文人,他在杭州报坛上的耕耘,收获不小,既给他带来了更多粉丝,也对他和他的家庭在杭州的生活和消费不无小补。须知,郁达夫举家南迁,花费很大,尤其是建筑“风雨茅庐”共花费了一万五六千元,这笔钱中除了历年的积蓄外,一半以上是借贷来的。 03. 新闻界深卷郁达夫的婚变 在杭州的3年中,郁达夫和王映霞感情不错,两人出双入对,给人印象他俩恩爱甜蜜,新闻界也时有人开他俩的玩笑,“醋鱼”事件便是一个例证:“文学家郁达夫氏,做官回来,丰采较前益佳,日昨夫人王映霞女士,至本报访晤刘湘女氏,谈及本刊半上流信箱发明‘丈夫有外遇,太太称醋鱼’问题,至为轩渠不置,临别刘谓将往视郁新居,郁笑答请吃醋鱼,刘连称不敢,王女士则芳颜微颊,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想到,郁达夫后来回家还果真以“醋鱼”为题作了诗:“宋嫂鱼名震十洲,却教闺妇暗添愁。旧词新解从何起,恨煞萧山半上流。”新闻记者本就最喜欢开郁达夫夫妇的玩笑,现在郁达夫自献题材,记者们自然求之不得,当天的报纸上编辑就特地给《醋鱼》加了按语:“自本刊发表《郁达夫请客吃醋鱼》一文,上海各报,竟相转载,郁夫人王映霞女士,不承认本人为醋鱼,更不愿意其藁砧请客吃醋鱼,曾与编者大起交涉,达夫先生为其闺妇解愁计,以‘恨煞萧山半上流’之句,代夫人声讨半上流君,但据日前半上流君信箱答某君问,谓家住半山脚下,而郁君硬派他为萧山籍,然则所谓萧山半上流者,苟非别有其人,定系盲打瞎撞,半山之半上流君读此,当哑然失笑其摸索暗中,大类无的放矢也。” 
▲郁达夫与王映霞 文坛上也有不少人就《醋鱼》来和郁氏夫妇凑趣了,比如一个笔名叫“看云楼主”和那个笔名“半上流”者来与郁氏夫妇凑趣了:“醋溜鱼名满福州,达夫快活映霞愁。萧山饶舌终轻薄,合署头衔是下游。”“从来朝奉出徽州(看云徽州人),未吃醋鱼心亦愁(看云无妻)。捧得艳秋天上去(看云为捧女伶新艳秋健将),如何沧海竟横流(看云对艳秋鞠躬尽瘁有曾经沧海之语但近又赏识遏云是沧海竞有横流之日也)。” 谁会想到,这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婚姻关系竟然仅仅维持了12年。他俩1928年结婚,1940年分道扬。造成郁王婚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郁达夫怀疑政界新闻界一个重要人员介人了他们的婚姻。此人便是许绍棣。 许绍棣,浙江临海人,192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后又兼任了杭州民国日报社社长。1934年,他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前后长达10余年),辞去报社社长的职务,但仍为报社的常务董事。1946年离职教育厅后,又回来担任了东南日报杭州分社社长。郁达夫和王映霞搬到杭州后,当时杭州往来的朋友较多,许绍棣也是其中之一。郁达夫和许绍棣本有同学关系,加之当时他们都是杭州上层社会的名流,两家时有往来,王映霞晚年也说过:“我和郁达夫搬到杭州后,当时杭州往来的朋友较多,许也是其中之一”。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比如1937年5月2日,他写道:“午前十一时,绍棣偕周校长至柔来,同去杏花村喝酒。因与幼甫阎氏有午后去九溪之约,故饭后即匆匆驱车往。车过钱江大桥北岸,见桥墩都已打就,大约十月通行之说,确实可靠。车中,绍棣为讲红舌村故事,听者讲者,两都忘倦九溪茶场,今天游客特多,程远帆氏夫妇、邵裴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坐至午后四时,返城。晚上由绍棣作东,约慕尹主任夫妇在三义楼吃饭,饭后并去东南日报馆看演《狄四娘》话剧,至十时始散。”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许绍棣成了郁王婚变的导火线,这点王映霞也是承认的:“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做难人。我和郁的争吵、出走、最后离开,凡事种种似乎均归之于由我与许绍棣的相识为导火线。” 1936年12月间,许绍棣的妻子病故。在许妻生病和去世期间,胡健中的妻子及其亲友们都去帮助照顾许妻遗下的3个幼小的女儿,和参加尼庵中“做七”的习俗。王映霞也去了。接着,就有流言传出,说许绍棣在暗中追求王映霞,还给了她37万多元港币。郁达夫听到了传言,恼怒万分。王映霞是郁达夫千辛万苦追求到手,尔后,“他和夫人王映霞的罗曼史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被渲染的一页。达夫博极群书,风流放诞,映霞则丰容盛,顾盼生姿”,郁达夫岂能容忍别人来觊觎王映霞? 其实,郁达夫夫妇原本就有很多矛盾。胡健中认为,郁达夫“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正常的婚姻生活经常被郁达夫多变的脾气破坏。除此之外,令王映霞更加无法接受的是郁达夫始终没有同第一任妻子孙荃离婚,而是仍然和孙荃暗中往来藕断丝连,还多次在诗作中将王映霞比作“妾”。作为一个新时代接受文化教育、有着强烈自尊心的女性,王映霞对这些岂能无动于衷?有关许绍棣,她也向郁达夫坦承过她的确经常向许绍棣诉说心中苦闷,她把他当作了一个寻求心理慰藉的对象。许绍棣也对王映霞甚为关心,经常询问她的生活情况。王映霞背井离乡的时候,许绍棣给她写过信,询问她和她家人的安危情况。 然而,郁达夫却认为许、王关系远不止于“心仪”,他做出激烈的反应。据新闻界人士曹聚仁回忆:“我在福州时,不曾碰到郁达夫兄,可是他俩脱辐的事,真的闹得满城风雨;而他把许氏写映霞的情书制版影印,派送给朋友们,更使映霞十分难堪。”同时,郁达夫还想方设法地寻找他俩不正当关系的证据。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到武汉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离开福州赴武汉的路上回到丽水,张罗着把全家接去汉口,走时还带上了自己一个朋友的女儿李家应。据王映霞解释,去汉口的路上,李家应托王映霞替好友孙多慈(画家)介绍一个对象,王映霞便想到了许绍棣。之后,李家应让王映霞写信给许绍棣,询问对方的态度,许绍棣也回了几封信。没想到郁达夫见到这几封信后,认定就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还将信拿去照相馆印了出来。王映霞说,怎么也想不到,这几封信会将自己的婚姻推向绝望的深渊。 而郁达夫一想到这几封“情书”,始终感到极为羞辱,心气总不能平,便到处找王映霞的茬。就这样,他与王映霞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在一次争吵中,王映霞赌气去了一个朋友夫妇的家中住下,并且不让朋友去通知郁达夫。郁达夫找不到王映霞,气急败坏,以为王映霞跑到了许绍棣那里,便叫上了他的一些同事,到家中看许绍棣和王映霞的“情书”,并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信告状,要他们管管许绍棣。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刊了一则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许绍棣也是个名人。这则启事中,郁达夫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点了许绍棣的名,王映霞也丢尽了颜面,一时间舆论哗然。继福州后,当时的武汉三镇除了战争新闻外,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连敌伪报纸《新浙江日报》也刊载过报道《情海乍兴波澜,郁达夫妻私奔》。 胡健中不赞成郁达夫激化矛盾的做法,同时为朋友、为同事,他想把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7月9日,正在武汉公干的胡健中辗转拉上杭州市长周象贤(周企虞),一起在汉口太平洋饭店里为郁达夫和王映霞调解。胡健中和周象贤煞费苦心,还让郁达夫和王映霞签了一份和解书。 在胡健中和周象贤的劝说下,7月10日,郁达夫又在《大公报》上再登一则启事,痛责了自己感情冲动,向王映霞和没有点名的许绍棣致歉:“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责女士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的风波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破镜虽能重圆,但是裂缝却难以消弭。王映霞经历了这样一次巨大的侮辱之后,已经难以再和郁达夫回到从前的恩爱状态了。郁达夫也仍对王映霞和许绍棣的关系满是疑虑,不断暗中侦察。离开汉口回福州的路上,郁达夫一边沿途给王映霞写信,一边打了几个电话给他在浙江省政府中的熟人,打听王映霞是否去丽水和许绍棣同居了。当然,王映霞当时对此浑然不知,这是后来在浙江工作的弟兄告诉她的。7月26日,郁达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仍这样说:“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 总之,胡健中的努力付之东流了,郁达夫和王映霞最后还是劳燕分飞,各奔东西。1939年3月至8月,郁达夫于上海《宇宙风乙刊》连载了其《回忆鲁迅》。文中有几处谈及了鲁迅与许绍棣的关系,虽然没有点名: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更糟糕的是,在上述引文尚未见报之前,同年3月5日,香港《大风》第 30期上,刊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诗19首、词1首),全面叙述了郁达夫与王映霞感情破裂的过程,尤其是《毁家诗纪》的原注中,多处将矛头直指许绍棣,比如:“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xxx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x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x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x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x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x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x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x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虽然“诗注有许多话不能够照着来稿全文发表,不得不略予删去”,但是,《毁家诗纪》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1940年的一天,王映霞托刘湘女在《东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1942年4月2日和4月5日,《东南日报》又出现了两则启事:“王映霞、钟贤道结婚启事:兹承吴启鼎、朱邵阳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詹于三十一年四月四日在渝结婚,特此敬告海内外诸亲友。”“王映霞、钟贤道结婚启事:谨择于国历三十一年四月四日晨渝嘉宾馆举行婚礼,并敦请王正延先生证婚,特此敬告诸亲友。”这两则特地在《东南日报》上刊发的启事,算是给浙江的亲友一个交代吧。《东南日报》上的这两则启事,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胡健中晚年写了一些文章和书信,回忆了许、王两人的情感纠葛,并极力为他们开脱。胡健中认为,社会上有关许、王的种种传言,多属虚构。他说:“以许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实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1989年,胡健中在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中又写道:“健中之作此文,不仅为方正清廉之亡友许绍棣兄与相交已久知之有素之王映霞辟谣,亦所以对历史负责,不容史实为悠悠之口所混淆。君等之招物议,由于达夫之过分歇斯底里,亦由于绍棣之冷漠,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君当年之绝代风华,亦娥眉谣诼之所由起。君等相处既久,彼此心仪,此贤者所不免,不容为讳。至一般社会所传,健中深信多属虚构,考汉朝有一名直不疑之大臣,被控盗嫂,又为人诬为掴其妇翁之颊,嗣经朝廷彻查,直不疑并无兄长亦独身未娶,世之多嫌,古今无二,健中平生不轻信人言,正如是幸!君与健中均已垂老,应善加珍摄,毁誉事小,不必多所介怀。” 1990年12月21日,应胡健中及台湾传记文学社的邀请,85岁高龄的王映霞由女儿陪同,去台湾访问。郁、王婚变和许、王纠葛天下皆知,王映霞的台湾之行轰动海外。王映霞在胡健中家里前后逗留了3个月,除会见了许多当年的旧友外,还与胡健中尽情地回忆了从前的许多旧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