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友兰先生晚年时曾将自己毕生的事业总结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其中,“三史”是指所著的三部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指他在抗战期间所著的“贞元六书”。“三史”和“六书”是冯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所做的两大贡献,他自己也因而成为少数几位思想自成体系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之一。青年时期他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又接受了西方柏拉图哲学、新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能熟练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做到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本文重点阐发、探讨冯先生“三史”中对“阳明心学”所做的多维透视和比较研究,从而在学理上推进阳明学的研究,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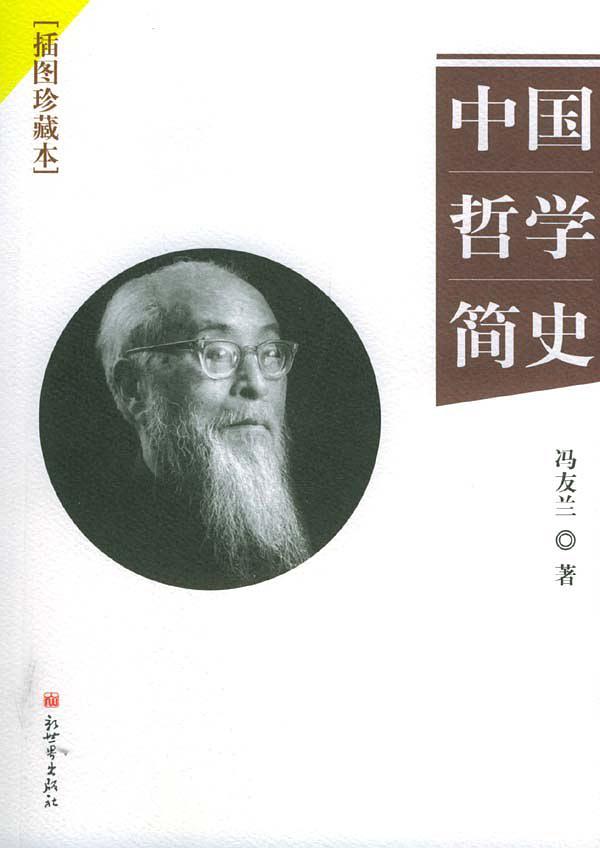
一、分析程颢、程颐二人哲学的差异及其开创的心学与理学两派 中国古代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形成了与先秦孔孟之学和魏晋玄学不同的哲学思潮,出现了儒家思想的新形态。有人称之为“宋明理学”,有人称之为“宋明道学”。冯先生认为,用“道学”这个名称,比用“理学”更合适。因为如果用“理学”这个名称,会使人误以为就是与“心学”相对的那个“理学”,不易分别“道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派。只有用“道学”,才能概括“理学”和“心学”。 冯先生指出,道学的前驱是北宋周敦颐和邵雍,奠基者有二程和张载,接下去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以及明朝的王守仁(王阳明)。准确地判别“二程”的哲学属性,是研究朱、陆、王诸家哲学的前提。早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冯先生就把北宋的“二程”,分别界定为:程颢为“心学”之先驱,程颐为“理学”之先驱。他指出,程颐所说的“理”,“不增不减,不变亦不动”,所谓“寂然不动”也。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亦谓“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也。不独人具有万物之理,即物亦然。不过人能用之,物不能应用之。“人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而程颢所说的“理”,“似指一种自然的趋势。一物之理,即一物之自然趋势。天地万物之理,即天地万物之自然趋势。”正因为理不能“离物而有”,所以,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并不十分注重;而程颐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极为注重。程颢对于“气”未有多言,而程颐则多言之。关于“性”,程颢所言甚少,而程颐则将人所得于理,称之为“性”,而且说“性即是理”。程氏兄弟不仅在上述对理、气、性的看法上,分别成为以后心学与理学之前驱,而且在修养法上也成为心学与理学之前驱。“涵养须用敬,明道亦如此说。但明道须先‘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此即后来心学一派所说‘先立乎其大者’者也。伊川则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求‘脱然自有贯通处’。此说朱子发挥之。” 二、探讨朱熹与陆九渊哲学思想的对立和“鹅湖之会”
冯先生指出,朱熹把程颐关于“理”的理论向前推进,阐述得更加明晰。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朱熹用佛家常用的比喻“月印万川”来说明太极整体之理与万物个别之理的关系。如果只有理,那世界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但我们外部还有一个“形而下”的物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理”与“气”的关系。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阴阳相交,生出五行,由此生成万物,而“理”是“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朱熹赞成程颐关于“性即是理”的说法,人性是人类得以生成之理居于个别人之中。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人类这理虽然是共同的,但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朱熹把理原来的普遍形式称为“天地之理”,以和人所禀受的“气质之性”相区别,据此作为区分性善、性恶,天理、人欲的理论依据。朱熹认为,“心”是“理”加上“气”之后的体现,和其他的个别事物一样,是具体的可以活动,如思想,感觉;“性”是抽象的,却不能有这些活动。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是四种“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德之四端”则是“心”的活动。人们通过心的活动,才能认识人性。仁是“性”,恻隐是“情”,情要从心上发出来,所以才说:“心统性情”。 “心学”派的哲学家陆九渊,与朱熹的上述观点有重大的分歧。朱熹认为“性即是理”,而陆九渊却说“心即是理”,“心”也即是性。在陆九渊看来,世界只有一个,现实只是一个包含心的世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反映在修养方法上,朱熹主张“格物”以“穷理”,通过格各种具体的“形而下”之器,去寻找那“形而上”之道。而陆九渊则认为,“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去掉“限隔”,恢复心的本体。心学的方法是“先立乎其大者”,而理学的方法是“即物穷理”。两者之异,显而易见。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朱、陆两人的共同好友吕祖谦邀请朱、陆两人及两派的人在江西的鹅湖寺相会,探讨“为学之方”。结果陆九渊一派说理学的方法是“支离”,朱熹一派认为心学方法是“空疏”。会议不欢而散。其实朱、陆之争只是理学与心学对立的序幕,王、朱之争才是两派斗争的正剧。虽然王阳明是活动于250余年后的明朝。 三、阐述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以及他对陆九渊心学的发展 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是继陆九渊之后,心学思想的发展和完成者。他早年曾追随程朱理学,决心依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见竹取而格之,沉思不得,遂被疾”,终于放弃了“格物”这条路。后来,由于朝廷政争,37岁时被贬贵州龙场驿。“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43岁时,“始专以致良知训学者”。 冯先生对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做了阐发。他说:陆九渊着重在于说明人都有良知;王守仁着重在于“致良知”,是圣人或不是圣人,关键在于那个“致”字。陆九渊对于“行”说得不够,王守仁特别着重“行”,所谓“知行合一”的要点,说是说如果没有“行”,“知”就不能完成。 其实,陆九渊和王阳明所讲的都是要“穷”人理。“穷”,不能靠语言,也不能靠知识,只能靠道德。王阳明讲“穷人理”,不是不要“穷物理”,而是说,穷“物”之理,是为穷“人”之理服务的。“穷人理”就要尽量发挥“良知”的作用,这就是“致良知”。既然“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那么,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与行为的关系,而是要去掉私欲,恢复本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人心之本体不为私欲所蔽时,知与行实际上就是一回事。 四、指出王阳明与朱熹对《大学》认识的分歧 冯先生在《新编》中充分展开了对此问题的阐述。朱熹把儒家经典《大学》列入《四书》之首,并在《大学章句》中,把第二纲领中的“在亲民”,改为“在新民”,并且增写了《格物补传》,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大人之学”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所谓“明明德”,就是“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王阳明反复强调:“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一体之用也。”冯先生明确指出:(《大学》的)三纲领其实只有二纲领,那就是“明德”和“亲民”。“至善”不过是“明德”和“亲民”的极至,再进一步说,只有一纲领,因“亲民”“至善”不过是“所以明其明德也。”冯先生指出,“在亲民”的那个“亲”字表示出“己”与“民”的内在的联系,“新”字就只能表示外在的联系,那就不是“仁”了。“亲”表现为“爱”,是“热”的,而“新”是“冷”的。三纲领的目标不是增加知识而是要通过道德实践,实现“完人”,成为“圣人”。所以,王阳明不赞成朱熹把“亲民”改为“新民”。 冯先生还指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问题在于:“穷人理”为什么要从“穷物理”开始,“物之理”和“人之理”如何沟通?程朱未能提供满意的解释。王阳明的《大学问》把“物”看作是“事”,“格”字也就是看作是“正”的意思。这样,“格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