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陈寅恪先生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学界对于什么是新材料,如何定位不同性质的新材料的研究价值,有了新材料如何提出新问题,如何处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关认识得以不断提高。对于唐宋史研究来说,新材料不仅包括出土的文书、碑刻和其他各种考古资料,也包括不断被发现的湮没无闻、久不“传世”的文献,如明抄本《天圣令》。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材料如何才能做到高度警觉、紧密跟踪,与此同时,又不被材料所牵绊,真正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从容驾驭材料,淡定“预流”,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期笔谈特邀唐宋史领域的领军学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就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的问题各抒己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是我们要终生面对、尽心处理的对象。
史学领域中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距今86年前,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即指出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于“一时代之学术”的重要意义。与中古其他时代相较,宋代存世文献尚称丰富,而新发现的材料不多,足以撼动既有认识的材料更少。尽管有考古学界的长期关注和宋史学者的不断跟踪,但出土材料的发现,仍属可遇不可求之事。宋史学者日常所见材料,有许多是来自“坊间通行本”的。严耕望先生曾经说过:“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些材料经过深度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视域、新的方向、新的问题点,即可能“激活”许多以往不曾措意的内容,从中领悟到新的认识。 
对于宋代出土材料和常用史籍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这里仅举突出的两例:就出土的文书类材料而言,浙江武义南宋时期徐谓礼文书的出土,特别是2012年包伟民、郑嘉励领军对于这批文书的高水平整理,为学界开启了新的“议题群”,提供了深化研究的依据;就宋史界熟悉的文献史料而言,《宋会要辑稿》的再度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方便,更引发对于这类基础史料本身深入认识的可能。近些年学界注意到的宋代行政文书类材料,包括法令汇编、地方军政文书、公牍之类,相对集中的有《天圣令》、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以及宋人佚简等。这些材料被发现后,受到唐宋史学者广泛重视,从整理到研究,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呈现。传世文献中有许多涉及行政文书的内容,但对于文书流程通常并非直接记载。政令文书的流程是政治秩序的体现,反映着权力的枢纽、制度的环节与政令的流向,从中得以观察帝国时期行政网络的运行方式、官员关系网络的结构形式。当年留下的有关行政运作程序的书法卷帙和出土文书,使我们有机会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讨论从唐朝、五代,经过北宋直至南宋的制度设计、行政规程与实施中的具体情形。徐谓礼文书,基本是围绕官员个人的个案材料,就其涉及内容、篇幅规模而言,自然远不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材料相比;但它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尽的中古官员个人仕履资料,在制度史上有其特殊价值。该文书的面世,为宋史学界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扉,提醒我们追踪新的材料,也使我们得以提出并且思考新的问题。这批文书的发现,充满了偶然性,但偶然中也有必然。仕途是官员的命运所系,官宦身份是其一生成败的重要证明。就今见唐宋时期的材料来看,以不同形式保留仕履记录(尤其是官告),可能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唐代西北、宋代东南,都不乏例证。研究者曾经指出,唐代有以正式告身文本随葬者,也有家人在临葬时抄录死者告身原件用以附葬者;不同地区发现的唐代随葬告身抄件,有纸本,亦有石质。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随葬告身抄件实为唐代丧葬的一项制度”。南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后附8份官告1份敕黄,杨万里《诚斋集》附有其“历官告词”31份。陈康伯、方逢辰等人的文集,都是其后裔编成,其中也存有他们任官南宋时的敕牒、告身。徐谓礼是南宋中后期众多官僚中的一员。正是由于其身份、事历平常,因而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其历官文书,是成千上万中下层官员履历记录的代表。官告、敕黄、印纸等材料备份“录白”,承载着官员(包括已逝官员)的精神寄托,鲜活体现出当时官僚社会的特色,也反映着时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些告敕无论是珍存于家中、附着于集内,还是随葬于墓中,都体现着官员本人及其家属的理念,体现着他们对于仕宦身份证明的重视;而不同之处是,文集中的告身等材料,皆无程序,无签署,对于实际流程的质证意义,远远不及文书实物。对研究者来说,保留完整的徐谓礼文书无疑是珍贵的制度史资料。整整30年前,我自己的硕士论文,主要针对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研究。当时讨论到宋代的磨勘叙迁、差遣除授,成资、年满、待次、待阙等问题,也涉及宋代考核官员的印纸批书。写作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官方文献的记载。近年里一些青年朋友关注文书制度,观察官僚体系的运行方式,一直希望寻求能够体现“运行流程”的实物载体,不仅从正史文献,也从传世的书法卷帙中探索制度的运行踪迹。恰在此时,这批文书提供了契机,使学界的认识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徐谓礼的告身、敕黄、印纸录白,反映南宋时期人事除授中文书档案制度的成熟,也呈现出以往不为人知的若干细节。通过这批文书,我们了解到当时相关制度运行的方式、程序、实态。这“实态”一方面是相当的程式化,体现制度的异化,并非如想象般地“运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得以窥得制度的实际目标及其施行重点所在。《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面世后,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反应。继2012年11月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之后,201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学术研讨会”;2014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出土文献与历史研究:7~13世纪”博士研究生研读班,也包括了有关徐谓礼文书的专题。我个人2014年春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开设的“宋代文官选任与管理”(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ng Civil Service)课程以及2015年秋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走向‘活’的制度史”工作坊,也都涉及文书中的内容。出土文书带来了新研究的可能性,而将这可能变为现实,要靠我们的切实努力。就徐谓礼文书而言,尽管其性质相对单一,但我们的研究要秉持多面向、重综合、广格局、深追问的原则。所谓“多面向”,主要是对于观察与研究的切入点、着眼点而言。首先,传统史学应该与田野考古工作相结合。如郑嘉励所说,文书是墓葬整体的组成部分,要结合南宋时期的墓葬理念、墓葬格局、墓葬形制,观察文书材料在特定墓葬随葬品“序列”中的原始位置。我们的研究着眼点,是要把特定材料“嵌入”历史现场,力求还原其本初“意义”。其次,议题要充分拉开,要对文书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从目前对于官告、省札、荐举、考核的研究,对于给舍封驳、签署花押的研究,对于地方行政、发运司的研究,对于公文处理乃至书手书法的研究,等等,延伸出多方面的认识,挣脱出论题单一的窠臼。另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录白”特点,既关注文书类型、文书性质、文书内容、文书结构、文书形制,也关注“录白”与原始文书的区别,这样才可能形成更为丰富的研究生长点。所谓“重综合”,主要是指材料的综合利用,相互发明。首先,要将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形成不同来源的“材料组”,彼此质疑、印证,这样才能改变我们习用的设问方式,真正深化我们对于相关制度的了解。其次,要善于汇聚不同类型的散在材料,例如文字材料中的石刻材料、书法作品、宗谱族谱,以及非文字材料中的各类图像、历史遗迹、墓葬群等,使我们对于文书自身及其制度文化背景、环境氛围的认识相对综合而非琐碎“散在”。所谓“广格局”,主要是对于南宋整体的观察与研究而言。“点”状的研究本身并不意味着“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心中是否有开广的格局观。就文书解读而言,随文释义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而“义”之所在,不仅通过文书中的语汇字词表述出来,也经由充斥、渗透其中的倾向、气息体现出来。仅就文书讨论文书,不是历史学真正的出路。徐谓礼文书对我们而言,是思考的例证,是观察的线索,而不是聚焦的终极。现有的知识结构对于文书理解有重要帮助,但不能拘泥于既有框架;要以文书实例来丰富以往的认识,挑战以往的认识;要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前行,走出以往认识的束缚,争取对于宋代制度格局有新的体悟。所谓“深追问”,是希望提醒我们这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善于提出问题,善于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就学人普遍关注的印纸来说,徐谓礼时代的批书方式,可能比北宋规定细密,但从目前材料来看,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这一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盖着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能停留于表浅层次的论断,不能让我们的研究沦为具文。真正的“研究”,要继续追问如何理解这“制度”本身:世上本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原原本本谨守规定的“实施”。就徐谓礼印纸批书中的考成文书而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尽管异化却有模有样、代价不菲的做法,在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退一步讲,即便如我们所批评的,当时某些做法是体制内“敷衍”的产物,甚至是各级人事部门对朝廷规定阳奉阴违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行家里手”们根本不了解这类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问:这种循规蹈矩的“阳奉”,为什么会被认定有其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阴违”,为什么会被长期容忍。这些问题,都牵涉对于印纸性质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2014~2015年在宋代基本史料建设方面的另一大事,是《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的整理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众所周知,《宋会要辑稿》称得上宋代史料之渊薮,被所有宋史学者视为“看家”的重量级史籍。先父邓广铭在其自传中曾经说,抗战期间他到昆明不久,在傅斯年先生的强烈建议下,用自己的全部月薪购置了《辑本宋会要稿》,从此“把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辑稿》对于宋史学人的意义。《辑稿》在辑录、流传、整理过程中的坎坷身世,一方面使其受到许多关注,辗转整理者不乏其人;另一方面因其部头太大,内容纷繁,甚至蒙罩着不少谜团,长期以来对其的整理研究被视为畏途,工作难以到位。研究者对于这一重要史籍的阅读利用,感觉诸多不便,学界一直期待严肃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着手进行《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准备工作。1988年,陈智超先生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补编》面世。2001年,《宋会要辑稿·崇儒》在王云海先生指导下点校出版。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U盘版的《宋会要辑稿》数据库,可惜并未做全面整理。多年前,四川大学古籍所与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完成了《宋会要辑稿》的校点工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该电子版经台湾大学王德毅先生加工修订,纳入台湾中研院汉籍全文资料库,登上了海外学术网络,而当时国内学者却无缘直接使用,无疑是一大憾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倾力合作,2014年终于贡献出水准上乘的《宋会要辑稿》校点本。在喧嚣扰攘的时代里,能够致力于古籍整理研究,沉潜于校正纠谬,可以说是造福学界的“良心活”。这项工作不仅是比对整理,而且渗透着学术研究的心得。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鉴别文本、移正错简、添补缺漏、改正行款。多年整理过程中的甘苦和崎岖,非他人所能想象。2015年,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由陈智超先生领衔,启动了“《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工作,争取整理出一部尽可能符合《宋会要》原貌的《(新辑)宋会要》。这一课题的起步点,建立在剥茧抽丝、回溯源流的基础上。20年前,陈智超先生在《揭开〈宋会要〉之谜》一书的出版序言中说:“(历史的)真相并不一定很复杂。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却非常复杂,并且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个过程,也就是一层一层地拨开当事人以及后人有意无意地所加的种种迷雾的过程。”下决心进行这样一项探索性的整理工作,无疑需要学术的眼光与切实的步骤。

课题组提出的基本目标是:“体例适当、类目清晰、内容完整、接近原貌、便于利用。”这一任务,显然十分艰巨。复原工作是项目的核心,可能也是将来争议集中之处。这里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要“复原”什么?或者说,复原的对象或曰标靶是什么?《永乐大典》中的《宋会要》,显然并非宋代原有书名;这是自后人角度回头去看,取定的一个集合式名称。《辑稿》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却具有与其他辑出著述非常不同的特点。例如,同样自《永乐大典》辑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内容相对集中,且因系编年体例而易于整理编排。《宋会要》则限于《永乐大典》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的体例,被分散收录在《永乐大典》诸多不同的字韵事目中,加之其原有体例并非清晰确定,因而编排复原颇为不易。如果我们承认《永乐大典》收录的《宋会要》是“集合式”的材料群组,就需要分解辨析,先把所谓《宋会要》及其编纂方式看透,把《永乐大典》的收录方式厘清,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考虑到宋代的修史方式,会要作为当时的官方档案,是分阶段编修的。两宋尽管一直在纂修会要,却没有一部贯通前后的、严格意义上完整一体的本朝会要。北宋三部《国朝会要》基本延续相通;而南宋则大多侧重于特定阶段的内容,即所谓“断朝为书”,只有张从祖《(嘉定)国朝会要》和李心传《十三朝会要》(《国朝会要总类》)是相对通贯的。《(嘉定)国朝会要》“自国初至孝庙”,淳熙七年(1180)启动,其实截至乾道;《十三朝会要》应至宁宗朝。这两部会要,都是在前修会要基础上“纂辑”而成。也就是说,宋代的会要,南宋时没有经过“定于一尊”的全面整合重修,其后的元代也未做此工作。换言之,《宋会要》本来并不是完整的“一部”书,它不同于《唐会要》《五代会要》,不是总成于一时;即便说到“原本”,其原始状态本来也是编纂叠加甚至重复参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原”的对象或曰标的,本身即是值得厘清的问题。就大众普遍的认识和预期而言,可以说是“复原《宋会要》”;而就学者切实的目标而言,应该是进行有关宋朝会要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整编一部结构序次相对合理、相对接近宋代原貌的《新辑宋会要》。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奏效的工作。就个人感觉而言,陈智超先生在《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中提出的“合订本”概念,可能是解题与新辑的关键。如若《永乐大典》收录的是南宋后期秘书省(?)整编的合订本,则意味着它并非文献记载的16种宋代会要中的任何一部。宋人对于《国朝会要》的重视,首先因为其中提供了本朝的制度依据,如高宗赵构所说,“《会要》乃祖宗故事之总辖”。当年需要“合订本”,其益处正在于内容会聚相对完备,便于查检、征引。时至今日,若能争取在合订本的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充分地保留整理有序的材料,对学人利用这部史料的方式将有重要的帮助。正如陈先生所说:“如果我们也采用合订本的办法,将每一门的内容按顺序排列,对今后的研究者来说已经足够了。”宋代的合订本,应该是“将各部《会要》的同一门按顺序编在一起”。根据现存材料来看,当时没有打乱原来各门内在的顺序,没有把不同会要记载的事件重新混编叙述,而可能是将不同会要中同一门的内容“叠加”式地抄录在一起(按照门类,抄录了一部内容再抄一部内容。完全重复者,则有删削)。也就是说,在各“门”之下的大单元中会有来自不同会要的若干小单元。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宋会要辑稿》中对同一性质的内容会有不同的概括叙述,而且被分散“剪贴”在不同部分。针对这种情形,本次编纂时“内容相近者两存或多存”,是合理的做法。《宋会要》的深度整理,如陈先生指出,问题的复杂在于构成的复杂。“类”与“门”,是宋朝会要结构性的体现方式。“复原”和“新辑”的入手处,首先在于类和门的把握。这相当于从目录到全文的“绳套”“纲目”“关节点”,值得下足功夫。各部会要虽然内容不同,但在编辑时分类分门的方式有一些前代规制,形成一些基本做法,有其脉络可寻。把握住类和门的分疏与层次,新辑会要的规模和轮廓才能有所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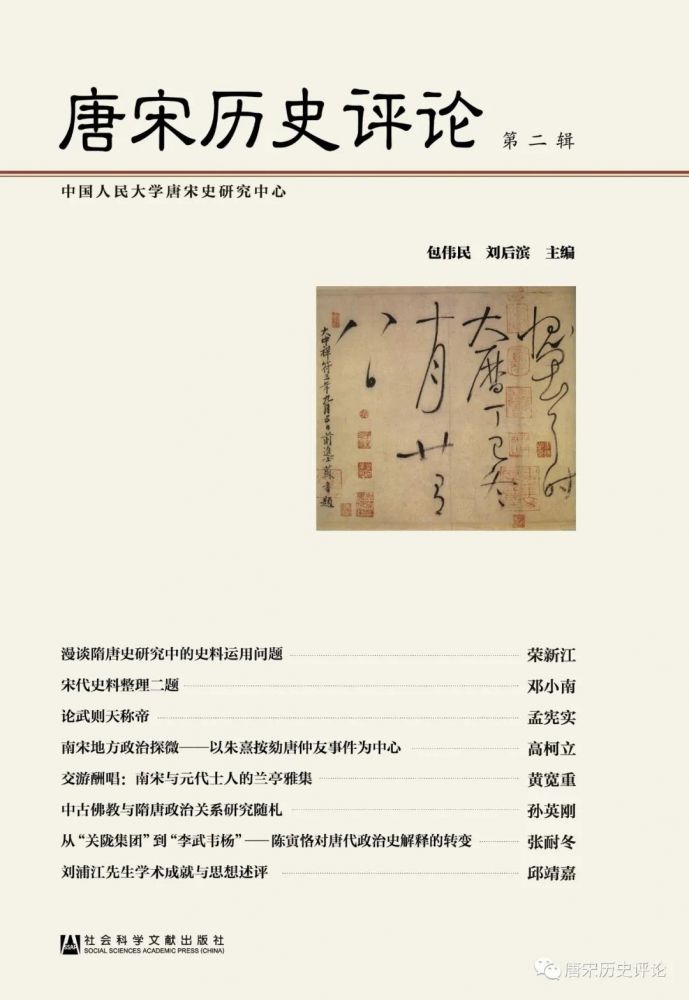
包伟民 刘后滨 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目前,《宋会要》中《职官类·中书门下门》《崇儒类·太学门》以及《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刊出,作为课题组的首批成果,呈献给学界。新近出土的徐谓礼文书和学界熟悉常用的《宋会要辑稿》,是不同类型的两种史料。而其共同处在于,内容都与宋代的制度现实相关,牵涉面广,情况复杂,要肯于下硬功夫,才可能有高质量的整理成果。出土文书及传世文献的整理,并非仅靠“工匠”式的劳作所能奏效,这是对我们知识结构与既有能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整理和研究,二者实在无法分开。《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出版,让学界有机会更为贴近历史现实,也让我们得以从语汇释义、句读、结构分析、制度比较诸方面进行基础性训练,累积制度史研究的底气。相形之下,《宋会要辑稿》的校点与深度整理,更是压力重大的“工程”。课题既为学界提供方便,又要通过集体协作,通过反复比对追索来锻炼学术人才,提升研究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并磨炼出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步步紧逼解决问题的中青年团队,应该是不容回避的任务。这些年来,海内外学人对于宋代基本史料愈益重视,包括对《宋会要辑稿》、《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官箴书、地方志、石刻史料乃至出土文书等的研读课、工作坊愈益普遍。从基本训练开始,夯实基础,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就制度史研究而言,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各类材料的沃土中,才能“活”得了。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认真而非敷衍地对待面前的诸多史料,宋史学界希望可期。 _____
本文出自《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作者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