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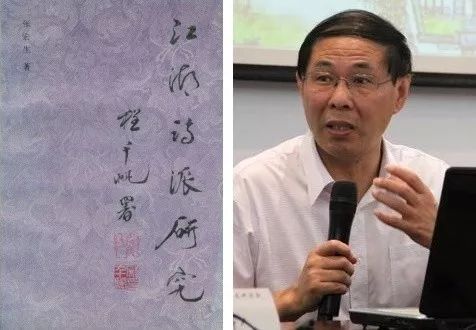
1985年,我开始对江湖诗派进行研究,用了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写成《江湖诗派研究》一书(主体部分于1989年完成),于1995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的美意,要我谈谈“治学门径”,可我每加自我评判,觉得自己还在门外,需要努力学习,争取入门,怎敢谈什么“门径”呢?但转而一想,毕竟自己曾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把其间的得失体会向读者们作一汇报,以求得指教,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选择江湖诗派作为研究课题时,学术界对这一文学现象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1989年,我曾对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江湖诗派的研究作过一个统计,发现除了欣赏和漫谈者外,正式的研究文章只有34篇.其中12篇是考证文字,其余各篇,重点多落在刘过、姜夔、刘克庄和四灵身上,而对这一流派进行宏观研究者,则几乎没有。事实上,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多出现于1987年以后,因此,我从事这一工作时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说,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明确将要勾勒的内容和切入的角度,也就无法为其“定位”。但研究基础薄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这使我从一开始就沉潜于具体作品之中,沉潜于与那一特定时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史料中,不加任何框框地去发现问题和探索问题。 文献的清理或许是研究江湖诗派的最基本的一环。陈起以南宋以来“以诗驰名者”的作品为主,选成《江湖集》,刊行于世,标志着这个诗歌流派作为群体的力量正式出现于诗坛。但这部重要的选本,却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言官指为同情济王,反对史弥远,遭到劈板之祸。此后,虽经历代目录学家和有关学者的努力恢复,但总的来说,这一流派的面貌长期以来是不够清晰的。比如江湖诗派的成员应该怎样确定,多年以前梁崑的《宋诗派别论》把《四库全书》本《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中所收者统统列入,其结论虽然多年来一直被研究者所沿用,但总的来说是不够严密的。我经过广泛的调查,发现残本《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九种江湖诗集,明、清人的影、抄、刊本江湖诗集也有11种以上。这些江湖诗集是陈起的原刻,还是后人对陈起原刻的恢复,或是出自后人的依托,一时尚不容易搞清楚,但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这些江湖诗集,连同当时一些笔记、诗活、书目中的记载(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罗大经《鹤林玉露》、张世南《游宦纪闻》、张端义《贵耳集》、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周密《齐东野语》、方回《灜奎律髓》、韦居安《梅涧诗话》等都记载了陈起原刻《江湖集》的收录情况,可据以恢复),就成为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不过,收入江湖诗集中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江湖诗派成员。因为,陈起当年刊刻《江湖集》,主观上并不一定是开列一份江湖诗派成员的名单,像郑清之这样的宰相,或许就是出于报恩心理而收入的。在明、清人的诸江湖诗集中,或收有北宋人及元人,或收有一些高官,或收有女性诗人,都值得推敲。所以,我从社会地位、活动时间、诸本收录情况、与陈起的唱酬情况以及传统看法等方面,制定了5条标准,在全部诗人中,确定了138人为诗派成员,排除了32人,另有11人生平无考,则不予置论。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可行,还可以讨论,但其文献基础却可以说是尽可能厚实的。经过这些工作,我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了一个尺度,找到了一个基点,明确了一个标准。所以,也许一点点地翻资料、排比文献很枯燥,也许看了很多书与课题有关的东西只是一点点,但回想那差不多整整两年的专门泡图书馆的日子,仍然深切感到它的不可替代性。我有将近10年的时间,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受到文献学的严格训练,这在撰写《江湖派诗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检验,而我也的确深深体会到,文献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千万不能忽视。 江湖诗人在当时和后世,也往往被称为江湖谒客,这是指他们在生活中,每以诗歌为谒具,奔走势要之门,干乞钱财。这一现象虽然很早就有人提出了,但学者们进行研究时,仍然更多地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忽略了其谒客属性的价值。对江湖诗派这个课题,我本来所知甚少,心中也没有数。但中国古代历来有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也一直将其视为重要的治学方法,所以,我在一开始,就没想把这个课题做成纯文学的,而是在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方面的书越读,越感到江湖诗派的文化意义决不低于其文学意义,如果不是超过的话。循着这一思路,我探讨了江湖谒客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等,从而认为,从文化上看,宋代以来,士大夫以其拥有的文化知识参与国政,而较少像唐及先唐那样依据门第,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江湖谒客虽然都是些下层知识分子,但他们在那一特定的时代里,却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他们的种种表现,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理解。 不仅如此,我还更进一步考察了中国的仕与隐的传统,认为江湖谒客作为一个非官非隐的阶层,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而就对宋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过去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这一探索则增强了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 说到这一点,还应该特别谈谈对陈起的意义的认识。每一种在文学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现象都必然有其独特性,找出了这种独特性,也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这无疑是研究者所要着力追求的。我一开始接触江湖诗派,就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成一个如此规模的流派的形成,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专门做了一篇《<江湖集>编者陈起交游考》,又详细分析了陈起为江湖诗人选诗,有目的地组稿刊刻,以及提供陈氏书铺作为活动中心等事实,说明了这位书商在诗派形成中的重要的声气鼓吹和组织联络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这与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刻书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功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我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一种文化史的眼光,对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开拓研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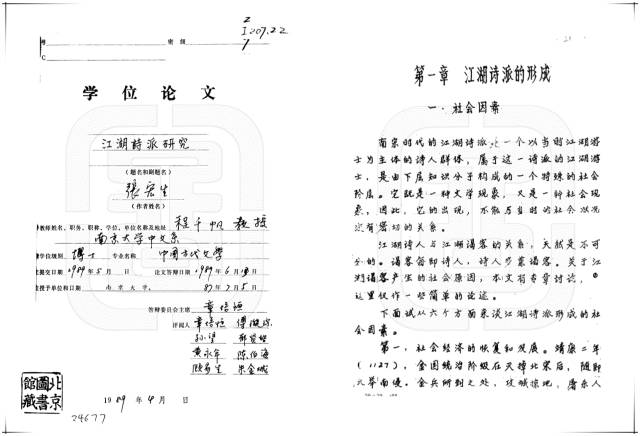
▲《江湖诗派研究》是张宏生教授的博士论文 ▲《江湖诗派研究》是张宏生教授的博士论文 在历来的文学史研究中,对江湖诗派的评价一向偏低。我感到,从情理上来说,一个能够风行诗坛五六十年的流派,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因而绝对不应该给予近乎完全的否定。这一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明确。问题是翻案文章该怎么做。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为了突破以往的传统观念,往往对遗产进行重新清理,纠正成说,争出新义。这当然无可厚非,应该鼓励。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也往往由于对研究对象的偏爱,任意加以拔高或溢美,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我的这一研究涉及翻案之处不少,如何把握合适的尺度,始终是我非常重视的。 如关于江湖诗人的政治态度,一种文学史评价说:“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形式上萎缩、清寒,反映了中间阶层消极丑恶的思想本质。”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意见的根本缺点在于未能认真研究诗人们的作品,并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以《南宋六十家小集》为对象进行了统计,发现在全部5340首诗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这个数字所占的比重,应该说是不小的,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一是对恢复失地的期待,江湖诗人的笔下,几乎写遍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时事;二是对农民生活的关心,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所反映的南宋社会租赋猛增、苛捐杂税繁重的局面,都在江湖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形象的刻画。所以,有理由说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并不缺少政治内涵。 但是,一切作品都有一个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确定了江湖诗中的政治内涵,指出江湖诗人并不脱离现实,这只是理解问题的出发点。下一步要做的,便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价值判断。比如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整个南宋都是如此,并非江湖诗派所独有。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被时代同化,但心灵上的那层阴影却始终无法消除,所以,反映故国之思的作品确实在南宋非常普遍。但我所特别希望指出的是,主题的相同并不能说明没差别。正如整个江湖诗在南宋诗坛上呈现着低潮一样,其中的爱国呼声比起前(如陆游等人)、后(如郑思肖等人)两个时期,也是微弱的。其突出的表现,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因此,在本质上,可以说,江湖诗歌中忧国忧民的政治内涵,在深度、广度和强度上,都较之南宋前期和末期的诗歌为弱。朱熹曾批评当时的诗歌“称今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朱子语类》卷一百九),江湖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也是“衰气”的一种表现。有一种翻案文章,随便挑出一个二、三流作家,选出几首具有政治意义的诗(实则也不过是常见的题材),就宣布有了新发现,认为找到了重新评价的依据,这能说是其独特个性所在吗?也正如情景交融一类的概念,往往被滥用,像两篇题材相同的作品,都是情景交融,莫非彼此就没有区别?所以,我在研究中,涉及翻案之处,一是努力避免爱而讳其恶,二是尽量以特定的标准作同类的比较,这样,或许更能说明些问题。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也许和现在一些希望提升其地位的学者相反,而与传统的意见有所认同。我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按照专业的部署,曾认真精读了《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等典籍。在唐宋诗中,对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诸家也下过功夫。严羽说:“入门须正,立志要高”,这种情形也许无形中影响了个人的审美鉴赏力。所以,我读江湖诗,经常由于自觉不自觉地与诸大家相比,感到不能引起审美愉悦。有时同学之间谈论起来,我就会开玩笑地说,成天读江湖诗对艺术心灵真是一种折磨,还是读那些大家的作品过瘾。但玩笑归玩笑,工作还得做。一个学者应该能够欣赏异量之美,包括不同类型的美和不同方面的美。江湖诗的水平虽然不高,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一定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足够的敏感去发现这一点。 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一是“粗”,我就想,如果不戴有色眼镜,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循着这一思路,我探讨了江湖诗的纤巧之美、真率之情、俗的风貌和清的趣味。第一点从小、巧、纤、细四个方面去谈,说明这是他们创作个性之所在,也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第二点涉及他们对社会、人生以及个人欲望的直率表达,并认为这种感情影响了其作品的结构、句式、修辞和声律等;第三点从题材、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叙述了其俗的风貌,并指出这一点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受到当时蓬勃兴起的市民文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第四点论述了江湖诗语言之清新、境界之清寂、风格之清瘦和辞气之清和,并说明了其中的深层内涵是对晚唐诗风的学习和对江西诗风的反拨。通过这几点的探讨,一方面,我想揭示江湖诗派在宋代诗坛上的独特意义,另一方面,也想说明,所谓研究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宏观指导意义,但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通用的,换句话来说,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特点,又能很好地加以阐发,那么你就算是掌握了最合适、最恰当的研究方法,你的研究也就能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去钻研原始文献,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另外,我还要简单说一下我在具体操作时的某些考虑。有时候,同行之间谈起来,常说先唐文学患在材料太少,宋以后文学患在材料太多,这当然不足深论。但由于我这十几年来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宋以后的,所以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感受,除了材料的繁杂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定位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后代的文学,必须对前代文学有着相当的了解,即使不说是精深的了解的话。否则,你说到的某种特色,怎么知道在前人那儿没有已成陈迹呢?所以,比较的方法是不可缺少的。我在这部书里,考虑到江湖诗派与中晚唐姚贾一派颇有渊源,所以常常以此为基点,与唐代作家作纵向比较;考虑到江湖诗派是打着反对江西诗风的旗号走上诗坛的,所以把与江西诗风的比较放在重要位置;又考虑到江湖诗派在整个南宋诗歌的发展中处于低潮,所以也注意与南宋前期诸大家作比较,以说明诗风的发展变化。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受到学力的限制,或者难免有时强人以就我,表现得过于主观。我觉得这个问题对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后段文学也许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所以在这里提出来。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