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沈松勤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唐宋文学、中国词学等研究方向取得显著成绩。
提要:舒亶在履职御史期间,弹劾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指斥乘舆”,伙同同僚炮制“乌台诗案”,被后人视为“甘心为人鹰犬”的“小人”;因恶其人,故陋其词,在当代诸多宋代词史论著中,也几乎不及其词。其实,舒亶的这一政治行为,并非道德层面的“小人”人格所驱使,而是基于作为御史的职责与作风,以及特定时期的政治需求,具有深层的历史性内涵与意义。舒亶在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晏几道诸家小令外,以其“极为清婉”的七绝入词,开辟新的创作路径,别具一格,在令词演进或词的雅化历程中,不乏推进之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舒亶 “乌台诗案” 令词特色 词史地位 以人废言,或以道德绑架文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其中被废之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无论其当下的所作所为,抑或以后世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都是十恶不赦的小人;一种是出于其当下历史的某种需求而不得不为,却被后世视为了无道德底线的小人。北宋词人舒亶属于后者;而在后世学者看来,舒亶小人形象主要体现在炮制“乌台诗案”的行为中,故历来恶其人,陋其词。近三十余年来,学界虽开始关注舒亶及其词,但对其小人形象的历史内涵及其词的历史地位,尚待进一步认识。 一 舒亶小人形象的历史内涵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试礼部第一。元丰年间,权监察御史里行,徽宗时,起知南康军,累官至龙图阁待制,六十二岁奉命讨伐蛮叛,收复二州,边功卓著,次年殁于军中。有辑本《舒懒堂诗文存》三卷、《信道词》一卷。元丰二年(1079),舒亶伙同御史李定、何正臣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炮制并勘治“乌台诗案”,为人唾弃,所以“世知其为凶狡无赖,而不知皆留意文学者”,导致“文集百卷,存者千百之什一耳”。(张寿镛《舒懒堂诗文存序》,《舒懒堂诗文存》卷首,《丛书集成初编》,第101册,第941页。)丁绍仪又说:“因其倾陷坡公,己亦不免被斥,恶其人,并陋其词。此如蔡京之书,严嵩之诗,马士英之画,初不让蔡君谟、王元美、董香光诸公。今词坛艺苑中,绝无齿及者。在小人得志之秋,率意径行,非不炫赫一时,卒之身败名裂。”(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7页。)但也有论者因舒亶词艺之高而为之动心,难禁评论的冲动,但其评论的动力却来自对词体的维护。如清初王士禛说: “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舒亶语也。钟退谷评闾丘晓诗谓:“具此手段,方能杀王龙标。”此等语乃岀渠辈手,岂不可惜。仆毎读严分宜《钤山堂诗》至佳处,辄作此叹。(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78页。) “空得”二句是舒亶《菩萨蛮》的歇拍,因其警策,王士禛深赏之,但又因出自舒亶之手而惋惜不已,并将舒亶为人与杀害王昌龄的闾丘晓,以及奸佞严嵩相提并论。近人易大厂集舒亶、苏庠、曹组词为《北宋三家词》,朱孝臧点评。朱氏认为:“舒亶乃奉权邪,密意与李定锻炼坡翁诗案者。览其文辞,亦非士俗下才,乃甘心为人鹰犬,遂自侪于蟊贼鬼蜮,哀哉!复何及矣。”所以评舒亶《虞美人》“芙蓉落尽天涵水”一阕云: 如此等雅词,倘出太虚、无咎之手,便觉神骨俱仙,乃辱以舒信道乎。 又评舒亶《一落索》“正是看花天气”一阕云: 亶当日考讯坡公,退而曰:“子瞻真天下才。”亶能隐服坡公,固应有此吐属。卒甘心为小人,故君子尚德,浮华有文,非道所贵。(朱祖谋《彊村老人评词》,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73页。) 由此等等,虽与王士禛一样突破了“以人废言”的陋习,对舒亶的词作了不低的评价,体现了评论者应有的文学价值的判断能力,但均以为舒亶是缺德的小人,玷污辱没了优美的词体,并为此痛惜不已,深致哀叹。这看似维护词的尊严,实则使词体包括对词的文学判断淹没在人云亦云的道德判断中,变得缥缈虚无。 据载,舒亶“博闻强记,为文不立稿,尤长于声律。程文太学,词翰秀拔,为天下第一”;(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97页。)又“生而魁梧,博闻强记,为文不立稿,登治平二年进士第,授台州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其民慓悍,盗夺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者至亶前,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以令投檄而去。留诗云:‘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丞相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74号,第5165页。)可见舒亶才思敏捷,颇具文学才华,但其为官,却属于干吏,甚至不乏酷吏性格与作风,与其秀拔的文学才性判若天壤。然而,舒亶参与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炮制“乌台诗案”,却与他的酷峻性格并无内在联系,而是其台官的身份与责职所致。 在宋代,履职御史与谏院的官员合称台谏。作为帝王的“耳目”,宋代台谏因拥有“风闻言事”的特权,养成了随意弹劾官员的习性。譬如:在“濮议之争”中,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遵仁宗遗旨,追尊英宗生父赵允为“皇亲”;司马光、王珪、范纯仁等台谏官则主张称“皇伯”,引起了震动朝野的一场政坛风波。司马光等台谏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上疏指控韩琦“交中官”,欧阳修“盗甥女”,无中生有,诋毁政敌,侮辱对方人格,况且“交中官”又是杀身重罪。在庆历以后的北宋朋党之争中,台谏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相当程度上毒化了政治,阻碍了文学与学术的发展。(说详拙文《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27—45页。)不过,舒亶、李定等台谏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并非“风闻言事”。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之前,作《上神宗皇帝书》,指陈新法之非;(详见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9—741页。)在通判杭州期间,神宗命前往两浙访察的沈括探望苏轼,了解其在杭行实。在探望中,沈括得到苏轼“手录近诗一通”,回京后,将苏诗上呈神宗,声称“词皆讪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36页。)所谓“近诗”,就是苏轼在杭期间所作《钱塘集》中之诗。《钱塘集》继承儒家诗学中“刺”的传统与主张,批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已退居金陵,神宗全面主持变法新政,而新法的弊端日趋严重,反对新法的声音也日趋强烈,加诸西北边事的困扰,给试图通过实施新法,富国强兵,解决西北边事的神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按:熙宁新法由王安石具体策划,得到神宗的倾力支持,王安石对内变法,神宗对外用兵,互为倚重,是熙宁新政的两个重要侧翼。据王铚记载,“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东坡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默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自熙宁三年始,为了复河潢、取西夏,连年发兵西征。十余年的西边战事,神宗还对前线将帅亲自一一发令指挥。陈师道《古墨行》:“睿思殿里春夜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细字答边臣,万里风云入长算。”任渊注:“元祐中,苏辙等上所编《神宗皇帝御制集》。内四十卷,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哲宗为之序曰:其指授诸将,应变制宜,虽在千万里外,而尽得其形势之要;先后缓急之机,皆如在目前,而无遗画云。”(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6—187页)从中可见神宗之用心。)这是台谏炮制“乌台诗案”的背景和前提。在儒学正趋向中兴的北宋,以诗歌作为证据,治诗人之罪,显然是思想领域里一种反动,但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勘治“乌台诗案”,却不失为抑制异论,保证新法实施的一种举措。因此神宗不惜背负以言罪人的恶名,以“特欲申言者路”(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载,苏轼刚入狱,直舍人院王安礼向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神宗却说:“特欲申言者路。”并告诫王安礼:“第去,勿漏言。”)——怂恿台谏,广开言路为由,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换言之,勘治“乌台诗案”既是台谏的权益与职责,又出于神宗新政之需。在立案后的三堂会审中,御史台审定苏轼讥讪新法是“指斥乘舆”,属于《宋刑法》“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恶“大不敬”,应予“特行废绝”;大理寺却遵循法理,判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应予赦免;审刑院也支持大理寺的判决。然而,苏轼的生死予夺,无论御史台抑或大理寺,还是审刑院,均无权决定。苏轼贬谪黄州,最终取决于神宗超越法理的“特责”。(朱刚根据宋代“鞫谳分司”制度,详细条理了“乌台诗案”的审与判的具体情形,并以审刑院“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判决为依据,对《宋史·苏轼传》关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糵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的表述作了纠正,认为苏轼被贬黄州并非出于神宗的“独怜”,恰恰相反,是神宗超越法理而采取的一种“特责”即特别惩罚。详见氏著《“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87—95页。) 上述不难看出,舒亶参与指控苏轼,炮制“乌台诗案”的历史性情境与意义;而“历史性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人无法脱离历史,因为他正在历史之中、并通过历史而成其所是的东西”。(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2页。)台谏炮制“乌台诗案”而“成其所是的东西”就是帝王的“耳目”形象,以及为弊端日现的神宗新政清除异论的功能。这是舒亶小人形象中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对此,舒亶也不乏反思。其《浣溪沙·和仲闻对棋》云: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郞闲去忆鏖兵。何方谈笑下辽成。(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6页。) 元丰六年(1083),舒亶因“不晓法意”被劾,追官停勒,(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己酉”条:“诏:通直郎、试御史中丞、权直学士院舒亶免除名,止追两官勒停……亶不晓法意,误谓当别置录目,因言尚书省不置录目,不奉法。尚书省办论既明,亶犹固执。他日,上谕都省,令取亶台中所置录目,必无之。亶果不置,仍以他簿书增写‘录目’字与寮属书押送都省,坐此被劾。”)退居故里近二十年之久。该词作于退居故里期间。作为干吏,舒亶能恪守职责,且行事果断,不乏政绩,颇得神宗赏识。据载,“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为集贤校理,以上批‘亶优于辞学,详于吏治’,自丞属宪府,能以先后左右朝廷政事为已职责故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16页。)在退居故里以前,舒亶有两次“战争”被后世视为“小人”行为:一次是以“朝廷政事”为原则,弹劾于己有恩的张商英;一次就是参与指控苏轼,炮制“乌台诗案”,尤其是后者,不仅治了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之罪,而且惩罚了与苏轼有关联的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等一众官员,予以罚铜处分,成了其小人形象最为突出的标志。上列《浣溪沙》开篇以“对棋”比喻曾经参与的政治斗争。“几人心手斗纵横”二句,则从职责与人情两个方面,反思自己,包括自己以台谏的身份参与勘治“乌台诗案”。从私人情感上,舒亶与苏轼并无宿仇新恨,且如前引朱孝臧语所谓隐服“子瞻真天下才”;在公职或责任上,则须恪守台谏的职责,遵从圣意,指控与法办苏轼,最终作为台谏的“心手”胜出,成就了现实政治中的“所是”,充满人性温度的情却无能为力,被扼杀于无形,令之感慨不已。这是身处无法脱离当时“本无情”的“战争”而参与打击他人,后也被他人打击的亲历者所发出的感慨,局外人是无法品咂其中的况味的。闲居故里,舒亶对“本无情”的政治已深感疲倦与无奈,即其《与吕少府帖》所说:“向以狂妄见黜于朝,毁于乡人,身自退宿,不求闻达也。”(曾枣庄等编《全宋文》卷二千一百八十,第1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等,2006年,第75页。)舒亶罢官后,迁居鄞县月畔湖,名其居曰“懒堂”,并自号“懒堂”,其用意也就是“不求闻达”。下片“谢傅老来思别墅”二句,化用谢安、杜牧典故,书写经历政治上升降沉浮后的闲适心境,也昭示了作者告别往日的“战争”,祈求回归人情、游艺人生的心声。 从无法摆脱政治斗争而参与指控他人到“胜处本无情”的自我反省,再到被政敌打击后“不求闻达”而祈求回归人情,是解读舒亶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和途径。假如罔顾这一点,将炮制“乌台诗案”与苏轼被贬黄州,简单归咎于舒亶等人的“邪恶”本性,是小人迫害君子的产物,显然失诸偏颇;进而恶其人,陋其词,或因佳词出于舒亶之手而深感痛惜,为之哀叹,更非词学研究应持的态度。 
北宋文人与党争 沈松勤
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二 舒亶词的历史地位 在北宋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中,炮制文字狱,不仅是小人,而且也是君子打击政敌常用的手段,成了司空见惯的一种政治现象。(详见拙著《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因此,当时士大夫社会指斥文字狱的炮制者主要基于政治立场而非道德标准。舒亶参与炮制“乌台诗案”后,并无来自纯粹的道德层面的评价与抨击。约至南宋刘克庄,舒亶在道德层面的小人形象开始确立。刘克庄出于自己的《梅花》诗被炮制“梅花诗案”的经历,作《病后访梅九绝》,其三云:“区区毛郑号专精,未必风人意果然,犬彘不吞舒亶唾,岂敢与世作诗笺。”(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千四十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276页。对舒亶的人品与文品一并予以否定,但这与他自身陷入“梅花诗案”不无关系。)痛斥舒亶为猪狗所唾弃,不啻道德人品之低下。在此之前,舒亶却作为词坛“名公”受人尊重。 绍兴十六年(1146),曾慥所编《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问世。该书共选录了欧阳修以来50家“名公”之词,为宋人选编宋词而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曾慥说:“余所藏名公长短句,裒合成编,或先或后,非有诠次,多是一家,难分优劣,涉谐谑则去,名曰《乐府雅词》。”又说:“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按:欧阳修)词,今悉删除。”(曾慥《乐府雅词引》,金启华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2页。)可见其心目中的“雅词”并不包括“艳曲”或“涉谐谑”之作。据此,《乐府雅词》则又是较早以选人存史的方式倡导“复雅”的一部词学文献,旨在昭示北宋词的“复雅”历程。其中不录柳永、晏殊、晏几道、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词,(按:《乐府雅词》不选苏轼词,也许因为曾慥同时编有《东坡词》《东坡词拾遗》。)却选录舒亶词48首之多,舒亶词也赖此得以传世。暂且不论这一取舍是否合理,但至少表达了对舒亶这位词坛“名公”的认可与敬重,以及舒词在雅化历程中的地位。 《全宋词》据易大厂校勘劳权抄本《信道词》,录舒亶词50首。其中慢词3首,余皆小令。诚如薛砺若所说:“舒亶词仍具《花间》神韵。”(薛砺若《宋词通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譬如《菩萨蛮·别意》: 江梅未放枝头结,江楼已见山头雪。待得此花开,知君来不来。 风帆双画鹢,小雨随行色。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4页。) 代言女子盼归,是温庭筠以来“花间词”最为常见的一个主题,该词虽为代言,但突破通常运用的以香艳为氛围的闺阁空间,将女子“待得此花开,知君来不来”的盼归心绪与“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的别后心境置于宽广的江天飘雪、楼阁梅枝、画船风帆等自然清新的景象之中,虽不失“《花间》神韵”,却少了一份《花间》绮丽,多了一种自然清新,使词的意境变得清雅深婉。而将离情与盼归情思置于宽广清新的空间,营造意境,则是舒亶小令的一大特色。如《菩萨蛮》云: 画船搥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知君何日同。(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62页。) 该词不仅跳出了香艳的闺阁,而且波澜开合,曲折层深,摇曳多姿。“画船”二句在一“催”一“留”中,传达欲去未忍、欲留未能的矛盾心绪。“去住”二句借江潮这一自然景象,诉说行者的惜别情愫:尽管去留两难,情有不堪,但江潮已欲平岸,征棹出发在即,除却挥泪而去,别无选择。“江潮”二句则又接续江潮景象,抒发送者的离情别绪:江潮虽去,犹有来时;离人一去,则难重逢。歇拍二句呼应开篇,将惜别之情与盼归之意寄托在杯中,并出诸“知君何日同”的怅问,情韵尤为深长。 舒亶小令除个别如《木兰花·次韵赠歌妓》外,绝大多数以清新的景物替代香艳的闺阁,形成了清雅深婉的体性特征,而且多数又淡化或模糊了代言体的女性身份。如《菩萨蛮》: 杜鹃啼破江南月,香风扑面吹红雪。赋就缕金笺,黄昏醉上船。 年华双短鬓,事往情何尽。明日各天涯,来春空好花。(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62页。) 从“明日各天涯”二句观之,既可视为代言女子的离别情怀,也可视为作者的自我言说,导致抒情主体的模糊。抒情主体的模糊,则使“花间”小令在保持原有语体与体性特征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抒情空间。该词不仅冲破了闺阁氛围的限制,而且也少了上述《菩萨蛮》“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的女性情态,全由自然景象兴起,抒发个体的生命感伤,深化了小令的体格内涵,不啻清雅深婉。沿着这一书写路线,舒亶以传统的“花间”小令自言情思,也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 从作者代言女性情感到言说自我情思的转变,早在李煜笔下就已完成,在晏殊尤其在苏轼的笔下得到全面的体现。但舒亶小令在言说自我情思中,既无晏殊的浓丽富贵与情理圆融,又无苏轼“诗人之雄”的创设,而是在吸纳与变化“花间词”的构成要素的同时,融入了其七言绝句醇远清疏的意境格调。 现存舒亶126首诗,多半为七言绝句。张邦基为其中“香满钓筒萍雨夜,绿摇花坞柳风春”“空外水光风动月,暗中花气雪藏梅”“宿雨阁云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万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见松高”等一系列“警句”所折服,由衷感叹:“信道清才而诗刻削有如此者!”又认为舒亶《村居》“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逼肖“极为清婉,无以加焉”的王安石七绝。(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7、180页。)舒亶在政治上被列为新党,在文学上被视为王安石门人,其七言绝句与王安石晚年于自然景物寄托情思的清婉雅丽、精工隽永的七绝多有近似之处。张邦基的品鉴说明了这一点。而纵观舒亶的小令,也主要以清丽的自然景象为画面;换言之,舒亶小令以清新的景物替代香艳的闺阁,就是以绝句的作法写小令,将其绝句清雅深婉的意境与格调融入小令之中。上述诸词均体现了这一点,再看其《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0页。) 张宏字公度。据舒亶《游山题壁记》,建中靖国辛巳年(1101),“鄞江张宏公度、吴升潜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独辛巳晴和,登山为斗草之剧余,辄雨雪……皆欲往而不果,而公度约余道奉川境上游安岩,且不复至,亦遗憾焉。”(舒亶《戊辰游山题壁记》,《舒懒堂诗文存》卷三,民国《四明丛书》本。)故舒亶写了这首《虞美人》,表达与张宏的惜别之情。上片“芙蓉落尽天涵水”二句,水天一色,沧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清隽深邃之气象;“背飞双燕贴云寒”二句,在燕子成双,背抵寒云的景象中,目送友人离去,犹如其绝句《村居》“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写景达意,“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2页。)下片“浮生只合尊前老”二句,说友人远去,只能与酒相伴,并将人生离别写成如同铺展无垠的雪地般无声的悲凉;“故人早晚上高台”二句,在写对友人的期许的同时,化用范晔赠梅诗句,寄托情思。全词所运用的语象常见于《花间集》,其体性虽“仍具《花间》神韵”,但其情思却出诸水天一色,云燕渐远,一派白雪无垠的醇远清疏的景象;换言之,在吸纳“花间词”绮丽语体与婉约体性的构成要素中,注入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在江山自然之景中,抒发人生境遇的“不得已”之感,即所谓“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王幼安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页。)且意境空灵浑成,清雅深婉,难怪朱孝臧读之“便觉神骨俱仙”(引见上文);而这种意境格调则常见于舒亶的七言绝句。 舒亶七言绝句的意境格调赖以形成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锻字炼句。舒亶《题灵桥》诗说:“沧海一时传丽句,天才真实杜陵翁。”对杜诗仰慕不已。杜甫诗境自然浑成,虽不见刻削之痕,但“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5页。)刻削而又自然浑成。舒亶在仰慕杜诗的同时,其绝句也取径杜甫诗“丽句”的锻字炼句之法。在取径中同样“尤工于用字”而不见雕琢之迹,故“丽句”即警句频出,令张邦基赞叹不已。这一锻字炼句之法同样被用于其词意境格调的创造,如上述《菩萨蛮》“杜鹃啼破江南月,香风扑面吹红雪”,《虞美人》“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又如《菩萨蛮》“画檐细雨偏红烛,疏星冷落排寒玉”,同调“斜日下汀州,断云和泪流”,同调“楼前流水西江道,江头水落芙蓉老”,同调“愁斛若为量,还随一线长”,同调“露湿井幹桐,翠阴生细风”;(以上见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364页。)《蝶恋花》“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木兰花》“点衣柳陌堕残红,拂面风桥吹细雨”。(以上见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65页。)在现存舒词中,几乎每首都有经过锻字炼句而形成的此类“丽句”。锻字炼句不仅止于“一字得力,通首光彩”,(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卷四,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59页。)而且如胡仔所说:“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06页。)质言之,锻字炼句是整首词的意境格调赖以形成的重要一环。舒亶将其七言绝句所运用的刻削而又自然浑成的锻字炼句之法,用于小令的意境格调的创造,在唐五代北宋词坛并不多见。 诚然,舒亶词“思致妍密,要是波澜小”,(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但舒亶在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晏几道诸家的小令以外,以其“极为清婉”的绝句入词,开辟了新的创作路径,使其词在“仍具《花间》神韵”而不失“本色”的同时,赋予空灵浑成、清雅深婉的新的意境格调,别具一格,推进了小令的发展,既为北宋小令繁荣的标志之一,又为南宋雅词导夫先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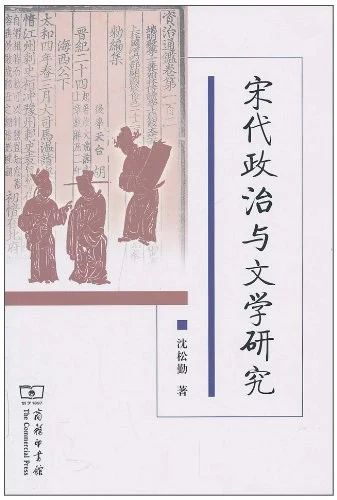
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 沈松勤
商务印书馆2010年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3年第4期
*注释请参照原文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