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軍
李建军(1974—),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后、宋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州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儒学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宋代浙东文派研究》等。 提 要:宋元時期“話本”一詞,作為説話伎藝的文本化產物,應釋為“故事傳本”,即將故事按照一定次序組織起來的相對完整的口頭或書面傳本。宋元話本存在着從口頭傳本到書面文本,從簡本到繁本,從脚本式准話本、録本式話本到擬本式話本的演進態勢;擬本式話本還會經歷從文言擬本到白話擬本的發展脈絡。脚本式准話本,指尚無話本體式特徵但有為説話伎藝而進行改編形跡的小説文本;録本式話本,指説話内容的記録加工本,從體式而言參差不齊但大都有説話伎藝痕跡;擬本式話本,乃是文人模擬説書口吻和話本體制,用文言體或者白話體編創而成的文本。從脚本到録本再到擬本,體現了話本從雛形到成型再到被模擬的演進邏輯,呈現出話本從粗糙到精緻、從民間發育到文人模擬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宋元話本 形態演進 脚本式准話本 録本式話本 擬本式話本 話本作為説話伎藝的衍生品,濫觴于唐五代,興盛于宋元,流衍於明清,逐步開拓出白話小説的新天地,在中國小説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宋元話本作為話本史上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作為“小説史上的一大變遷”[1],吸引了衆多學者的目光。[2]目前學界在宋元“話本”的“所指”、宋元話本的文本形態等方面尚有争議,筆者結合敦煌文獻中的唐五代説唱文本,力圖從“源”與“流”的視角對宋元話本的文本形態演進進行新的探討。 一、宋元“話本”應釋為“故事傳本” 説話是以説為主的敍事性伎藝,屬於口傳敍事,而所“説”之“話”的文本化即形成為話本,話本則橫跨口傳敍事與書寫敍事。學界關於話本的“所指”,有多種意見。 敦煌文獻中已出現“畫本”一詞。敦煌遺書中有一篇成于唐代的講唱韓擒虎故事的文本,原本没有題名,結尾處云:“畫本既終,並無鈔略。”[3]不少學者指出此處“畫本”即為“話本”的同音借用,[4]該文的整理者將此文擬題為《韓擒虎話本》。該文結尾處的“畫本”(“話本”)顯然指故事的書面文本。宋代文獻中已正式出現“話本”一詞,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云: 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虚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5] 吴自牧《夢粱録》“百戲伎藝”條云: 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更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鏃,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升、王閏卿等,熟於擺佈,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耳。[6] 後者承襲前者而有補充完善,比前者更加詳盡明白,更便於作為討論的依據。 濫觴於上述材料的“話本”一詞應如何釋義,還有與之相關聯的另一問題,即現存宋元話本是底本、録本還是編創本,學界衆説紛紜。關於前一問題,學界目前主要有“説話人底本説”、“故事説”、“故事書説”(“故事本子説”)、“故事的口傳之本説”等説法。 “説話人底本説”源於魯迅先生。其《中國小説史略》認為:“説話之事,雖在説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7]他又在《中國小説的歷史變遷》中指出:“那時操這種職業(筆者按:指‘説話’)的人,叫做‘説話人’;而且他們也有組織的團體,叫做‘雄辯社’。他們也編有一種書,以作説話時之憑依、發揮,這書名叫‘話本’。”[8]魯迅先生明確將“話本”釋為“説話人憑依的底本”。後來不斷有學者對魯迅先生的“底本説”進行修正、發展和完善。王古魯先生《話本的性質和體裁》將底本分為“原來的底本”和“文人潤飾過的底本”[9];胡士瑩先生《話本小説概論》將“話本”釋為底本,而將記録加工整理本稱為“話本小説”[10];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説研究》一方面認同話本是説話人的底本,另一方面又指出話本有“提綱式的簡本”和“語録式的繁本”之分,[11]實際上是將“底本”的外延擴展成了“書面文本”。王慶華先生《“話本”考》認為: “話本”一辭在古典文獻中的意義主要有如下三點:(1)作為專有名詞,“話本”在宋元時期指“説話”、影戲、傀儡戲、戲文等伎藝的底本,明清時期引申出“伎藝的故事内容”、“通俗故事讀本”,主要用於介紹伎藝和説話人“做場”時對演出内容的説明。(2)作為社會普通用語,元明清三代一直沿用“話柄”(人們的談論物件)或“舊事”等意義。(3)雖然“話本”一辭在古典文獻中有説話人的底本之義,但古人却從未在“底本”的意義上指稱現存的“宋元話本小説”,現存的“宋元話本小説”並非當時“説話”伎藝的底本。[12] 指出“‘話本’在宋元時期指‘説話’、影戲、傀儡戲、戲文等伎藝的底本”,將“説話人的底本”延展為“伎藝的底本”。聯繫《都城紀勝》和《夢粱録》的記載,王先生的延展有合理性。另外,王先生對於“話本”明清時期引申義以及作為社會普通用語涵義的論斷,對於現存宋元話本與當時説話伎藝底本關係的論斷,都是真知灼見。 “故事説”源于日本學者增田涉先生。他於1965年發表《論“話本”一詞的定義》,認為漢語文獻中的“話本”一詞除偶爾可以解釋為“故事的材料”外,多數時候只能解釋為“故事”。[13]中國學者施蟄存、蕭欣橋、張兵等先後撰文對增田涉的觀點進行質疑,認為“故事説”難以服人,“底本説”仍然成立。[14] “故事書説”(“故事本子説”)是我國學者在揚棄魯迅、增田涉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的新見。周兆新先生《“話本”釋義》明確指出:“不把話本解釋成説書藝人底本,而是解釋成故事書或故事……宋元明清時代‘話本’一詞的‘話’指故事,‘本’指書本,話本即故事書,其轉義或引申義乃是故事。”[15]劉興漢先生《對“話本”理論的再審視——兼評增田涉〈論“話本”的定義〉》認為“話本”一詞雖在宋元明白話短篇小説的例句中,往往既可解作“故事”又可解作“故事書”或“故事本子”,而在有的例句中則只能解作“故事書”或“故事本子”,因此魯迅把“話本”解釋為“説話人的底本”是不錯的。劉先生進一步認為:“現存宋元話本,雖然有粗簡與詳細之别,有的或許是説話人自己編寫的底本,有的是説話的記録,還有的或許經過書會才人的加工,但它們却都可以充當説話人的底本。”[16]顯然,劉先生是把“底本”外延擴展成了“本子”,其“故事書説”(“故事本子説”)其實也是魯迅“底本説”的修正和完善。同是“故事書説”(“故事本子説”)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周先生和劉先生對“底本説”的觀點却迥然不同,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原因在於兩者對底本的理解有嚴、寬之别。 “故事的口傳之本説”是宋常立先生在《“話本”詞義的口頭屬性》提出的新觀點。該文認為:“‘話本’一詞只用于藝人的口頭表演語境之中,‘話本’之‘話’專指‘口傳故事’,‘話本’之‘本’指師徒傳承的‘口傳之本’。‘話本’作‘口傳故事’解,體現了‘話本’一詞的伎藝性,一旦脱離伎藝表演的語境,宋人就不用‘話本’一詞而使用作為書面語的‘故事’一詞。將‘話本’理解為書面的文本,是明以後人的引申或誤讀。”[17] 筆者認為,“故事説”用明清時期的引申義覆蓋宋元時期的原始義,有以“後”概“前”之嫌疑,難以采信;“説話人底本説”和“故事書説”(“故事本子説”)僅僅將“話本”釋為書面本子,“故事的口傳之本説”又僅僅將“話本”釋為口傳本子,這些觀點可能都有以偏概全之缺失。筆者認為,可以充分吸收上述觀點的合理内核,將宋元時期的“話本”一詞釋為“故事傳本”,即將故事按照一定次序組織起來的相對完整的口頭或書面傳本。其中“話”指故事[18],“本”指傳本[19],兩者為表裏關係,“話”為“本”的“裏”(内容),“本”為“話”的“表”(載體),“話”為敘述的内容,“本”為敘述所形成的傳本。“話本”既包括故事的口頭傳本,也包括故事的書面文本;既包括故事的底本,也包括故事的録本、加工整理本乃至書會才人編創本。 按照上述釋義,宋元文獻中的“話本”一詞就可得到更為圓通的解釋。比如《夢粱録》中的“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此句中前半句講傀儡戲的故事内容(“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後半句用“話本”一詞講傀儡戲的故事形態(“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根據前後語境,此處“話本”不應釋為“故事”,而應釋為故事的表達形態和文本形態。同時,此處“話本”如釋為“底本”,雖比釋為“故事”稍好一些,但指稱範圍過於狹窄和具體,關鍵是排除了口頭文本的可能性,如此一來恐怕未必合於事實。總之,仔細推敲《夢粱録》中的這段話可以發現,將“話本”釋為“故事”或“底本”,都不是很合適。此處“話本”如果釋為“故事傳本”(既可能是口頭傳本,也可能是書面文本,其中口頭傳本的概率更大),則語意貫通。《夢粱録》還提到弄影戲,指出“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其中的“話本”釋為“故事傳本”(口頭傳本可能性更大)也更為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夢粱録》這段話中的兩處“話本”,一指傀儡戲的“話本”,一指弄影戲的“話本”,而從“(傀儡)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和“(弄影戲)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推斷,講史、雜劇、崖詞等敍事性伎藝的故事傳本大概也可稱為“話本”。這樣一來,傀儡戲、弄影戲、講史、雜劇、崖詞等敍事性伎藝的故事傳本都可稱為“話本”。因此,宋代“話本”可能是敍事性伎藝的故事傳本的通稱,既可用來指稱説話伎藝產生的口演故事的傳本,也可用來指稱傀儡戲、弄影戲、雜劇、崖詞等敍事性伎藝產生的表演故事的文本。元代鍾嗣成《録鬼簿》“陸顯之”條下注云:“汴梁人,有《好兒趙正》話本。”[20]此處“話本”解釋為“故事”肯定不通,解釋為“説話人的底本”也不好,因為陸顯之並不一定是“説話人”,其撰成的《好兒趙正》可能已不是粗糙的“底本”,而是比較成熟的故事傳本。元刻本《新編紅白蜘蛛小説》殘頁是現存最早的小説家話本的刻本,篇末有“話本説徹,權做散場”八個字,《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宋元舊篇也有不少此類套語,如《陳巡檢梅嶺失妻記》、《簡帖和尚》、《合同文字記》等。其中的“話本”解釋為“底本”肯定不通,解釋為由“底本”之義引申出的“伎藝的故事内容”[21]雖然講得通,但也不是非常貼切。而如果將此“話本”解釋為“故事傳本”(此處應該是故事的口頭傳本),那麼“話本説徹”就是指該故事的口頭傳本已經説完,這樣一來,語意通貫,毫無滯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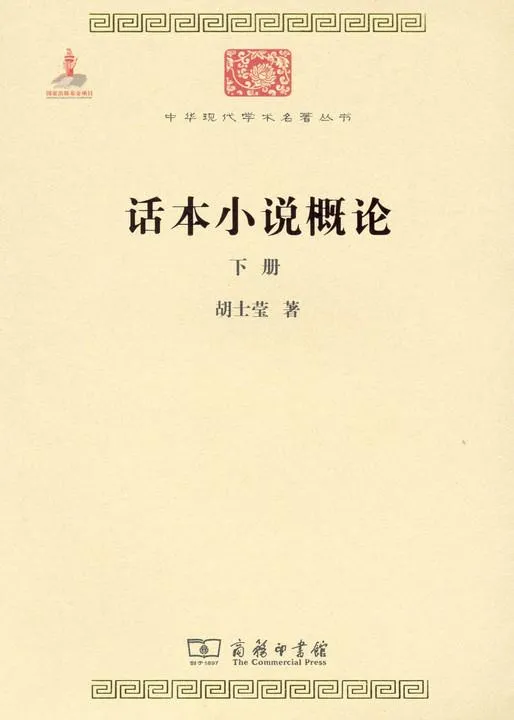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