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略有改动,以原文为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9ZDA200)的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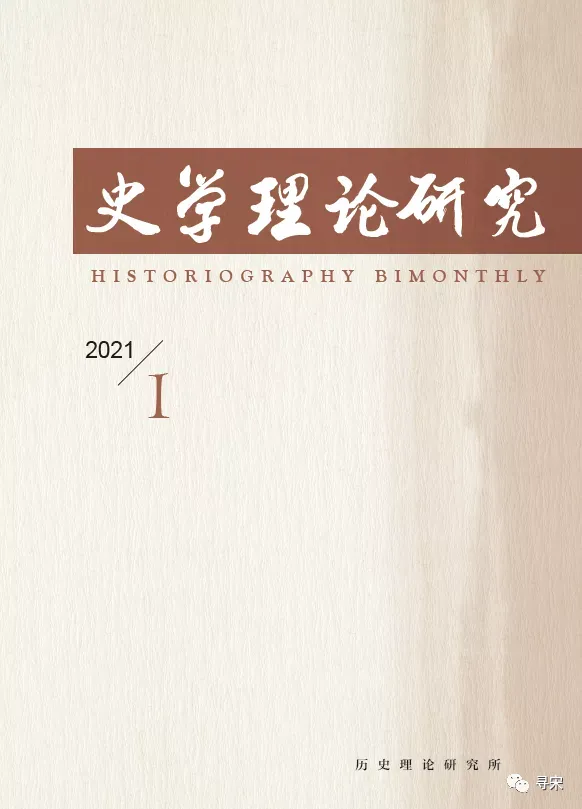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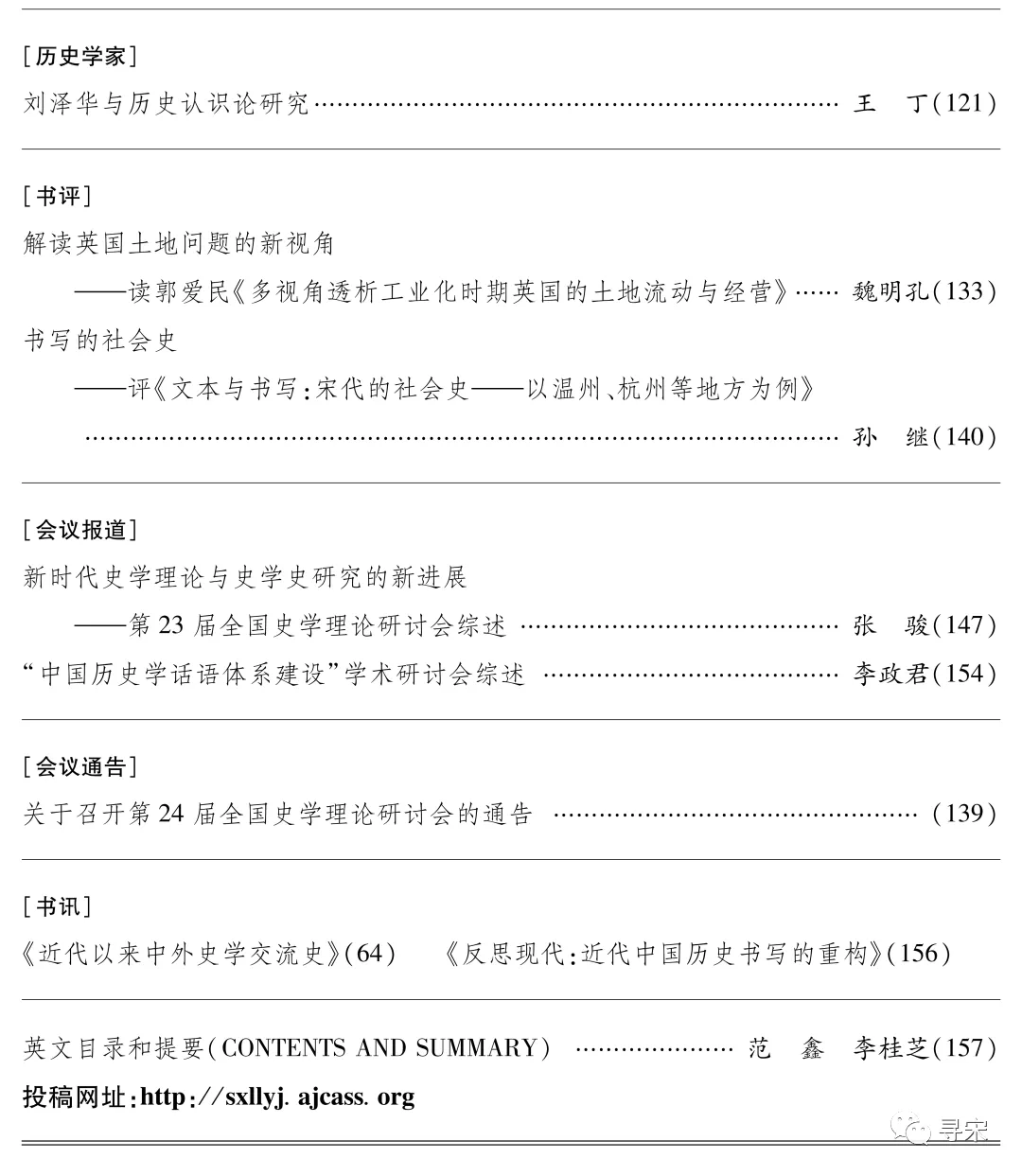
近年来,宋代社会史研究相较于政治史而言渐呈式微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史料的限制导致了议题的匮乏。具体来说,它既不像中古史那样时常受到新出文献的刺激,也不像明清史有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可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宋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视野、议题的突破显得至关重要,浙江大学吴铮强博士新近出版的《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1](以下简称《宋代的社会史》)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与以往研究将史料视为“历史事实”的承载物,直接采用其描述的信息不同,《宋代的社会史》从文本与书写的角度,通过对笔记小说、石刻、方志、族谱等四种文本的批判性阅读,发现不同类型史料中的社会史线索,实现宋元温州、杭州等地方社会图景的再建构。作为作者长期从事宋代社会史研究,注重汲取社会学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晶,该书的出版拓宽了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与议题,为学界带来了一股“活水”。在历史学的语境里,“历史”一词主要有两种不同层面的意涵:一种是指人类所经历的如此这般的过去,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一种是指人们凭籍人类过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对过去的表述与追述,即记录下来的历史。[2]由于客观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人们只能从史料中获得对人类过去的认识。因而,古往今来史学家对史料的研究都极为重视。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们就已经发明了一套严谨的史料考订方法。进入19世纪,以德国近代史家兰克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他们追求“如实直书”,[3]认为“历史事实”根基于原始史料,“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4]兰克认为史学家应“忘却自我”,主张用史料说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历史的“客观性”诚如他在《英国史》中所说:“我想消灭自我,只让事实说话,让推动力量出现。”[5]尽管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思想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判,但其史料考证(quellenkritik)方式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后现代主义席卷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实证史学遭到巨大挑战。后现代史学主张“从史实至语言(language)、从语言到文本(text)、最后从文本到符号(sign)”。[6]在这种“怀疑理论”的关照下,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中尤以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书写”(writing)概念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最大。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它物”,书写是针对文本进行的,只有通过对文本的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才能无限接近已逝过去的真相。[7]在这里,文献史料被视为一种“文本”或“述事”(narratives),学者的目的是发掘其背后的社会情境(context)与个人感情。[8]事实上,主张对史料进行批判性阅读并非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独创。早在唐代,我国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已指出史书中的“曲笔”,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9]梁启超先生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揭示了史书中的主观因素: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两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10]其后,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张对古代文献持怀疑态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两者在方法论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赵世瑜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甚至也包括经学)在史料学或文献学上的建树不仅具有现代意义,而且也具有后现代意义。”[11]不过,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史学研究范式,引起中国学界尤其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却是近些年的事情。一些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对历史书写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内涵和外延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历史书写”又称“史料批判”,在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日本学者安部聪一郎看来,它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12]可见,历史书写研究立足于史料分析,强调对史料的再批判,从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书意图等多个取径探讨文本形成时期的社会情景及撰者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从而实现对历史图像的再建构。[13]当前,历史书写研究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获得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辛德勇从史源学的角度,考证了《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重大转变的记载不可信,现在看到的汉武帝晚年形象是宋人司马光塑造的结果。[14]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孙正军、徐冲、赵晶等对史料批判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15]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历史书写研究范式也得到广泛的运用。以新出上官婉儿墓志铭的研究为例,仇鹿鸣分析了上官婉儿墓志及新旧《唐书》中不同记载的源流,揭示“在当时与后世,因种种政治与社会原因,上官婉儿的形象如何被不断地构建、涂抹和重塑”;[16]而在仇文基础上,陆杨进一步从书写的角度探讨了上官婉儿墓志的书写特征,并将其与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作对比研究,认为三种文本所建构的上官婉儿形象之所以迥然不同,是与它们被制造的政治环境和书写策略息息相关。[17]从时段上看,历史书写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古史领域,且大多以《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主要分析对象,落脚点多在政治史上。[18]就社会史而言,历史书写研究也广泛运用于对碑刻、族谱、契约等文本的解读中,但主要集中在这类史料相对丰富的明清区域史研究领域,而在宋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见。[19]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社会史》首次将历史书写的研究范式引入宋代社会史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开拓之功。《宋代的社会史》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中论证了藉由对温州、杭州两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而复原整个宋代社会图景在学理上的可能性。正文部分凡十章,各章相对独立,互成专题,分别选取了笔记小说、碑刻、地方志、族谱等四种常见的史料类型进行批判性研究。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以散文笔法写成的随笔、杂录的统称,其特点是篇幅精短、内容包罗万象,写作方式较为随意。这种文体区别于有韵律、有节奏的诗赋骈文,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宋代,笔记小说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洪迈的《夷坚志》便是其中代表作之一。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记内容往往荒诞无稽,大部分故事乃向壁虚造、道途听说之作,因而如何从这些“虚构”的故事中挖掘背后的历史事实一直是学者们面临的问题。因此,《宋代的社会史》转换思路,试图通过探究洪迈获取这些故事题材的途径,讨论洪迈与故事提供者之间建构的人际关系、故事提供者的地域关系以及故事类型反映的地域特色。第一章考察《夷坚志》中的23则温州故事。作者将这些故事的提供者分为温州本地人和外地人,根据他们的身份展开论述,不厌其烦地分析每则故事,借此考察洪迈与故事提供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认为洪迈主要通过亲人、好友、同乡、同僚等渠道收集故事,由此展现了人际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个人获取信息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内容上看,这些故事可以分为报应、鬼怪和命定三种故事模型,其中报应故事是温州地方社会流传最广的故事类型,反映了报应观念作为熟人社会构建道德秩序的重要方式在温州地域社会的广泛存在。鬼怪故事多发生在游宦士大夫和游学士子身上,这其实是他们在陌生环境下宣泄恐惧情绪的途径。从温州两则关于待阙者的故事来看,宋代乡居士大夫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怡然自得,而是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情绪之中,说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者与家乡的关系模式在此时尚未稳固建立。[20]第二章分析了《夷坚志》中的175则杭州故事,其中144则故事可归入温州类型,即发生在举人、官员身上的预言故事、游士或游宦处于陌生空间中的鬼怪故事、杭州当地平民阶层的故事,据此作者认为温州故事的类型分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杭州作为都城,与温州有着很大的不同,为此着重探讨了剩余的24则故事,按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将其分为权贵、官场和市井三类,这些故事正是杭州的都城特殊性在历史书写中的反映。[21]石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泛指镌刻在石材上的文字和图像,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我国有着悠久的石刻历史,《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数次出巡各地,共留下七处刻石。由于质地坚固,石刻成为古人颂扬功德、纪念先人的理想书写材料。秦汉以降,石刻文献不断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代的社会史》第三章以目前所见的20种宋代温州寺院碑铭为例,从书写者以及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间隔效应的角度讨论当地寺院的社会史。这些寺院碑铭除来自传世文献外,还有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碑铭实物,许多是首次面世,具有较重要的文献价值。宋代寺院碑铭虽然比较丰富,但学者要想对它们进行研究,始终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书写内容的模式化、同质化。它们大多记载寺院修建的缘由、经过,往往成为佛教史研究的史料,运用范围比较有限。为此,作者将关注重点从寺院碑铭记述的修造活动本身,转移到碑铭作者的书写缘由及其与寺院修造活动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上来。作者认为由信徒们——僧人和施主撰写的碑铭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且以弘扬佛法或宗教祈福为主旨,但到南宋时温州本地士大夫成为寺院碑铭书写者的主力,主旨往往是显示士大夫特定的社会或文化身份。这种变化体现了温州地方文化在两宋时期的变迁,即南宋儒家文化的兴盛对佛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侵蚀。[22]宋代墓志史料极为丰富,成为石刻文献之大宗,但和寺院碑刻一样,墓志铭书写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其书写原则是为墓志主人隐恶扬善,通常只透露的“部分”而非全部真相(only part of the truth),[23]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墓志铭是撰者根据一定的模式有选择地制造出来的。与以往墓志铭研究不同,作者试图解读温州士大夫通过墓志书写在地方社会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直是墓志研究的难点。第四章从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中收集到255篇宋代温州墓志铭,认为科举对温州墓志文献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墓志的数量与当地科举及第人数呈正比例的关系;另一方面墓志书写者一般都是进士登第的官员或者参加科举的士人。从传主的身份来看,墓志书写者与传主之间多存在着血缘、姻缘、地缘、学缘等多重社会关系,而且传主主要集中在富户与士人两个阶层,作者据此认为宋代温州墓志的书写是科举士人乡居与地方士人、富户建立社会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传播。[24]方志作为详尽记载某地事务的文本,其史料价值早已为学者所共知。到宋代,方志编纂获得极大发展,不仅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成为“博物之书”,而且数量众多,在各地大量出现。据学者统计,仅宋代可考的地方志就有492种,[25]但留存下来的只有40余种,极大限制了我们对宋代地方社会的认识。第六章作者另辟蹊径,从明代方志中挖掘宋元温州地方史料,通过对明代《弘治温州府志》中关于温州永嘉县、瑞安县祠庙记载的分析,复原宋元时期的地方祠庙体系。作者认为宋元时瑞安县的祠庙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其性质包括自然神祇、移民祠庙、英雄祠庙、航海神祇等,农民、富民、移民、海商等群体是推动这些祠庙形成、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相比之下,作为州治的永嘉县城内的祠庙明显多于乡村,并且出现了诸如先贤祠、赵清献公祠这类儒家化的祠庙。两种不同的祠庙体系正反映了两地政治地位及社会结构的差异。[26]第七章以《咸淳临安志》和《梦粱录》为例,探讨书写目的、作者身份对文本内容、体例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官修方志,《咸淳临安志》以服务地方官员的行政治理为旨归,因而其内容以大内为核心,开篇先介绍分布于吴山一带的皇宫和中央官衙,民众和自然山川次之,寺院、学校等最次。而《梦粱录》作为私人化的文本,关注的重点并非政治空间,而是杭州的生活空间,因而在编排、内容、语气上都与前者迥然有别。[27]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族谱是一种重要的记载宗族起源、迁徙、分布和发展历程的文献,被誉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然而,和方志一样,宋代虽是族谱成熟、定型期,但留存下来的族谱并不多见。现存族谱中绝大多数都始撰于明清时期,因而其中关于宋元史实的记载往往不被宋史学者所重视。但从学理上讲,有些家族确实有可能自宋元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其族谱也有保存宋元族谱资料的可能。基于这种认识,第八章作者从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的近百种温州族谱中挑选出五种,讨论明清族谱中的宋元书写,认为多数明清族谱中记载宋元时期的内容系杜撰、拼凑,不值一提。然后,对《抱川蒋氏宗谱》《包山陈氏宗谱》《锦园瞿氏宗谱》《枫林徐氏宗谱》《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中宋元内容进行了考证,发现它们都有作伪的现象,但程度不一。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对与考证,作者指出有些内容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具有延续性而且信息完整的雁行小传一般都是可信的资料。第九、十章主要探讨了光绪十四年(1888)编修的《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该谱仍保留了较为可靠的宋元时期的史料,据此可研究永嘉苍坡李氏的家族与人口变迁。该族在宋元明时期,经历了经济豪强、科举官宦、武装豪强、平民宗族等不同阶段的演变,这种变化与朝代的更替息息相关。同时,从南宋后期到明初,李氏家族人口增长率虽受到朝代更替的严重影响,但人口总量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变动。由此作者认为,家族人口发展的总体规模和速度,主要是由家族组织模式或资源等内部因素决定的,朝代更替对家族人口的影响是短暂性的。[28]这一结论拓展了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近世家族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认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宋代的社会史》在对四种史料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历史书写理论的探索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该书开篇就总结了史料的三种解读方式,即文献、文本与书写。当我们拿到一则史料时,通常会先关注这则史料记载的内容,对其内容进行严谨的考证,这是我国史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从清代考据学派到现代史学,无不重视史料考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辟两章论述了史料之性质、类型、收集及鉴别,他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29]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还应该从文本的角度关注这则史料的形成、留存、传播、销毁、篡改、重构的过程及影响这个过程的观念。[30]而历史书写的视角则是将这则史料的编撰活动视为一次社会行为,“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31]在作者看来,这三种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同一份史料采用不同的视角,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认识。综合利用这三种解读方式,以前许多被认为是虚构的、未被我们利用的史料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史料来源。对这类史料来说,重要的不是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人们如何掩盖、构建和叙述历史。 其次,该书结合宋代社会史史料的特征,提出“书写的间隔效应”,即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不重合现象。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被动书写的情况下,书写者与求书者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书写内容的影响,就成为书写内容另一种社会史的脉络。[32]藉由这种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史料的认识。以宋代墓志铭的书写为例。在宗室或功臣去世后,帝王依照惯例敕令翰林学士或文采出众的大臣为其撰写墓志铭,而普通士人去世,一般由丧家向亲朋好友或不熟悉的人求铭。[33]通常这两种情况,撰者甚至都不认识墓主,对其事迹自然无从知晓,因而丧家在求铭时都会提供逝者的行状。司马光在《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记载了为苏轼之母程氏撰写墓志铭的由来:“治平三年夏,苏府君终于京师,光往吊焉。二孤轼、辙哭且言曰:‘……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铭,子为我铭其圹。’光固辞不获命,因曰:‘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愿闻其略。’二孤奉其事状,拜以授光。”[34]可见,作为撰者的司马光从未见过程氏,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源于苏轼提供的行状,墓志书写者与书写内容之间显然间隔着丧家的意志。除私人文本之外,“书写的间隔效应”也广泛存在于官方文献中。众所周知,《宋史》是元人根据宋代《国史》编撰的,《国史》又是宋代史官在《实录》基础上“旁搜博取,校订是非”而成。[35]所谓“校订是非”,不仅是指对史料真伪的考订,更重要的是根据统治者的政治和价值观对人物、事件进行剪裁、定性,显然《宋史》中间间隔着宋代史官的意志。[36]这些说明在研究史料时,如果我们不充分考虑“书写的间隔效应”,就可能无法捕捉到文本制造过程中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情境。再次,该书总结了历史书写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书写视角可能为社会史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境的线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史料,本身就是古人精心谋划与刻意营造的结果。[37]具体而言,文本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如宋代墓志铭的书写就是丧家和撰者精心选材、制造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在当时价值体系下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38]而在明清社会史广泛运用的族谱资料中,历史书写的研究视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物质”文本,族谱是由家族中的某些有文化、有势力的人员编纂、生产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他们的个人意志和利益诉求,这一过程实质上展现了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同时,族人对族谱的使用和流传,使它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渗透于家族关系、仪式传统和文化习俗之中,从而反过来塑造着族人的日常生活。[39]最后,作者对历史书写理论进行反思,认为我们在使用历史书写视角时,还需要注意书写本身呈现与掩盖的对应关系。易言之,应该将文本置于生成的社会环境中综合考察,警惕陷入迷信文本的桎梏之中,切勿从文本到文本。如南宋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主力是文士,但这并不意味着寺院仅仅为文士的生活而存在,其在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比文本所展现的往往要更加丰富多彩。基于此,作者提出书写的社会史研究中“留白”的意义,“只有将这些书写线索以外的内容在历史想象中预留出来,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书写提供的历史线索”。[40]总之,《宋代的社会史》在研究视角、材料运用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诸多创新,引出了一系列颇具学术价值的议题,为宋代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对“猿猴盗妇”的论述虽属历史书写的范畴,但与全文紧紧围绕着温州、杭州地方社会展开的主旨无关,稍显突兀;又如作为一本专著,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略显松散,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各部分专题研究都保留其独立的社会分析脉络,各章内容并非统一主题演绎的结果。”[41]不过,瑕不掩瑜,本书作为国内首部以文本与书写的分析方法探索宋代社会史的专著,其学术价值值得关注。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