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处理相邻两个朝代的关系,这在历史研究中几乎就是日常事。通常,相邻两个朝代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因为时间的魔力,这基本上不构成问题,比如秦汉,比如隋唐。在史学研究上,把相邻朝代置于同一个研究时段进行考察,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在秦朝事实不甚清晰的时候,利用汉朝资料加以佐证,这在史学方法上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汉承秦制”是大家公认的常识。但是,例外还是存在的,比如唐宋。唐宋之间在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是近邻,它们之间的50多年的五代十国,无论置于唐后还是宋前,都不妨碍唐宋的近邻关系。虽然所有朝代的关系都可以用“承上启下”来联结,但是紧密还是疏离,还是大有区别。对于唐朝而言,不仅隋唐,在史学的研究中,甚至“南北朝隋唐”,甚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划分也远远多于把“唐宋”归结为一个阶段。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唐宋之间建立了一个隔离墙,它们虽然是近邻,但却总是走不到一块。这究竟是自然历史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原因?是史料提供了“绝缘体”,还是研究者的目光发生了“光学变异”?即使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但今天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唐宋无关论已经成为唐宋历史研究者的潜意识,如同中国的历史在发展到宋朝之前忽然结束了一切,宋朝好像在一面高墙后面消失了。从此以后,唐不知宋,宋不知唐。以前代为近代,在近代的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历史源泉,在十分重视历史借鉴意义的中国,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而宋朝几乎是一个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时代。宋代重视唐朝的历史,这样的证明俯拾皆是。宋代把唐代当作自身朝代的前身,研究唐代、总结唐代,几乎就是宋代历史学家的宿命。 
唐代的史料,主要是宋人搜集整理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这些大部头的类书,虽然并不是唐代资料专辑,但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正是唐朝的资料。宋朝重视唐朝资料的整理,这四部大书最有说服力。此外,《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对于唐史研究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同样是宋朝学者努力的结果。搜集整理的这些史料,既有利于宋代学者对唐朝的研究,也可以造福于后代。所有的唐朝历史研究者都得承认,在唐史研究中,我们最该感谢的就是宋朝学者。宋朝学者也是唐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学者,他们的观点至今仍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任何后来的唐史研究者首先必须认真对待的便是宋人的观点。《旧唐书》虽然不是宋人书写的,但他们很快就写成了《新唐书》,虽然《新唐书》也有诸多问题,但是直到清朝中期,新旧《唐书》才实现了平起平坐,而此前一直是《新唐书》独领风骚,《旧唐书》几乎濒临佚失。这里并不评论两《唐书》的优劣问题,仅仅想说明这个简单的事实,即宋人的观点长期影响宋以后的中国各代,唐代历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宋人的巨大影响。《新唐书》之后出现的《资治通鉴》,虽然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唐五代的内容所占份额平均最高,比如从战国到三国,平均8.28年一卷,而唐五代3.11年一卷。不仅如此,《资治通鉴》是十分出色的唐史研究著作,对后世,不管是专门的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宋人唐史研究著作,不仅时间上有先发优势,而且史料上也占有优势,毕竟唐代史料在北宋时期还有很多留存,而后世则多有佚失,所以在对待他们的历史认识上,在后世史料缺乏的条件下,不得不对宋人的观点给予更多的尊重。 
包伟民 刘后滨 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唐宋之间,在宋朝学者的研究目光中,损益同在。比较唐宋之间的继承与流变,显然也是宋代学者所重视的,在他们的笔下,我们没有发现那道横亘在唐宋之间的高墙。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唐宋之间的高墙,在宋代还没有搭建起来。如果要破除唐宋之间的隔离墙,宋代学者的研究和经验,都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历史确实驶入了一个新车道,藩镇割据,中央不振,凡此等等,使得中国这趟列车摇摇晃晃进入宋朝。宋朝对这份历史遗产显然是不满的,于是纠正五代弊政成为宋廷的首务。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赵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这很清楚地反映了宋初的状况与时代课题。其实,唐朝后期的朝廷,何尝不是心同此理?回到唐初去,可以看作唐后期朝廷的理想,而宋初则更有条件去实施。据说,《唐六典》的再发现曾经引发宋廷的兴奋,宋神宗主导的元丰改制,处处闪现着唐朝制度的身影。宋代的法典文献如《宋刑统》等,对于《唐律疏议》的继承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为什么明明不再实用的条款还要规规矩矩地刻写在法典之中?唐朝难道也是宋人的理想?或者他们认为宋朝距离唐朝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制度上也并不遥远?《天圣令》的发现,也证明了同样的原理。即使很多唐令的条目在宋朝被废止不用,但是整个令文的体系依然保持着唐朝的模式,还在努力使用唐朝的句式。或许,宋人有一种情结是不愿意割舍唐朝。而这个唐朝当然是初唐和盛唐,不是中央不振的唐后期。宋人没有在唐宋之间修建隔离的墙,其实后来的元明清也没有。有关唐宋的隔离,完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巨大“成果”。在西风尽吹的近代史学体系中,面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而划分历史阶段,给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判断,则成为研究的基本方法。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分开唐宋最有力度的研究。京都学派有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把唐宋分别划归为中古与近古。东京学派虽然不同意这样的变革论,但是他们同样把唐宋切开,分别命名为古代与中古。日本学界与西方联系比较紧密,日本的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西方。现在,中国学界也有赞成唐宋变革论者,虽然如邓广铭先生等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只要赞成这种结论,就有利于唐宋研究的分割局面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关,甚至有人认为唐宋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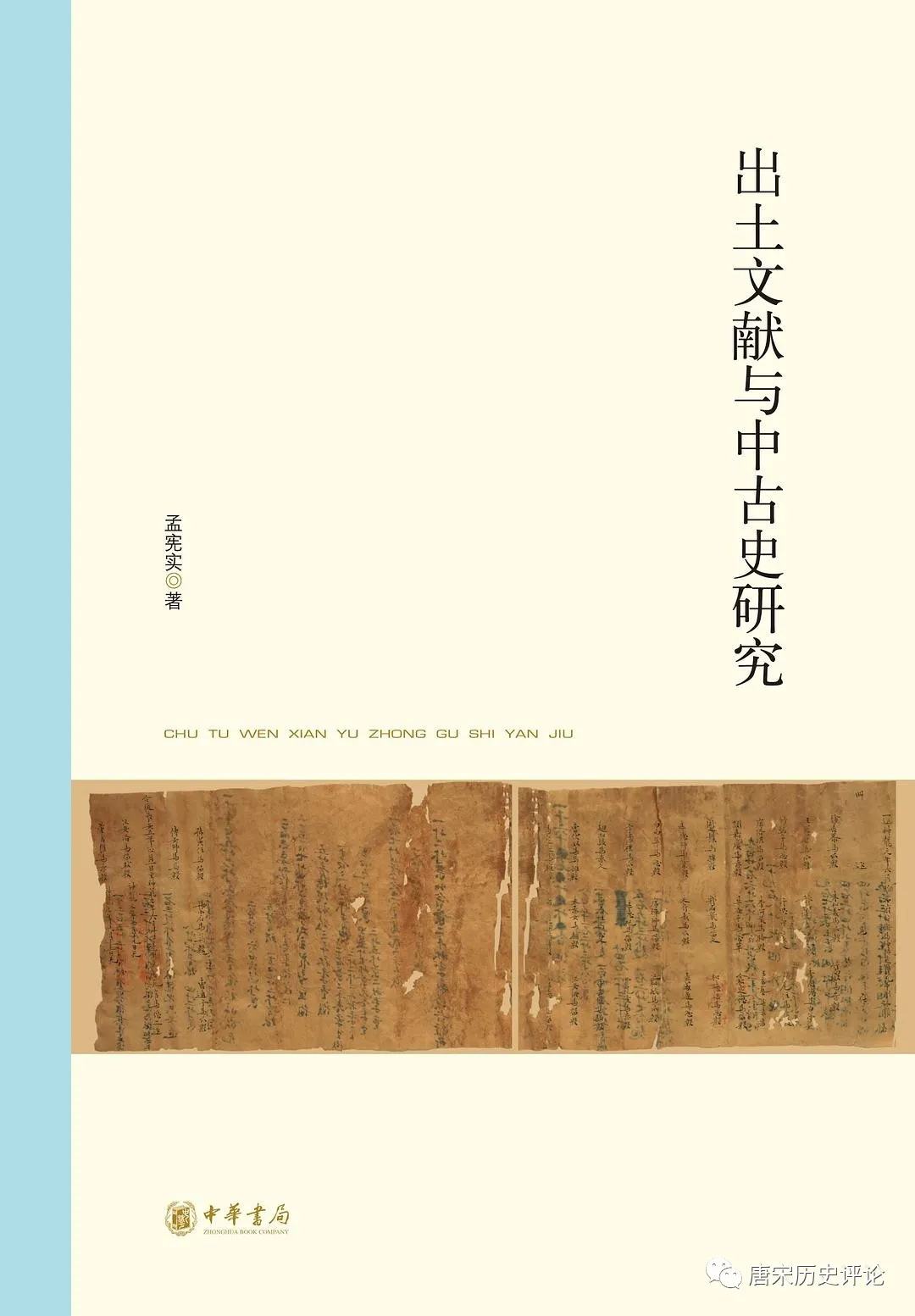
唐宋之分,难道仅仅是一个外来结论吗?其实,中国学者的研究倾向,某种意义上也让唐宋之分变得似是而非。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而言,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与宋朝无涉,但与魏晋南北朝关系重大。他的研究,把魏晋至于隋唐的中国文化发展,用“制度史”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梳理,让隋唐制度的渊源清晰显现。同时,陈先生的政治史研究,把北魏之后的北方政治史用“关陇集团”概念统合起来,找到了一条贯穿北朝与唐朝的历史红线。陈寅恪先生的成功研究,不仅开辟了一条研究路径,更是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魏晋与隋唐历史的内在联系,就这样呈现出来,后来者在领略陈先生的研究思想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把魏晋隋唐纳入一个研究阶段或者框架之中。陈寅恪先生之后,中古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大家纷纷涌现,星光灿烂,一片繁荣,这更吸引了后学的紧追不舍。如此一来,魏晋隋唐概念,在后来的研究者心目中,便成为一个研究方向,而越是研究深入,就越会发现其中的联系性。其实,陈寅恪先生也著有《论韩愈》,专门勾勒出唐宋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想,到佛教,到文学,唐宋的联系显然是十分紧密的。后来的研究者,追随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如今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已经紧紧把唐宋联结为一体,似乎思想与文学属于另外一个天地,在讨论唐宋的历史联系时,这两个领域沉默不语。于是,文史在唐宋真正实现了分家,唐宋文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概念,而唐宋历史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毫无关系一样。相对于魏晋隋唐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唐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对于唐宋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变化但绝没有“唐宋变革论”所说的那么巨大,但是邓先生的研究精力主要用在宋史而不是唐宋,所以他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想,在“唐宋”概念下,对于后学同样影响不显。前辈学者的引领在学术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后学而言,前辈开辟的领域等同于成功与畅通,而前辈学者研究不充分的领域,后学则完全可以视作畏途,担心此路不通。唐宋之间,联系还是区隔?发展还是突变?凡涉及重大理论判断,结论都需要研究者不断重新检验。任何相邻时代都有密切的联系,之所以会有紧密与疏离的差别,除了史料的证明之外,也与研究者的目光分不开。发挥作用的,不仅有事实,还有研究理念。突破研究思路,就会发现新的景观。此前,唐宋联系性的研究确有不足,我们主要努力的方向是开放新视野,拆开高墙。本质上,唐宋之间的损益究竟孰多孰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实现理念突破。不管是联系还是差别,只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只要比此前的研究有所进步,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唐宋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一定会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_____
本文出自《唐宋历史评论》(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