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社成员黄忏华(1890-1977)既是一位卓越的佛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在我国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他的《中国佛教史》自1940年由商务书局初版后,多次重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全国众多佛学院列为必修课教程。多年来,这部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汉传佛教史,使他成为我国第一位采用现代学术方式研究撰写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 
《中国佛教史》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写到清末民初在在我国再次复兴,对佛教传来中国后的演变、发展、衰微、再兴等作了系统论述。史料丰富,考证有据,文字流畅,一直到今天仍受到研究中国佛教专家的重视。另一本书《西洋哲学史纲》一直被近代哲学界视为一本权威介绍近代哲学的史著。他与蒋维乔合作写《领导干部读经典》一书,成为众多党政干部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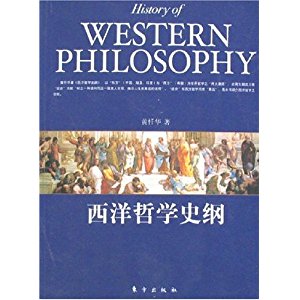

(《领导干部读经典》)
一位治学严谨的作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忏华应当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加入新南社,这是一个以在京(南京)、沪等地活动的文人团体。黄忏华先生不仅对史学研究卓有贡献,而且,能诗善文,二十岁就有文名,一生勤于笔耕,对美术、哲学、汉传佛教的研究造诣甚深,他的著述,诸如,《佛教各宗大意》、《佛学概论》、《华严根本教义》、《金刚顶菩提心论浅释》、《佛学丛话》等至今仍被全国诸多大专院校列为必修课本,尤其是他的哲学、美学、文学以及译作等。 
黄忏华(1960) 《西洋哲学史纲》、《印度哲学史纲》、《现代哲学概观》、《近代美术思潮》、《弱水》、《献曝集》、《怀芳楼零拾》等)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仍被台湾、香港等华文出版社,一版再版。 忏华先生在杭州度过了后半生,与西湖有着不解之缘,我们有幸于2017年9月8日在下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见到了黄忏华的女儿(黄本元女士),请她谈谈父亲一生的故事,特别是在杭州的经历。 黄女士说,父亲祖籍在广东顺德陈村,自幼就跟随爷爷黄金钺居住在南京城南的泰仓巷,爷爷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廷宿迁县知事(县长)。 父亲由黄宾虹介绍加入南社,也是同盟会成员之一。 年青时,父亲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新时报》、《学术周刊》任编辑,后又在南京《立法院公报》当编辑。 抗战前,父亲一度执教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课余从事佛教著作的撰写。抗战时,撤退到了重庆。 胜利后,父亲又随立法院返回到南京。 
(黄忏华夫妇与女儿黄本元40年代) 在南京时,父亲用稿费收入在大悲巷14号买了一幢二层小楼作为安身之所。1947年,父亲的高血压病复发,体力不支,只好辞去立法院的工作。是年,他的《佛教各宗大意》再版,得了一笔稿酬,于是,陪同太虚大师游览西湖,杭州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湖散记》一文中,写道:“西湖足以瑰目璨心”。不难看到,父亲偏爱西湖,于是,举家迁居杭州,一边养病,一边写作,把杭州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住所。
黄忏华移居杭州 初到杭州时,我们一家人住在栖霞岭的香山寺(香山寺以香山洞而得名),又称香山精舍,不过,我们只是暂住在那里(二年多)。 记得当年栖霞岭山脊有一个小院,住着父亲的一个朋友,叫孙慕唐(1889-1957),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家。小时,父亲常带我到他的住所玩,他家住在岭上一座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小院里。 
(黄忏华一家在杭州40年代/左一为黄本元) 我家在香山寺只是过渡。后来,经孙老先生介绍,又搬到附近凤林寺旁的牛将军二弄去住。其实是一条通向山脊的小路,我们一家人租住在弄内的一幢别墅院里(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后面的半山上),地方相当幽僻,住着一位香港老板的姨太太,不过,父亲与往常一样,每天仍奋笔疾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要建造杭州饭店(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我们住的地方被征用,全家搬到城里的法院路54号(今庆春路、仁德里口)的一座石库门房子,父亲一直到过世为止(1977)都住在那座房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灵隐寺大殿修复,父亲先在灵隐寺的修复委员会做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赵朴初先生的介绍,父亲到上海静安寺图书室任职,对图书室的书籍、资料做一些整理、校点与考据工作。那段时间,还担任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这些职务。 由于父亲学习过梵文与藏语,对唯识学、印度哲学、西洋哲学与藏传佛教均有研究,由此,参与了周总理主持的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英文部分的编写以及《辞海》佛学部分的编撰工作。  (黄忏华夫妇50年代)
父亲生活简朴,从不张扬 到了一九六一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邀请父亲返回杭州,聘为浙江省文史馆的馆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行事低调,从不张扬,一个心态宁静、与世无争的人。父亲常常告诫我的话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凡事都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三排左二为黄忏华1963年2月16日) 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刚收到《辞海》编辑部来信,他们告诉我,我参与编写的那部书《辞海》,已经出版,编辑部给我寄来一套样书,已经寄到了省文史馆,编辑部让我自己到文史馆去取。” 于是,我(黄本元)陪他到了文史馆,父亲向管理人员问及那套样书时,管理员告诉他,他们原以为这套书是寄给文史馆的,所以已经放在图书室的书柜里(公家财产了)。父亲听了,也没有说什么,默默的走了。在回家路上,我问父亲:“那套书明明是寄给你个人的样书,为什么不向他们要回来?” 他说:“放在图书室也好,这部书大家都能看到了,我将它拿回家,只有我一个人看。” 在那个年代,父亲从不谈自己过往的生活,也不说以往的成就。坦率的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籍再而三的出版后,各地好评如潮时,才知道父亲一生所作所为的。 寓居杭州时,父亲经常带我出去会会他的一些老朋友,诸如,画家黄宾虹、国学大师马一浮,以及居住在栖霞岭的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严群(翻译家严复的直孙),还有郑晓沧、王驾吾、姜亮夫、陈樱宁(后去北京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理长)。父亲与老朋友谈得十分投缘,不过,我当时只是一个蒙蒙无知的小孩,只知道他们是些大学问家,并不清楚那些人都是辈受人尊崇的学界泰斗。 
(黄忏华夫妇在西湖畔60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爱看书、爱写作。解放以后,他住在租来的那个十五平米的小屋家(法院路54号)里,在那张既当饭桌,又当书桌的方桌上写作或者看书。在写作时,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有时快吃饭时,母亲偶尔去帮他收拾一下,动动他的书稿,他就会很不高兴。 父亲不抽烟、不打牌、不喝酒,不善交际,不善言谈,总是沉默寡言,读书、写作成了惟一的嗜好。在我们的房间里,除了一大一小二张床,一张方桌,几只箱子外,一半地方都堆着书。 文革时,我们厂(杭州轴承厂)造反派对我说:“你家的书肯定全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你将这些书送到厂里来销毁。” 我说:“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怎么拿得动?” 那时,造反派们忙着抄家、内斗,也顾不了那么多。 在运动中,父亲的那些老朋友纷纷受到批斗,几乎无一能够幸免,不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就是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幸好父亲的生活一向低调,谨言慎行,与他交往过的人不多,居民区也没有把他怎么样。 文革开始时,父亲自动对号,去居民区去报到,自述曾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的经历。人家见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安分守己的呆在家里(不太出门),又是浙江省文史馆的馆员,也没有为难他什么,将他放回家了。虽说父亲在文革时期躲过一劫,但那些日子,他仍然非常紧张与害怕。父亲对我说,中国佛教协会早年请他到北京的中国佛教学院教书。可是,父亲留恋西湖,不愿离开杭州,也不愿离开家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前排右三为黄忏华1965年10月) 有一次,他庆幸地对我说:“我幸亏没有去北京,如果去了佛学院工作,工资虽说比现在拿得多,文革时就很难逃恶运了。”(文革时,佛教学院1966年停办,员工被批斗后,全部遣送农场劳动) 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人在文革时的生活仍然如同惊弓之鸟。 父亲对我说,家里那么多书,总是一个祸水,还是自己处理掉罢,于是乎,几乎堆了半个房间父亲珍藏的书籍,包括父亲自己的著作,一古脑儿,一本不剩的送到了废品回收站,几分钱一斤的价格,成了一堆废纸,化为纸浆。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上半年),父亲再三叮嘱我到旧书店去看看,找一找,没有没他写的书。可惜的是,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都没有找到过一本。 我与父亲黄忏华 我(黄本元)一九四O年出生在重庆巴县,那时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中年得女,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自从我出生以后,父亲一直将我视作掌上明珠,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父亲从没有大声喝斥过我,更不用说打骂了。 
(左起黄本元、外孙女、黄夫人、女婿、黄忏华70年代) 但是,父亲仍有严格的家教,经常对我说,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要礼貌待人,孝敬长辈,不能撒谎、不能吧唧嘴,待人要和善,说话要和颜悦色。吃饭时,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先吃,吃饭不能剩饭粒。在外面时,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赠予。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黄本元女士说,我还在里西湖中心小学(今西湖小学集团)读书时,因为功课好,各方面都表现不错,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父亲听说了,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快乐神情。 有一次,学校让大家订阅《中国少年报》,于是,我回家向母亲要钱,家里经济已经非常拮据了,根本拿不出闲钱订报纸。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干部,已经向老师承诺订报的,只好在家里大哭大闹,父亲听见了,与妈妈商量好久,才从菜金里省出钱来给我订了一份报纸。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上泗钱塘江边一个偏远的地方表演节目,那天刚巧遇到了暴风雨,这个地方当时不通公交车,路又不好走,回不来了。老师只好将大家带到当地一所小学礼堂里避雨。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大雨仍然下个不停。 我们眼巴巴地等在那里,在夜色中,我突然见到有几个全身湿透的人从外面进来,其中,竟然有父亲的身影。原来父亲实在不放心我,与另外几个家长结伴冒着风雨与落水的危险,寻过来了(那天暴风雨太大,在乡下已经分不清道路与河塘了)。他们步行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们演出的地方。 这样的事,点点滴滴,在我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家常便饭。 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报考省立女子中学(后更名杭州女中,今杭州市十四中),当学校张榜公布名单时,父亲费了好大劲才从墙上长长的公布考生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开心得几乎要哭了! 因为省立女子中学是当时杭州的重点中学。 考大学时,父亲知道我喜欢化学课,鼓励我报考南京工学院的化工系(今东南大学),接到大学入学通知时,父亲开心得说不出话来(因当时只有1/3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如果考不取,就会被动员下乡劳动)。 去南京的前夕,父亲化了他二个月的工资陪我到钟表店买了一块瑞士女表。那是我第一次戴上手表,也是父亲对我考上大学的奖励。 启程时,父亲不放心我单独第一次出远门,再三叮咛母亲送我到上海,直到我在上海转车(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后),母亲才返回杭州。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苏州一家企业工作。 有一次,父亲在北京出席一个会议,一位中央领导问他:“在生活有什么困难与要求吗?” 父亲说,我只有一个女儿,自己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很想将她调到身边。在这位领导的关心下,我调到在半山的杭州轴承厂工作。 那家厂在郊外,上下班不方便,有时下班迟,我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快到站时,总会在矇眬的夜色中见到年逾古稀的父亲柱着拐杖,一个人站在公交车站上等我。一切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让人难于忘怀! 多少年来,对于我这个女儿,父亲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写了那么多文字,出版了那么多的书籍,我竟混混然而不得知。坦率的说,当年我以为父亲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才从事写作的。 就我的专业与爱好来说,父亲从事的工作(佛学研究),我不感兴趣,甚或,有点反感,因为当时这些都是属于封、资、修的范畴。 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浏览到人们对父亲的评价,见到他一生写了那么多书,涉及的范围包括佛学、美学、哲学、文学,方方面面,每一本著述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人们将他称为我国著名的佛学理论家、知名学者等,我才恍然大悟。 读了父亲写的这些书,想到父亲一生的为人,父亲的一言一行,往日琐琐碎碎的生活情景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在我渐渐了解父亲的时候,老人家早已离我而去了,他对我是如此的溺爱,而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关切又是如此之少。每想到此,止不住潸然泪下。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孝女,对不起老人家! 1977年8月28日,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享年八十七岁。过世后,仍留下了二部手稿《水经注捃华》与《南传佛教概述》。这是父亲最后留给世人的一份精神财富,我要帮他完成未圆的梦想。 2010年,扬州广陵书社接受了《水经注捃华》的出版工作,2013年正式出版。另一本手稿《南传佛教概述》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