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宪益,是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他先后在国立编译馆和外文局工作,英译《史记》《红楼梦》《鲁迅选集》,中译《奥德修纪》《牧歌》《罗兰之歌》,为东西文化交流贡献了累累硕果。
今年适逢杨宪益逝世十周年,文景首次将杨先生的中译作品集结出版了《杨宪益中译作品集》,并在夏至夜邀请李辉、赵蘅、戴潍娜,共话杨先生的翻译成就,共忆名家风采。杨宪益先生与妻子戴乃迭互相欣赏、彼此支持的坚贞爱情和两人所过的智性、审美的生活,老一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风骨和担当,在浮躁的今日尤为可贵。
翻译生涯的开端:因为爱情
戴潍娜:《杨宪益中译作品集》这套书的体量和广度都非常令人惊讶。从西方文艺起源的古希腊史诗戏剧,一直到新型的文学题材,比如说科幻小说、现代诗歌,杨宪益都有广泛的翻译和涉猎。在现在的翻译当中,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二位都是非常了解杨宪益先生的人,能否给大家讲一下杨先生的故事?

赵蘅:今天能到这儿来,是因为春天时的一个约请。这么多年来,关于我舅舅方面的采访和活动我都不会拒绝,觉得应该到场,毕竟有这份情感。今天来到这里做嘉宾,我实在不敢当,因为我只是一个晚辈亲属,对杨宪益的译著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只是他身边,尤其最后十年陪伴他的一个晚辈亲人而已。
我舅舅一生有太多的故事可说了。按我所理解的,他的最初愿望,应该是想成为一名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学者,从他的很多文章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跟戴乃迭结婚,改变了他的一生。我的舅母非常喜欢翻译,又合适又喜爱翻译。所以我想是出于爱情,他就陪着他太太翻译了一生。我舅母走了,他也就不再翻译了。

杨宪益与戴乃迭 戴潍娜:杨先生跟夫人两个人互相成就,互相欣赏,非常感人。我看过杨宪益先生晚年的一个采访。记者问他说,戴先生走了以后,您用什么方式纪念她?他回答了三个字,只有三个字,里面却饱含了所有的深情——忘记她。有的时候奇妙的缘分跟天才结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段学术上的传奇故事。李老师,您对杨老师也非常了解和熟悉,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吧!
李辉:杨宪益与我是1983年左右去外文局宿舍的时候认识的。见过杨先生之后,跟他的交往就越来越深。杨宪益十几岁就抽烟喝酒,90岁没去过医院。在2001年左右,我请杨宪益到郑州做学术讲座,讲中外打油诗。杨宪益基本上不喝水,也不喝茶,他就喝酒,什么酒都喝。我们在郑州,他就先喝酒,讲的时候,他说你再给我倒点酒吧。讲完之后,我又陪他到开封去。他说,我应该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住到这里来,那是我们杨家将奋战过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杨先生经常抽烟,我每次去他那儿,他都在抽烟。2009年3月底,我去什刹海看他,他还在抽烟,我给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他在抽烟的照片。
年轻未敢忘忧国
戴潍娜:谢谢李辉老师。杨宪益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百岁秘诀,如何能百岁?抽烟、喝酒、不运动,开个玩笑!
杨先生身上其实有非常不羁洒脱的风范,在他那个年代进入牛津上学的人,身上往往都有那种放荡不羁的傲气,同时又有研究的精神。他1934年先到伦敦,到伦敦之后,他花了半年时间去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然后他就去牛津大学面试。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他,希腊文你学了多久了。他说,半年时间。考官们都不相信,说那你考试考得好,一定是运气好。但其实是因为杨先生聪明。他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学的中国人,还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天才。二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杨先生学习语言的事情吗?
赵蘅:按照我姨妈说法,一百年就出一个杨宪益,其实也不足为怪。我舅舅的父亲是中国银行行长。中国的第一家中国银行就是在天津开办的。他是富家子弟,家里担心他被绑票,为了安全,在十二岁前都是在家里读书的。家里给他请了一个中文老师,叫魏先生,后来又请了一个英文老师。魏老先生教他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学生没法教了,因为他太天才了。他对对子,两个妹妹都比不过他。上新学书院之前,他基本已经饱览群书了。而且他很早就开始读原版书籍。那时候天津有书店可以订到国外的书,他就直接订,来了书看完,再去订,所以他什么书都看。
我还想提一下我外婆。我外婆虽然是一个生于18、19世纪之交的旧式女子,但她非常有远见,非常有志气。外公去世之后,她坚持留在杨家,努力把三个孩子养大,而且要让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不分男女都要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我的妈妈和姨妈都进了天津非常好的学校——美以美会中西女校。
都说有钱家孩子容易被惯坏,但我舅舅是惯不坏的。他从小就有志向,开始他非常佩服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有责任,为国家做事情。我跟他聊天时,他觉得现在的孩子缺少理想,不爱读书,他有点无奈,但他也不会过多干涉他们。他们那一代因为时代的关系从小就有抱负,我姨妈和妈妈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要怎么往前走?舅舅很年轻时就已经在思考这种大问题了。
所以杨宪益19岁到牛津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也有远大的志向。
翻译《红楼梦》,但不喜欢《红楼梦》
戴潍娜:杨先生曾主持过一个“熊猫丛书”,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像《聊斋》《西游记》等,包括一些大家的作品。他其实应该是最早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学者了,非常有远见。但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贡献还是翻译《红楼梦》。他们的翻译时间跟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石头记》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78年到1980年,杨戴翻译的全本《红楼梦》才得以出版。杨先生把那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翻译成了“Pages full of fantastic words,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真是既直白又精准。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二位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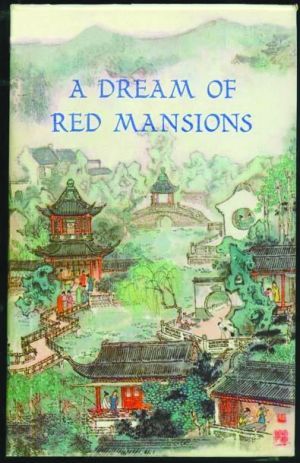
杨译本《红楼梦》
赵蘅:关于我舅舅的翻译生涯,根据他的自传,追溯到最早应是1938年的《离骚》,但是我舅舅始终认为《离骚》不是屈原所作。毕业之后舅舅毅然回国,那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中。他和未婚妻戴乃迭回国后辗转到了重庆,后来被推荐到了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应该是他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
那时候国立编译馆非常缺乏中翻英的人才,所以他把这个冷门和空白给填补了。梁实秋建议他先翻《资治通鉴》,他就从这儿开始,后来就是让他自己选书目。他曾经谈到过,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就是在国立编译馆。后来国立编译馆从重庆搬到了南京,他也去了南京。据我了解,《红楼梦》是在进监狱前翻译了80回,从监狱回来,稿子还好没有丢,又接着翻了40回。出版时间你说得对,就是在那个时候。
《红楼梦》他谈过很多次,他说我承认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最好的一部,但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我妈妈也说她不喜欢《红楼梦》。我猜他们是不是不喜欢宝玉黛玉那种人生态度?因为舅舅他们是从小立志,对社会有担当,《红楼梦》里面这些人物的生活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
我舅舅做事、说话,都非常公正,有一说一,从来不说假话,只说真话。不管面对大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从来不会因学问大就傲慢、训斥别人。我在舅舅身边陪伴他10年,我所学到的东西,就是他的待人接物。这些一点一滴的事情,就能够看出一个伟大的人性。

杨宪益
他就是这样一个老人,他永远坐在那儿。我觉得我表妹也是这样,话不多,他们家里就是特别的安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舅舅对所有人永远都是很平和,所有人去他家,他都说“欢迎欢迎!”每次走的时候会重复另一句话,“我腿不好,不能站起来送了,对不起。”
2009年11月1日,他走之前,下了头场大雪,他在煤炭总医院医院住院,我们拍了雪景给他看。当时他病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还挣扎出笑容回应。舅舅的眼神很纯粹,细长的眼眸里瞳孔那么黑那么亮,怪不得当年会吸引我舅母!他到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想念他。
老一代知识分子智性、高贵的生活
戴潍娜:杨先生和夫人戴先生真的过的是一种非常有修养的、审美的、智性的生活。我们说风格即人,风格就是人本身。听到了这么多杨先生的故事,我们更加能理解他的语言风格,那么流畅、那么率真、那么清晰。
李辉:戴乃迭先生去世之后,杨先生写了一首诗,写得非常好。我最近在香港的《大公报》开了一个专栏,叫“这些老前辈”,每周二一篇。杨宪益先生的那篇题目就来自那首诗里,原诗是“从来银汉隔双星”,我将之改为“银汉不再隔双星”用作题目。可以说。这些老前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
杨宪益的打油诗写得特别好,真是写得特别好,后来还出了诗集《银翘集》。黄苗子为他写的序,黄永玉为封底画的插图。后来他的文章、回忆等等还编成了一本书,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那本书正好出了,叫《去日苦多》。
杨先生最终是2009年11月23号走的,到今年年底11月份就是10周年了。他们做了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你能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爱中国的,爱中国文化、文学。
戴潍娜:在这样一个粗鄙的时代还能听到这些故事,真的是非常奢侈,里面都是那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高贵。刚才李老师提到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杨先生除了诗歌之外,他的知识也非常广博。他的杂文里面会考据中国典籍里面的火鸡,会谈到《水浒传》不同的故事版本流变,以及古罗马帝国跟中国汉朝之间的交往历史等等。
我们对杨先生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翻译。但是这样一位翻译大师,他却说自己不是翻译家,而是翻译匠。二位也都从事翻译。李老师有很多翻译著作。赵老师则来自翻译世家,赵老师的父亲赵瑞蕻先生翻译过《红与黑》,她的母亲杨苡先生是《呼啸山庄》的译者。请二位谈谈你们眼中的翻译,或者说你们眼中杨先生的翻译观,好吗?
赵蘅:确实,我爸爸是《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我妈妈翻译了《呼啸山庄》。我爸爸、妈妈和我舅舅,他们三个是一派的,讲求“信、达、雅”。我可能没有领会得很好,但大意是,既然翻译西方的著作,就应该忠实于原著,把那个国家民族的原汁原味和风格准确地传达给世人。如果你想创造性的翻译那也可以,那是另外一种译法。但如果作为翻译本身,还是应该忠实于原著。许渊冲老先生在昆明见了我,听说我是杨苡的女儿非常热情。他主动说起这个分歧,非常豪爽,他们那代人是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之间是学术之争,但非常有益的、积极的讨论。
舅舅舅母他们两个人合作翻译,据我了解,首先是舅舅初译。我舅舅是天才,他可以看着中文就直接说出英文。我舅母打字,然后校对并润色,这方面我舅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几个月就可以翻译一本名著,速度很快。很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们两人合作的场面,但是我听到过舅母嗒嗒打字的声音。那个声音和情景至今我还记得。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