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湃新闻: 您很早就用互联网了,而且与几位朋友一同创办了往复论坛。您的网名叫“老冷”,背后有什么典故?您在网上有什么印象较深的奇遇和收获?
罗新: 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并不是往复,而是天涯上有一个关天茶舍,那是我创办的。
往复最大的收获,是陆扬老师的加入。我们这些人说的话,即使不算坏,对大家都不那么陌生,只有陆扬的参与,他说的话,他带来的信息,他带来的想法,是当年的中国学术界很陌生的,所以他的意义非常大。2000年左右的中国学者,对海外学界的了解,和现在相比,不是一回事。现在陆扬说个什么,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但那个时候陆扬说的话,都是新鲜的,都没见过。云中君的出现,是网络学术生态的一个新现象。如果说往复(对中国学术)有贡献,这就是一个贡献。
因为我本家姓冷,我父亲本来姓冷,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嫁到罗家,这样我们家都姓罗了。这个在传统社会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传统社会根本没有所谓纯正的姓氏。姓氏的文化意义要远远高于姓氏的血缘意义。认同反映的是文化意义。谁养我,我就姓什么,对不对?
澎湃新闻: 您是个电影谜,一年大概要看多少电影?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片子?电影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何影响?
罗新: 我过去狂追电影和美剧。时间合适的话,我能没完没了地看。
我年轻时是爱文学的,也曾想当作家,更多的是看小说。但看小说需要时间,看电影,像看美剧一样,比较省事。所以,看电影可以说是一种偷懒,你进入虚拟世界,它迅速就结束了,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不像看小说,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真正看小说的收获比看电影的收获会大得多。
我经常在想历史和虚构文学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写的历史跟那些文学作品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游戏规则不一样,历史学要遵照一套自己的学理、研究和写作规范。历史和文学最大的不同是,文学从构想开始,就是有主人公的,有中心思想、故事主线,而历史没有,历史哪有什么主人公啊,只有写出来以后才有主人公,比如你把伟大领袖写出来,他才是主人公,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主人公随时都在死啊,随时都有新的主人公出现。真正意义的历史是没有主人公的,是一团混沌,没有主线,也没有故事,——故事是写作的时候,被历史学家特意找出来的,围绕一个主人公写出来,放在有限的时空里讲述。但是这样做就抹杀了很多别的主人公,抹杀了很多别的主线。我觉得,对历史学的这个叙事特征进行反思,可能对我们认识历史有意义。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我们会觉得我很重要,其实对历史来说,只不过是万万千千的线索之一,你把这个线索单独拿出来的时候,强调它的时候,意味着抹掉了很多其他的线索,而其他的线索也都是真实的东西,你抹掉了他们,是因为你认为他们在你的研究中不重要,当然也可能是你对他们认识的不够多。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要经常这样想,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别把你写的东西看得多么神圣、多么重要、多么不可动摇。
澎湃新闻: 您无疑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很好奇,您从大都到上都的路上还带着什么书?
罗新: 如果从背包客的角度说,不带帐篷,不带睡袋,不带吃的、喝的,所以带的东西不多。十来公斤,不到十五公斤。不重。露营的人,一般都得带二十公斤以上。十五到二十公斤是一个跳跃,到二十公斤就很难受,走一步都很难受。十五公斤以下,多一点、少一点,差别不大。背负增重到近二十公斤,我去年经历过,每一步都不是好惹的。我走之前,请社科院历史所的罗玮,他是张帆的学生,我请他帮我准备了相关史料的电子版,当然我还带了几本闲书,因为我还是喜欢看纸本。其实后来看不了。前一个礼拜还能看,后一个礼拜就看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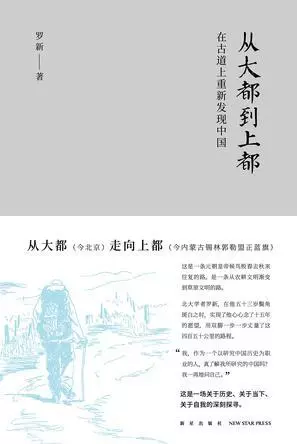
澎湃新闻: 《可汗号之性质》无疑给人很多启发。您在这篇论文中从功能的角度对谥号问题提出了新解,认为它是官号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您看来,“形成于自下而上权力关系时代的官号,最终被自上而下权力关系产物的谥号所代替。”限于论文主旨,这篇论文似乎并没有解答您在文中提出的一个疑问:“他们(指君主、皇帝)是怎样自动放弃了生前的美称,而甘心接受死后由别人给定的一个‘可美可恶’的谥号呢?”
罗新: 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是把草原官号和古代华夏制度联系起来讨论。我那时候受了人类学的影响,在几篇文章里都暴露出这一点,不愿意只说北方是这样的,非常想说我做的这个研究具有一般性,也可以用来反观其他文化,包括华夏早期文化。我那时候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后来我放弃了——认为北方的发展只不过是反映了华夏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北方的政治继续成熟发展,将来它会走到南边的华夏这条路上来。这种预设,很可能是受到普遍历史观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就是进步史观那套东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始终想把北方和华夏搭上,碰到谥号这个东西,觉得好奇怪,生前有谥号,为什么改为身后有谥号。我想对这个问题给一个解释,对这个解释,有人说很有启发,有的人没有感觉。时间长了,我也想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了。后来我就沉迷在名号的功能分析上了,不太敢跟华夏搭边了。除了《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这篇文章,我后来再也不敢把北族名号和华夏传统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种解释还是很冒险。当然做先秦的人也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启发。
澎湃新闻: 在史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您对史籍中有关南匈奴的零星记载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在《匈奴单于号研究》一文中,您认为:“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都是死后获得的。”这“是匈奴单于号传统的重大改变,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一定来自东汉王朝”。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直接证据,我对这个论断仍不免有所怀疑,毕竟内亚草原民族的名号传统根深蒂固。我想请教的是,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已有十几年,您是否有更多证据(包括旁证)进一步证明您的观点。或者,您是否改变了原先的观点?
罗新: 这个就是普遍历史观的影响,既然到了中国文化环境下,匈奴慢慢就接触汉朝文化这一套,所以匈奴名号就从生前变成死后获得的了。如果能说明这一点,我当时所信奉的那一套历史观就起作用了,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这套东西就不是中国独有的了,而是在某个社会、某个政治发展阶段必然经历的,是普遍的。北方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这个历史阶段。后来这套我就不提了,我感觉这背后的预设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有问题的。
相关材料就这么几句,后来也没有新的出土材料。别人要反驳也很难,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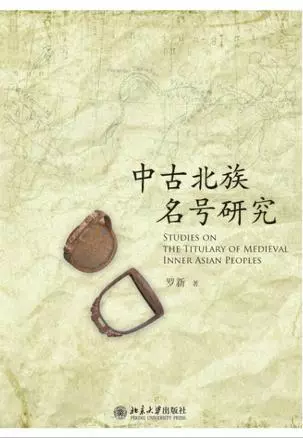
澎湃新闻: 受《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一文的启发,我想追问:汉族普通民众面对北魏皇帝赐名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反应?您的论文主要是谈授予者(掌权者)的举措,而被授予者的反馈究竟如何?当然这跟史料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根据墓志或考古材料,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探讨?
罗新: 我当时推测赐名几百个人,应该是有一个机构的,有一个赐名的班子,这个班子是秘密的。里面的成员级别可能不高,都是一些文人,让他们弄清楚,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去颁布。
我的一个学生写论文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赐名是不是被受赐者家庭接受,接受程度如何,使用范围如何,这还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家里可能没有行用赐名,当然在正始场合是用的。近年所出的“元苌墓志”,元昶不见于史。苌不像是赐名,苌就是长,长命、长安,都可以换用苌这个字。元苌的苌,可能是长命一名的缩略。那时候“长命”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汉语词早就连音带义进入代北鲜卑语了,所以代北集团的人取长命做名字并不奇怪。书写时按照汉语书写习惯,简写为元苌。按照元苌墓志,知道他官居高位,是个重要人物,但正史里却看不见。我的学生潘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考证,原来这个元苌就是《魏书》里的元俨。正史记他的赐名,家里安葬他时还是用他的本名,两不相干。这样,我们就知道,赐名不一定为家人所遵用。
澎湃新闻: 您在《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文中提出,唐代的皇帝尊号制度根本上渊源于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而武则天恰好借此自封“天后”,而后临朝称制。我的问题是,可汗号传统诱发了皇帝加尊号,并且形成一套制度,但皇帝尊号本身(所谓“允文允武,乃圣乃神”)是否包含了宗教因素,比如说武则天的尊号是否有佛教的因素?
罗新: 武则天的尊号里面带有佛教的内容,有的可能带有道教的内容,更不用说到了元代,那里面有太多宗教的内容。称号就是美名嘛,才不分什么道教佛教,只要觉得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用。
澎湃新闻: 唐太宗时期完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的修纂,高宗时期完成了《南史》和《北史》,有学者指出初期的唐朝政权是个具有异常高度历史意识的政权。今人研究南北朝史,必然要利用唐初编纂的这些历史文献,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陷阱或值得时刻警惕的地方?
罗新: 步步陷阱。但这几乎是唯一的材料。除了现在出土的一些墓志,文学有些诗文,几乎没有别的。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丧失,太严重了。
所以历史观很重要,得建立一套批判的历史观。你有了自己的问题,不要被这些材料迷惑住。学会从材料中读出材料背后的意图。我们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田先生,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叫“读书得间”,就是在字里行间去找背后的意思,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老师经常说这个词。现在人们说的少了。那时候见面就说,要读书得间、读书得间。

澎湃新闻: 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时期,变动的剧烈只有春秋战国和近代可比;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南北朝”,即大家熟知的魏晋南北朝和一般不称为“南北朝”的辽宋夏金元时期。您怎么看这两种说法?在您看来,就中国历史长河而言,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质?
罗新: 我们任何时候都在说某些时期变动特别大,当然有可能,但我们不能忘记一点,历史本身一直在变动的。所有重大的变动都是前面的小变化积累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只注意到那个重大变化发生的瞬间,比如只注意到辛亥革命的那一场暴动,可能没有注意到将近一百年来各方面的条件在往这方面指引。如果只注意到那场暴动,那是严重不够的。拿魏晋南北朝来说,至少有些变化在东汉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能只看到五胡十六国、北朝发生的动荡。归根结底,历史是写出来的,发生的历史跟写出来的历史不一样。刚才说过,历史没有主人公,没有线索。但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线索,都有主人公,都有“问题”——历史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历史上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历史学家的说法问题。他说这些的时候,是要表达某个目的。我们要注意他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
古代历史的特点是只记载重大的政治变动,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就写得很多,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熟悉的人物,应该超过两汉。我们大概只记得汉高祖时代、汉武帝时代、两汉之际、东汉末的人物和事件,东汉中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就不大管了。就此而言,做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是幸运的,因为这些政治变动都记录下来了。但是,这也容易造成错觉,你会觉得这个时候的历史变化特别多,其实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变动。很多重大的文化上的变动,如果不是因为有考古发掘和其他传世材料,我们几乎看不到。比如佛教,如果不是因为有石窟,有大量的造像碑,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文化上的,民众生活、社会形态的变化,可能出现了新的结社方式,人们有了新的交往方式,女性因为宗教而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她们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和价值空间,是过去所没有的。而史料在乎的是谁和谁打了战,谁赢了,并不关注更重大的变化其实是发生在另外一些方面。
澎湃新闻: 在您看来,日本的北族史、内亚史研究有什么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地方?
罗新: 我觉得日本学术挺有意思的,一方面日本学者跟西方学界关系非常紧密,另一方面它自有传统,它自己的研究传统非常深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问题、方法、资料整理等方面,它自有传统,甚至有一些东西比西方要强得多,比方说他们的蒙古研究和满文研究,特别是满文研究,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好。就这一点来说,姚大力老师开过一个玩笑,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玩笑当真,他说,你用满文材料,不需要懂英文,不需要懂满文,只需要懂日文就可以了,因为日本学者整理得很好,很可靠。
当然他们的传统也在变动发展中,比如早先比较重视与中国对立的游牧世界,把这个叫作朴素主义、文明主义,相当于罗马文明世界与蛮族世界的对立,这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不再把蛮族世界、游牧世界看成是跟中国历史相对立而存在的,他们是跟中国历史发生了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它们是自我存在的,而它们的自我存在是跟后面更大的内亚世界、甚至欧亚世界相联系,我觉得这是学术的新发展,不是什么分裂中国的政治阴谋。这个发展值得关注,因为阿尔泰语言和芬乌语言在空间上的确是连续分布的,因此它是一个广大的世界,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中国周边,只注意蒙古高原,以为已经看得够远了。日本学者是一直往西,看到乌拉尔以西,一直到波罗的海,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所以他们再也不把内亚史看成是东洋史的一部分了。这在学理上有它的道理。
澎湃新闻: 您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中指出,一切历史视野中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另外还提到文化体的概念。那么,文化体和政治体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和冲突?如果有,一般会有怎样的措施予以调解?
罗新: 我觉得文化体和政治体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对某种结构进行描述的时候,因为观察的东西不一样,就有不同的区分。政治体(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用政治关系塑造出来的,文化体强调的是用文化关系塑造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文化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汉字文化可以构成一个文化体,包括整个东亚,甚至越南,但它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体,相对来说文化体的连续性比较强,空间比较大,而政治体的连续性很不强,可能几十年就换一个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所以,政治体、文化体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政治体比较喜欢把自己描述成文化体。过去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两者不加区分。当我们讨论一个王朝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个王朝代表了某种文化,其实它只是这个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有政治边界,它想把边界之外的说成跟它在文化上也没关系,甚至是敌对关系,而事实是,那个是它所属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它不能在政治上征服人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边,就把人家推出去。另一方面,有的政治体无视别的政治体,人家明明是一个政治体,但你总是声称那是你的一部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至少我的研究倾向是,我们始终要重视政治体,因为政治体有不同的利益,虽然文化体、社会体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政治体有它特别的利益,它的利益是王朝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明白它的利益,才能理解它的政策、手段和统治方式。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