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国学术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广泛地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西方汉学对它的推动与影响相当明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国学术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广泛地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西方汉学对它的推动与影响相当明显。
关于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局外人的“话语权”有时甚至超过本民族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异的事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简单评判。不过,研究古代历史对于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研究领域今后能够得到持续的与实质性的进步,认真分析、思考这一现象,则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试图举笔者所熟悉的学术领域——主要是关于唐宋历史研究的一些例子,对于这种现象的表现、原因与利弊稍作分析,并就如何树立学术自信的路径略陈己见。
一、理论饥渴与汉学心态
笔者此前曾撰小文,指出当前史学界存在着一种“理论饥渴”的症状。[1] 这里再稍作补充。 所谓理论饥渴症,指学者们痛惜本学科可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说的一种焦虑心态。这首先可以从近年学界对探寻新理论方法的不绝呼声来观察。有学人甚至将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范式未见更新的状态,描述为一种“理论危机”[2]。也有学者反思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学术史,认为其中的一个不足就是“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3]。当时,笔者虽然指出了“饥渴”的各种症状,却并未及深入分析其成因,只是简单提到,这可能与新一代学者对传统经典理论失于教条主义而造成的疏远感,以及困惑于如何推动学术发展的心理压力有关。其实如果稍加深入,还可以发现,经典理论的主体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一些总体性的宏观结论,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历史理论”或曰“史观”[4],它虽然在理论信仰的层面给了学界以指导,不过宏观理论与落实到可供具体“操作”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史学理论”者,存在着一定距离。经典理论属于具体研究方法的那部分内容,大多是关于某时某地具体史事的结论,一方面,理论界一向认为这些具体结论对于历史研究虽然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涉及到研究不同方面的人类社会活动,其中有一些,经典理论的积累较为丰厚,例如关于经济学就是如此,但也有许多方面,或者涉及不多,或者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经典理论无法给予我们以现成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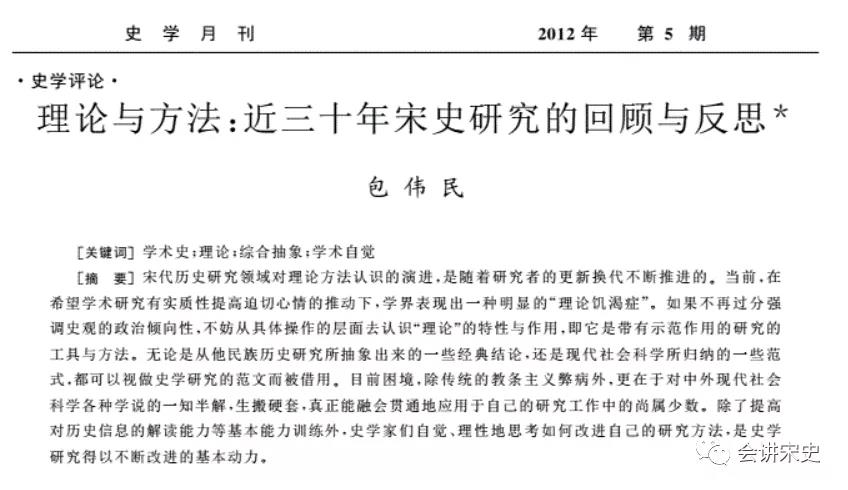
经典理论无法包揽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史学将已往的人类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这一研究对象许多必要信息的缺失,已至历史学很难归纳演绎出一整套针对当时人类社会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种“历史的社会科学”——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话,所以不得不经常借用人们针对现代社会归纳演绎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借鉴引用其中各不同门类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常有待于它们研究的进展,提出新见,以便得到帮助。可是及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学科,发展比较迟滞,其所能够提供给历史学借鉴应用的学术资源,也就极为有限了。 再一方面,虽然我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不过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20世纪初年在西方学术影响之下构建起来的一门新的人文学科,长期以来,因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战争,发展很是缓慢,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仍然相当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础性的学科规范,都不甚健全,亟需参照一些成熟的学科,引为借鉴,以有利于提高。 于是,出现了大量译介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现象。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我国学术思想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时期,“文化热”方兴未艾,知识界与出版界联手,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其中有几种大型译介丛书尤其引人注目,例如从1981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2012年共出版十四辑600种。在关于海外汉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则非数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开始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可。截止2013年,这套丛书共译介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161种,既囊括了费正清等名家的代表作,也推出了一些其作者相对年轻、但在丛书主持者看来其论说不乏价值的著作。近年来更按专题,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至今,依仍每年推出新书十余种,在知识界与出版界享有盛誉。在此之外,其它一些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各种译介西方汉学著作,面广量大,比较重要的如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文本,中华书局推出的《世界汉学论丛》数十种,各省市出版社几乎无一未推出过数量不等的译介海外汉学的著作,例如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等等。三十余年来,虽未见有人作过精确的统计,如果说这样的译介著作已超过千种,估计不致夸大。

专著之外,各类学术杂志也多开辟专栏,或撰文,或传译,介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陆续被建立起来,展开对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这些机构大多办有专门以研究、介绍海外汉学为主题的专业期刊,如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世界汉学》,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汉学集刊》,以及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汉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机构还经常性地组织召开关于海外汉学的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学术专著,讨论、介绍海外汉学。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译介工作的推进,国内学者接触了解西方汉学学术成果越来越方便,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出现了重视、借鉴西方汉学的现象。 在这样多方面的推动之下,西方汉学开始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产生持续性、全方位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丛书主编刘东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5] 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对学术的正面推动意义不容质疑。在各个专题具体研究之外,最有意义的,一是有助于基础性学科规范的确立,另一则是对一些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以“新史学”为标榜的社会史,或者以“华南学派”为重要代表的历史人类学,还是常常揽动学界一池静水的个别争议性议题的提出,例如所谓“新清史”的说法等等,无不如此。2004年,邓小南在梳理国内宋代史研究学术史时,就曾指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取径、方向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6]所以有学者这么说:“在我们看来,我们一直是在做中国自己的学问,其实背后却受到国外汉学治学模式的很深影响,它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学术。”[7] 可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矫枉过正往往是最为常见的认识路径。在“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的格局之下,一些为推动者所始料未及的现象于焉产生。这就是刘东所说的“现在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中国也净是汉学意识,年轻学子更是惟恐学汉学家的风格学得不像,这恐怕也是问题”[8]。张西平这样界定所谓的“汉学心态”:“但另一方面,西方汉学作为主导世界文化的欧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学术界对它的接受也显现了另一种特点:汉学心态的出现。这就是对西方汉学的一味追求和模仿。”“急切地套用西方汉学著作中的学术术语,照搬西方汉学的研究方法,这已经成为当前文科研究中,特别是在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论,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几乎都可以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著作中找到原型。”[9]一些尽管相当不经、却比较能迎合民众心理的西方学者的论点,经过一些文化人士的鼓噪,其影响甚至已经溢出学界,波及到了社会,例如关于“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即是。[10] 影响过于强化所带来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学者的论说为标准的现象,这些当然不仅无法对学术研究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更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它的发展。因此,有学者甚至将对这种复杂影响的评判,提升到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这样严重的程度。[11] 在一些具体的研究取向上,类似的批评也不少。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评近年来西方汉学流行的区域研究方法,认为它“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但在中国,由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欧洲存在差异,这种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不能不令人担忧。[12] 在大量译介三十余年、并且目前势头仍未稍见消减之时,针对西方汉学对我国学界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冷静客观地评估这一学术潮流,并站在学术本土化的立场上,就如何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走向深化,提出自己的思考,是这一学术领域每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学者不应回避的任务。 
二、西方汉学的主体性与其特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以及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最早比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之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出于更有效地向中国民众传播“上帝福音”的需要,基于对中国社会主导阶层的认识,在利玛窦从最初穿着僧服,到后来更换为儒服的所谓“易服事件”之后,耶稣会士们将传教对象集中在士人阶层,并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信息中,尽量放大其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所管理的“开明君主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以至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得以借用耶稣会士所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13]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逸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
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不脱这一规律。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关系缓和,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来作出对研究对象的观察,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那些宗教的与政治的等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时使得其学界困惑与沮丧,或者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着学者们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所谓“中国中心观”这样的命题被提出,但究其根本而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它。在这里,它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gos Jullien,1951-)的例子来作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自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而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1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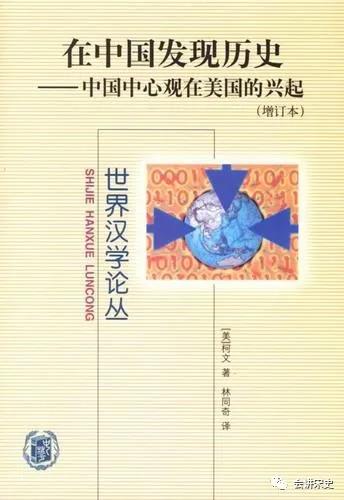
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非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莫属。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15],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坚雅的‘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16]。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无论是清代中期还是清代末年,中国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上一级城市人口与下一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关系,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呈现较大的差异。施氏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模式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17] 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18]因此,那些“检验”工作当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观察家们的这种“外来者”立场,误将他们“内化”了,就免不了会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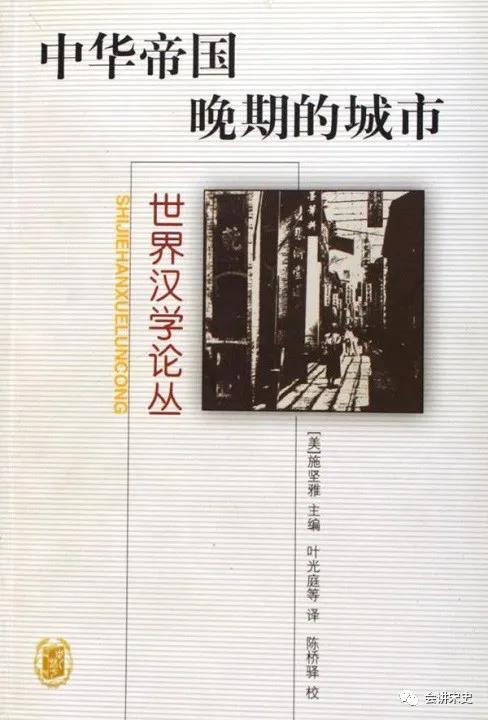
有学者已经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使其研究在理论界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19]。或曰:“一方面,他们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对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获得一席之地,又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说明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是‘中国中心观’的学者,他们虽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但由于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套用于中国研究。”[20]造成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汉学家的这种外来者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似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试验田。所以说,汉学“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西学”[21],它是一门西方的学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从立场到情感都转移到本土这一方面来。 根据这样的分析,再来观察学界长期以来批评的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学术假说,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他们本民族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时先生在评说“汉学一望无际,触处皆是”,“可是‘汉学中心’却未在任何地方出现”现象时,认为“主要由于研究的传统和关注的问题彼此不同,每一地区的汉学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22]。如果对余先生的评说略作补充,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世界各地汉学所展示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当然不是指中国历史这个研究对象,而是可能指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其二,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 也就是说,西方不同地区的汉学研究,其发生与发展自有因缘。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论是他们提出的议题、观察的取向,还是其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与归纳总结的学术倾向,都有着内在的隐情。中国学界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了解隐藏在每一部汉学著作背后的文化因素与学术史背景,也就很难把握如何才能恰当地借鉴利用的分寸。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学术要求也许是勉为其难的。这大概是为什么有人会对西方汉学“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三、走向实证与学术自信 那么,“汉学心态”之惑究竟应该如何破解呢?空洞地指责学界缺乏学术自信是没有意义的。学术自信与否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在现阶段,就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发挥本土学者在掌握历史资料与感悟历史情景方面的长处,通过复原更为准确的史实,来为进一步的理解阐释奠定基础。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各专题研究中取得切实的进展,来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历史阐释学,树立民族学术自信,从而走出“汉学心态”。下文,笔者将以近来讨论唐宋城市史专题的体会,略作说明。当今,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在其研究方法的层面,正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不过受历史学基本特性的制约,在研究方法层面,史学也有自己的一些显著特点。例如,史学研究不得不被动地依赖于存世历史信息来才能展开研究,而无法像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科学的一些门类那样,可以主动地去寻求研究信息。而且,存世的历史信息总是那么的残缺不全。因此,如何应对研究信息残缺不全的困难,就成了史家们无法逃避的功课。也因此,史学研究就必然是一个史实重构与现象解释(概念演绎)并重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评判学术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尺。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研究过程当然也需要有论证的环节,不过它们与历史学研究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社会,许多社会现象为众所周知,既不必为那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否大费周章,论证过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绎多于实证归纳,历史学则不然,特定历史现象的存在与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论证研究。所以,史实重构工作是否可靠,就成了下一步概念演绎的基础,前者失之毫厘,后者就可能谬以千里。在中国古代的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所谓宋代发生了“城市革命”的假说,比较典型,可引以说明本文的论点。宋代“城市革命”说最初由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23] 此书所讨论的议题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出一辙,[24] 它试图回答近代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伊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当时技术所可能利用资源的顶峰,宋代以后,受资源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的总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在质量上却再无提高,即所谓只有数量上的增长(Quantitative Growth)而无质量上的发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这就是他所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25] 为了证明宋代经济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的二手成果,来描述在宋代产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所谓的“城市革命”正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唐宋城市历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了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统计其书中有关描述史实的引文注释,超过90%出自日本学者的论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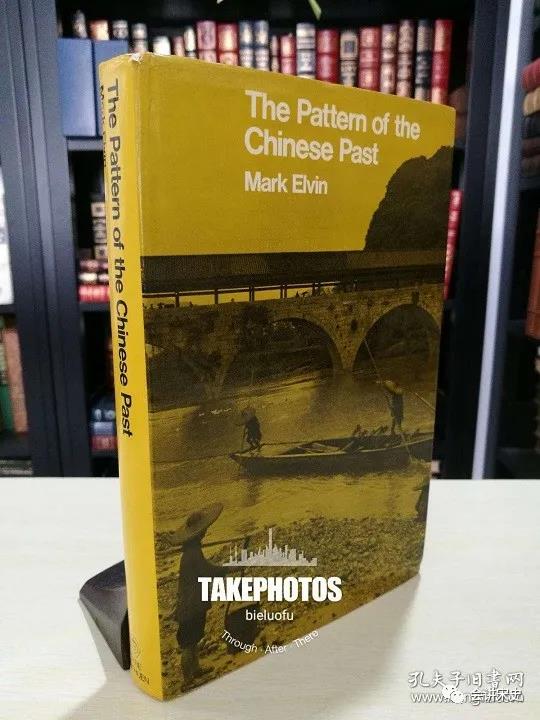
值得指出的是,伊氏此书的议题,反映了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这当然说明了前文所讲的西方汉学家们总是站在本民族历史经验的背景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现象。也因此,这也就说明了伊氏在引用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时,有着明显的选择倾向。所谓中世纪“经济革命说”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书主题能否成立的前提。由此可见,所谓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在伊氏推论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在于其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进,而只是作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说的一个铺垫。因此这一论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一种定性描述而已,用以表达对主要由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间城市发展史实的认可,以及伊氏本人对于如何描述这种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选择:“革命”。这一概念既在史实重构方面全无贡献,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创新。而且,这原本也并非是伊氏论述的重点之所在。数年后,当美国的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文集时,他在全书第一编的《导言》中,归纳传统中国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发展史,专列一节,题作《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列出了“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26]。很显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创,这些关于“革命”的“鲜明特点”的史实描述,也几乎全出自日本学者之旧说,仅就这一点而论,若说施氏对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自是实话。不过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并非针对唐宋时期,他归纳那些“鲜明特点”,只是为他讨论我国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铺垫而已。令人不解的是,从伊懋可到施坚雅,他们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虽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论述目的与论证特点,当这个概念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之后,却被不断“哄抬”,最终被誉为“理论”,认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深化”[27]。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的说法也被众多论著所征引。个中缘由,除了它迎合了数十年来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模式的心态外,[28] 看来就是“汉学心态”在作怪了。如何破解这种心态,在“革命”与否的概念上与之纠緾是无谓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取径,是重新检验日本学者关于唐宋间城市演变史事的描绘,是否符合史实。核心内容当然在于如旧说所描述的,从唐代的城市居民区(坊)与市场区(市)相互分隔、封闭状态,随着坊墙倒塌,市制崩溃,转向宋代的沿街开店、居民区与市场区相互混合的开放状态,亦即所谓从“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则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转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可以与西欧城市史相互映衬了。在这里,关于市制,旧说的核心论据,就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29]。新近的研究已表明,这一敕条指令“不得置”者,并非泛指一般的市场,而是指要限制在高级市场设置市官。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一般市场(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将商业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与其说是为了“限制”商业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方便官府征取商税。到了宋代,商贾虽然有了在城市其它区域设立店铺的自由,但在实际的城市生活中,商铺仍多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宋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州市县市,并未成为如加藤繁所称之“单纯的地名”[30],大多仍为活跃的城市市场地块。与此同时,由城墙等物体所标识的整个州县城区,又由国家法规界定为广义的城市市场,商品进出城市须纳门税,与前期市的区块相仿。其与前期的差异性,基本体现在市的区块与市民阶层的扩大。[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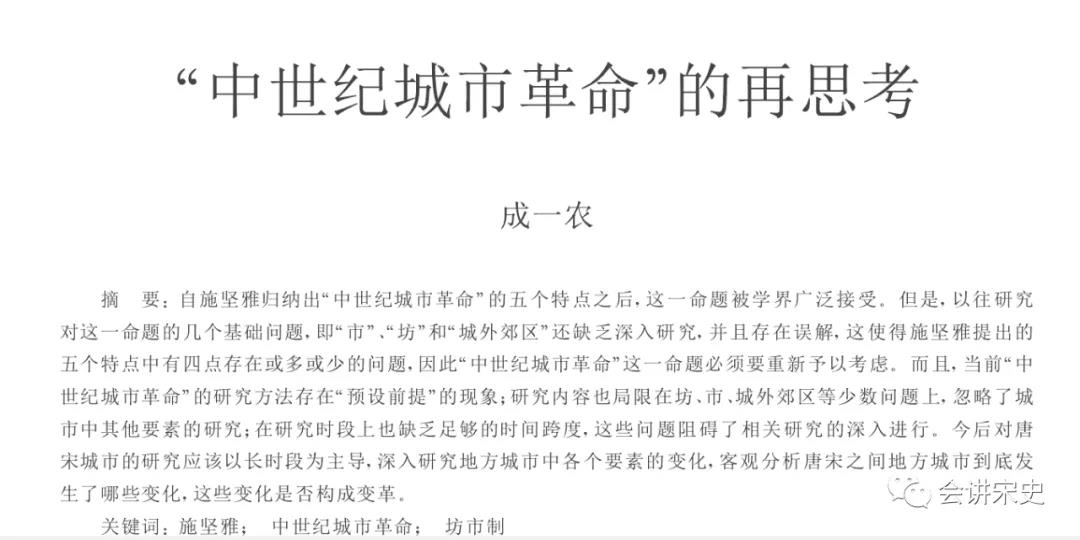
与此同时,由唐代律令所描述的严格的、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坊区制度,显然只推行于以京城为主的少数规划城市。这一制度相对多地被地方城市所模仿推行,已经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史事了,而且大多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各地扩建罗城,才乘机重新整顿城区里的里坊布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唐初到唐末五代,地方城市的坊区都只不过是一种以户籍控制为目的而编组的基层行政单位,它以居住区块为基础,但却并不一定就是封闭性的区块。在现存文献中,均未见有在罗城中营筑坊垣的记载,考古发掘也未见有可以确证的坊墙遗迹。中唐以后各州府城市(特别是节镇驻在城市)大规模地兴筑或扩修罗城,在罗城内普遍推行里坊制,正说明各地军阀、官府对城市居民及其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 ,而非如旧说所云,晚唐五代时期城市中里坊制逐渐松弛,终致崩溃,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日趋自由。[32]总之,所谓从封闭的“坊市制”转向开放的“街市制”的描述,无疑夸大了唐宋间城市结构演变的力度,并不符合史实。唐宋之间城市无论在经济还是其它方面的发展,虽然极其显著,不过新近的研究已经可以证实,以所谓从唐到宋坊墙倒塌、市制崩溃为主要论据的“城市革命”说,恐怕无法成立。这样一来,在这些虚构的史实基础之上演绎出来的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些认识、并进而牵扯到关于中国帝制后期历史演进轨迹的一系列推断,显然就有了重新考虑的必要。我们也就有了可能,来钩勒一幅与西欧不太一样、更重视唐宋间历史承续而非断裂的演进轨迹。关于宋代“城市革命”说的检讨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如何切实提高研究水准、走出“汉学心态”的一条路径,或曰一个方法:发挥本土学者掌握历史资料方面的长处,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有时候,这种重构不一定非得着力于那些“前人尚无研究的空白点”,用心于重新检验前人的旧说,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面。前人的研究无不都是从史实考释逐步展开的,他们的研究条件在某些方面其实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寻既已困难,现代化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误并不意外。可是,迷信旧说,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旧说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却不胜枚举,这就使我们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础之上。“汉学心态”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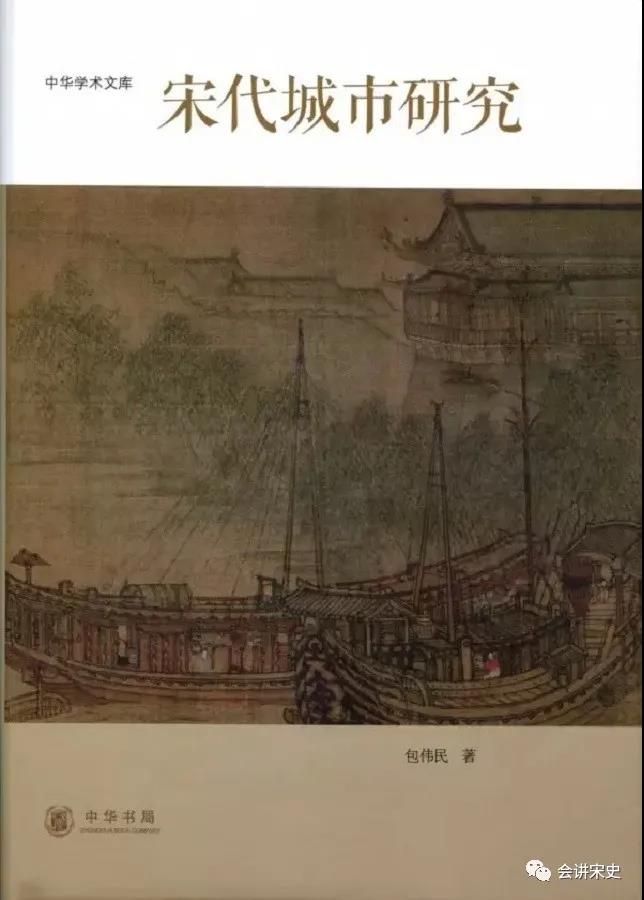
四、结语
外国人看中国,当然会与中国人看中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不可能要求外国人如同中国人一样来观察中国,也不必要赋予如本文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以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而且,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之深入发展,仍需要在方法、规范、思想等多方面向西方汉学学习。译介工作仍然很有意义。当然,如果对于译介哪些汉学专著的筛选工作做得更用心、更专业化一点,效果会更好。不过,我们还是将西方汉学放在“它山之石”的位置上去吧,不应让它喧宾夺主。 为什么应该走出“汉学心态”,主要的理由只在于:中国人看中国应该、也必然比外国人看中国来得更准确、更深刻一些。为什么?除了对历史资料掌握可能更全面,理解可能更准确,解读的立场可能更贴近实际等等理由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史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之际,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贴近感悟,仍然应当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占居至关重要的位置。 由于存世历史资料的偶然性与零碎性,它们所反映的历史现象难免是局部的、片面的,乃至不可避免地——表面的。所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充分认识历史资料不足的前提下,鉴别它,解读它,尽力从局部与个案中,拼凑出触及事实真相的历史全貌,以期收到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效。所以历史资料的解读总不得不先于论题的构建。更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史实的重构无法通过依据大量、全面的历史信息来统计归纳,而经常不得利用一些描述性的文献,采取“举例子”的方法来得出。在这一过程中,对资料的解读既已面临不小的挑战,“例子”的选择是否具有典型性,更考验着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于是,对特定阶段历史全局的掌握,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感悟,有时就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大概就是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与更具“技术”意味的社会科学式研究方法的重大区别。在我国,历史学作为传统“学问”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强调的是读圣人之书,行圣人之道,内圣与外王合为一体。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讲,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虽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来,这种物我不分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学者的客观立场,有着莫大的不利,不过它也有着社会科学方法所无法企及的长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物我一体,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浸淫其中,感悟其中,常能给零碎的历史信息补充一些至关重要的、背景性的历史场景,以达到真正理解历史的目的。同时,时至21世纪,我国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理论体系本土化奠定了可能的基础。历史学科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拥有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如果我们文化自觉的意识能够更强一点,学术管理体制能够更科学一点,史学研究更多地走向本土创新是必然的。 [0]关于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学界有不同的命名,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中国学。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领域,笔者以为名之为汉学比较恰当。参见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一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参见包伟民《“理论饥渴症”——中国古代史领域学术生态一瞥》,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日第1版;《“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第20-29页。[2]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第33~34页,见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3]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第555页。文载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9-564页。[4]参见张艳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文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55页。“史观”或称“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参见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0页。[5]参见王洪波《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的引进》,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7日第14版。[6]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第23页。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7]参见崔秀霞《汉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与交流——“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综述》,载《中国文化研究》 2005 年秋之卷,第177-180页。[8]王洪波《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的引进》。[9]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一讲,第27、28页。[10]参见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文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第145-149页。[11]顾明栋《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第93页。文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第79-96页。[12]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4、9页。[13]参见周宁《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第二章《大中华帝国(天堂传说之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140页。[14]张西平《汉学作为思想和方法论》,第143页。参见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16页。[15]胡勇军、徐茂明《“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文载《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8卷第3期(2012年5月),第28-34页。[16]朱炳祥《“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再认识——以摩哈苴彝族村与周城白族村为例对施坚雅理论的检验》,文载《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55-64页。[17]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第28页。文载《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18]参见陈倩《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第103页。文载《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100-104页。[19]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第117页。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106-120页。[20]陈君静《施坚雅中国城市发展区域理论及其意义》,第68页。文载《宁波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64-68,118页。[21]刘东《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第9页。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第13-15页。[22]余英时《开幕致词》,见李宗焜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中央)研究院2013年,页i-ii。[23]Mark Elvin(伊懋可),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中国过去的模式),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第113-199页。[24] 关于“李约瑟难题”,参见Joseph Needham(李约瑟), 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The Syndics of t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中译本题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25]Mark Elvin(伊懋可),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13-199页。[26]G. WilliamSkinner(施坚雅)主编:The City in Late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California, 1977。中译本题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多人合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27]参见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6-159页。[28]笔者称近二三十年来史学界在讨论唐宋间社会变迁时、一味强调历史发展的单一思维方式为“发展”模式,参见拙作《宋代城市研究》序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中华书局2014年,第1-41页。[29]王溥《唐會要》卷八六《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點校本下冊,第1874頁。[30]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第296页。文载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8-303页。[31]参见拙作《宋代城市研究》第三章《城市市场》,第172-236页。[32]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第267-274页。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第77-87页。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作者授权本公号发表,依据作者word版本,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