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时鉴教授简介 黄时鉴教授简介
黄时鉴,1935年9月生于上海,原籍湖南长沙。1958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1979年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1979年调至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任副教授,1987年任教授,从1998年起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蒙古史、元史和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编著和整理的书籍有:《元朝史话》《耶律楚材》《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一一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与龚缨晏合作)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 
《大漠孤烟》序 黄时鉴 2010年中秋前夜
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大学里度过的。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2008年对我来说有点特殊的意味,到了那年,我在大学里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已历半个世纪。这五十年经历的事情不少,但学术生涯却很简单,先是在内蒙古大学任教近二十一年,以后就一直待在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当然,严格说来,我在2001年末退休,任职并无半个世纪,但退休后仍继续做研究,自以为这样的学术纪年世可以算数。2008年底,蓦然自问此生如何?回顾往日,别的事情似乎已渐模糊。可是所撰之文,白纸黑字,倒是清楚的。于是动手搜检,编出一个目录,计算宇数,约有百万余宇。 有了目录,相关的存本大体上也翻了出来,再将它们厘定分编。十几年以前,1998年出过一本《东西交流史论稿》,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尚有约七十万字,无非是抽印本、复印本、电子本,另有两篇未刊稿。分编不难。我做的历史研究,由于兴趣较广,似乎采点分散,不过归纳起来,也就两个领域,一是蒙古史元史,二是中外文化交流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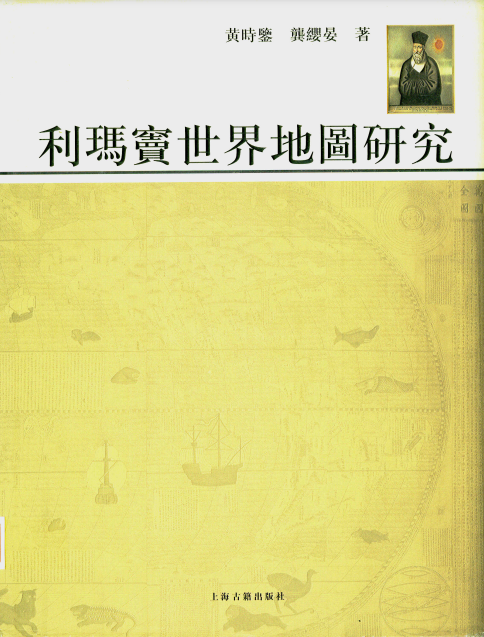
2004年出版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1998年我编印文集《东西交流史论稿》时写过一篇较长的序言谈过自己在治学方面的一些体会和看法;同年,为《学林春秋》写《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又陈述过自己学习史学和从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此两文已有重复之处。原先讲过的,今不再赘述。在1998年以后,我继续发表了近20篇论文,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三书。后两书是编著,它们的问世可能有助于在学术层面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史图像资料的开掘和利用。前一书导致我对地图文化交流史生发浓厚的兴趣,这方面的继续探索已成了我晚年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寻找和细读古地图,令我迷恋和陶醉! 
1998年出版的《东西交流史论稿》 在《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中我曾经说过:“就自己的生活而言。我感到人生把握不易。就自己的学业而言,我进入史学专业可以说是偶然的。一周前,我已到了七十五足岁。现在我想补充说:史学与我不期而遇,然后相伴终生。史学真是一个好专业,而且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更是好专业。它要求治学者有长期的积累,板凳可坐一生冷。即使间或中辍,而若持之以恒,仍有可期。相当一些专业似乎难有这样的适应度。它又可以容纳资质不等的学人,让他们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才能,在辛勤劳作之后收获相应的成果,其容度是十分宽广的。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此生更复何求? 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是缺乏根底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做不出多少成果。但鉴于我以上对史学的认识,在北大受教于众师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治学过程中,就自己发现的问题写下的这些文章,仍想它们可以是铺路之石、盖房之砖。张广达先生在他的文集“总序”中说,他较早发表的研究西域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论文,“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和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拙文显然也大多是对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和分析,但它们在较宏观方面或诸多棱面上可资读者参考之处,或就力有不逮了。至于先生这二十年来的深刻体认——在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需要对史学的传承和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反思,需要取得历史知识学层次的一些认识,我就更瞠乎其后,难以企及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拙编文集的性状,可能只是我这样的历史人的境况和勉力而为的一种呈现而已。 黄时鉴 2010年中秋前夜于杭州苦竹斋
黄时鉴:板凳可坐一生冷 翻看浙江大学历史系黄时鉴教授的履历,会发现他的兴趣点一直在不断变化。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在中国近代史组;毕业后最初从事的是蒙古史、元史研究,并参与了《元史》的校点工作;1979年来到杭州大学后,又逐渐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可是在主编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整理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写了多篇文章之后,又扩展为东西交流史,后来又迷上了古地图,并且在年近70岁时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至世界前沿;同时,他还对图像资料发生兴趣,1999年出版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2008年又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从此书可知是他最早发现了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参加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中国人的珍贵图像。学术兴趣的不断转移,固然与其兴趣广泛有关,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可看出他对史学的情长意深的追求,他对新资料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识见,以及他在论述史事过程中不时透露的逻辑力量和思想火花。 北大五年 读书报:一般都认为,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受重视的,北大当时有很多名教授,当时他们上课有什么特点? 黄时鉴:我是1953年入学的,为了在北大试点改五年制,我们这一届的物理系和历史系延长了一年。1953年到1957年春夏之交,学习相当稳定,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是少有的。 当时北大教师们的严谨学风,对我们学生来说,首先是从他们对教学的态度上体认的。简单归纳,就是认真、扎实。当时各门课教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我们这届起,授课老师都重新编写讲义,油印后发给学生。中国古代史的讲义比课上讲授的内容丰富得多,里面有大量史料引文,老师又浓缩了在课堂上讲,总体上给我一种沉稳、从容、游刃有余的感觉。 读书报:您觉得对您后来治学影响最大的是哪位老师? 黄时鉴:应该是邵循正老师。他为我们近代史专门化的学生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的对外关系”,另一门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到了专门化课,他是不发讲义的,我当时记了详细的笔记。前一门课讲每个时期的重点问题。后一门课按重大事件讲述史料,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样一段一段讲下来,中文的、外文的值得注意的史料,一一给你点了出来。每次上课,他总是把一两大叠西文书放在讲台上,讲到哪本就给大家看看。听了这样的课去治中国近代史,就是“师父领进门”。我们现在要给研究生们讲授的课,恐怕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邵先生的讲课使我深深感到,做研究必须掌握原始史料。后来我长期以来就形成了积累史料、寻找新史料的习惯。做什么课题,总是从原始资料开始,从新资料发现新课题。另一方面,就是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的学术动向和各种信息。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 读书报:您1979年离开内蒙古大学,是因为学术兴趣转移了吗? 黄时鉴:年过四十岁以后,明显感到不适应呼和浩特那里的气候,到了冬天很难受,每年封冻期有五六个月。大约从1975年起,那里不让调离的限制开始松动,我稍晚一些也终于办成调动,从内蒙古大学到了杭州大学。 学术兴趣转移应当说是在到了杭州大学以后发生的。198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仍是蒙元史,但从所写的论文可以看出,从1980年代中期起我已开始更多地注意元代的中外关系史。1985-86年间我第一次出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在那里用英文发表《波斯语在元代中国》一文,不久美国的《伊朗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就来约稿写有关条目。接着我撰写了《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和《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等文。同时我开始讲授古代中西关系史的课程,并主持编写《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这样,到1990年代初,我的学术兴趣就集中到了这个领域,元代本体史就顾不上了,继续做的只是涉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方面。做学问会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而且最好身边有一个小群体可以互相切磋研讨。如果我当时去了南京大学,在韩儒林先生那里工作,就可能会继续主要做蒙元史。结果到了杭州大学,单做元史有一种孤独感。此外,澳大利亚之行,打开了自己的学术眼界,可能也是导致我兴趣转移的一个因素。 读书报:您转向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与之前的蒙元史研究有所关联吗? 黄时鉴:我想有两个内在的关联:一是蒙元时代的中西关系有大的发展,它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上伸下延,便开设了古代中西关系史的课程;二是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古代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简单地说,也就是对不同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存在文献中的一些特殊语词的审音和勘同,从中发现和认知一些史事的方法。有时候,用这种方法可以取得有趣的新的认知甚至较大的突破,具有科学的原创性。而由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时空范围更广,这个方法就更有运用的机遇和效果。 读书报:您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是这个转向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吗? 黄时鉴:我转向的时候是有计划的,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按计划做完。在做这个《年表》以前,我已经写了若干篇论文。如果就著作而言,《年表》是第一个成果。我看到日本出过解说插图科技史年表,从中得到一个启发,就想编一部这样的中西关系史年表。我的设计是:分时期立章来编,每章有解说(条目),这是点;有年表,这是线;有概述,这是面;再加上插图和最后五种附表,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古代中西关系史的全貌。在这个基础上再采点撰写一批论文,最后有可能编一部新的中西关系史。主编这样一部《年表》,花了好几年功夫,到1994年才出版。 读书报: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黄时鉴:在编《年表》的过程中我渐渐积累了不少问题,其中有的可能发展成为课题。但是,当年表问世时我年已六十。我在思考做什么研究课题时已经习惯于分析自己所临的主客观条件。转的时候,涉及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其主要中介是传教士,我意识到不懂法文不行。大约就在1990年吧,我去跟研究生的法语班学习。可是当时工作很忙,学了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又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学到的东西也就容易淡忘。这次的法语学习并不成功,这也使自己意识到,有的课题再好,但力所不及,不能勉为其难。只有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才是上策。 读书报:这是说的主观条件。那客观条件方面您这些年来有什么感觉? 黄时鉴:要说做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西方文献资料的利用还是不够理想的。但是客观条件已在不断改善中。多次出国访学导使我有新的文献或图像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国外图书馆的一些特藏,逐渐被做成缩微胶卷或胶片,现在也已比较容易读到。特别是杭州大学图书馆在1994年买下了荷兰IDC公司做的两种特藏的缩微胶片,一是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迄于1850年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另一套是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的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有了这两大宗文献,做研究和带研究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客观条件。再说现在大学图书资料经费也已增多,能配合研究的需要来采购图书和电子数据库。此外,通过网络来搜集资料的途径非常宽广,其速度更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当然,也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譬如,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通过馆际申请,向本地区和外国的图书馆取得图书的某些部分和论文的复印件,这类服务都做得简捷到位,而且费用由图书馆支付,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研究进展,值得借鉴。 读书报:最近这些年,您出版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图像方面的著作,是因为对图像史感兴趣了吗? 黄时鉴:图像应该说是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图像首先给人以直接的视觉印象,使史事呈现具体而生动的面貌。第二,图像给研究者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历史。第三,它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 广义的图像概念也可以包含地图,但在历史资料的分类方面地图是相对独立的。地图史的研究可以认作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制图学又是属于地理学的。所以《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一种学科交叉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研究。而我和龚缨晏合作做此项研究时,更侧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这就属于地图文化交流史的范畴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我编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这三本书都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前一本是文献,后两本是图像。每本书前面都有导言,意在将这些资料放在合宜的位置,供读者在使用和做进一步探索时作参考。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图像资料非常丰富,我只编了两本,希望这样的图像资料会引起更为深广的学术性的关注。 读书报:您做历史研究时间相当长了,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您为什么能如此持之以恒,您会说是什么? 黄时鉴:我想是“兴趣”吧,是兴趣。我从小兴趣较广,但在进入史学之门后,我就被它的无穷魅力吸引住了。研究中不断引发出兴趣,兴趣又不断推动我做新的研究。跟着兴趣走,也有缺点和损失,但走得比较自在,乐在其中。现在已至老境,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要收,可是只要继续从事研究,总会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收中又难免有放。就这样吧!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