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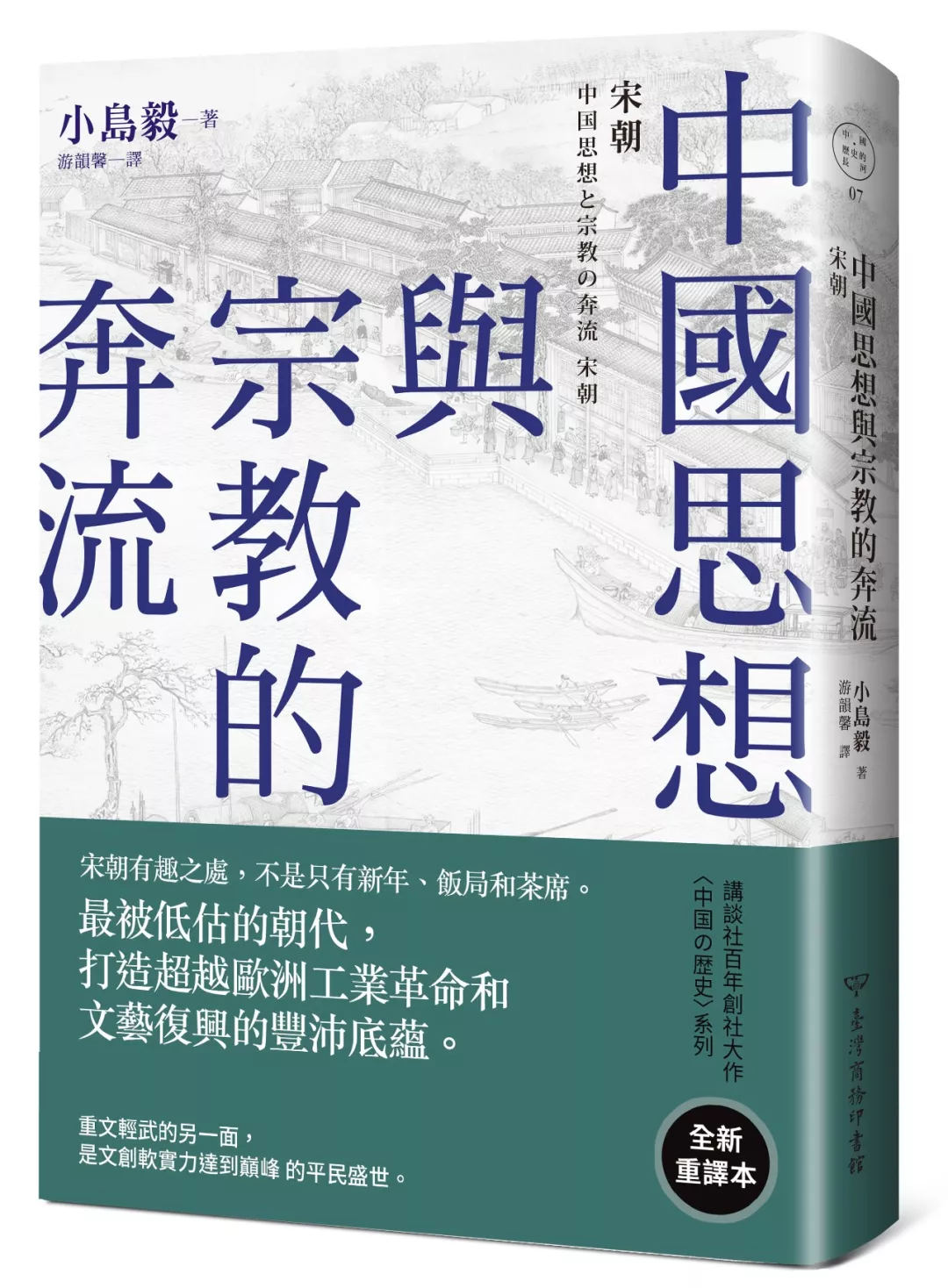
柳立言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史学方法→重建历史→产生史观 本导读主要针对是书的四大主题作出修订和补充:政治和制度(第一至四章、第十章)、宗教(第五章)、士大夫(第六章)和庶民(第九章)。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提出更多和更新的问题,如宗教里的巫觋、庶民中的妇女,和科举所产生的中产阶级政权。第二,介绍一些研究方法,希望读者在眼到、心到和口到之余,也能手到。第三,比对宋代与今日的议题,看看古今的差距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大。
许多人动辄就说,要用新的史观诠释历史。就逻辑而言,应先重建历史,然后才产生观点或理论,如倒过来做,就容易先入为主。根据历史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后到达共产主义,这就不大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宜硬套。同理,英美模式的民主能否作为所有国家的归宿,也一样说不得准。「历史」与「历史研究」不尽相同,前者绝对有真相,后者不一定能找出真相,就好像司法人员不一定能找出杀人凶手,有时还会冤枉好人,所以一定要讲究研究的态度、方向和方法。 历史研究是优是劣,关键不在旧或新,而在议题重不重要、论点合不合理。所谓重要,对象是古人而非今人。今人认为重要的议题,古人可能无感。史学家最害怕的,是拿着〈从男女平权看宋代的性别关系〉或〈转型正义为何没有在宋代出现〉等论文,通过时光隧道回到宋代,发现没有人认为有意义,没有人认为跟他们相关。研究历史必须设身处地,透过古人的眼睛去看、用古人的思维去想。 所谓合理,是指切合史学三论:论据+推论=论点。论据是以史料作为证据,如文言文不好,就无法正确解读,也不能抓出关键字句,更可怕的是误中副车,把跑龙套当作主角,用为主要证据大加发挥也大放厥词。推论有两项工作,一是把证据分门别类和排好优先次序,二是对着它们进行逻辑思考。时常听到的批评是「飞跃的逻辑」,从大小前提得不出作者的论点。就此来说,研究历史与法律异曲同工,都是搜集证据,进行逻辑分析,希望找出真相和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我一直不明白,历史系和法律系的入学分数为何相差甚远,难道逻辑不好的人能唸好历史吗? 谈宋代而上溯至安史之乱,是否合理?这涉及京都学派的史观——唐宋变革论。记者出身的内藤湖南及其学院弟子宫崎市定发现,历史一面延续一面变化,唐宋之间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足以淹没那些延续,把唐宋切为两段。巨变的源头就是安史之乱,乱前的中国属于中世,乱后属于近世(见文末附表)。巨变如革命般的强烈,故称变革;读者切勿轻重不分,把强弱悬殊的大、中、小变统统称作变革。历史事件的前因和后果往往不只一个,称之为「多元」是对的,但多元之中,是否有优先次序?一项水利工程也许同时有利于祖国和殖民地,但何者较为优先?优先(不均平)又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谁说了算,应该找出合适的切入点,进行历史研究而非政治解读。 从权力斗争中诞生:黄袍加身、陈桥兵变 许多人都比较后周太祖郭威与宋太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但往往徒见其表,未悉其里,其实两者都有权力斗争的性质。后汉高祖留下郭威等旧人为顾命大臣,新君和新臣起而夺权,把他们杀戮殆尽。郭威领兵在外,逃过一劫,但阖家被害,故后来没有儿子而由外甥柴荣继承皇位。他杀回京城,皇帝死于乱兵,朝廷宣布另立新君。世上竟有如此不智之人,没有推辞以便郭威顺势即真,反从地方匆忙上京,不知打算做傀儡皇帝,还是要夺取郭威手里的大权。接下来便是五代第一次黄袍加身,而准皇帝转向黄泉报到。世宗柴荣死后,军权落在太祖和韩通之手,后者较占优势,「周之军政,多决于通」,其子并建议杀掉太祖以独揽大权。陈桥兵变的重点,是太祖以御辽为名,带走韩通辖下的大军,透过威逼和谈判,把他们降服,本来答应不伤害所有大臣,后来还是由一名部下把韩通杀死,太祖并无加罪。太祖自己以武人君临天下,却说其他武人不足以治理大藩,恐怕不无减少权力竞争者的用意。 宋太祖开国,也开了历史的倒车。五代的一个特点是兵变频仍,骄兵逐帅,强帅易主。后周世宗是五代最有为和敢为的皇帝,一口气杀了六十多位不听号令的将领,足令强帅胆寒,不敢觊觎。陈桥兵变,又大开强帅易主之门,这是太祖不得不赶快杯酒释兵权的原因。他较前人高明之处有二:一是以利禄和婚姻代替烹杀,此后皇室一直与武家联姻,直到亡国。二是以制度代替权宜,把军权作长远的分割。两支禁军中,侍卫马步亲军司的首长职缺由五个减为两个,实际上分裂为马军和步军二司;殿前司仍维持一司,但首长由四个减为位望较低的两至三个。如此一来,难出强帅,纵使仍有悍将,手下亦无大兵。 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以制度驾驭宦官 汉、唐和明都有宦祸,宋代也出了童贯,即《水浒传》的童太师,既剿平方腊之乱,也因联金灭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反招来靖康之祸。童贯入主枢密院,掌管的是军政,整个宋代唯此一次,其他的宦官从军,大多负责监军和领兵,并屡立大功。北宋共有四十三位宦官在《宋史》立传,二十七位建有边功,受到武人和史臣的重视。今人难以体会宋代文人与阉人相处的心态,例如有没有轻视他们。 神宗时,阉将王中正开边有功,苏轼作〈闻洮西捷报〉,咏叹「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他跟另一位巨璫陈衍颇有交往,后来在政争中连累陈氏得了「结托词臣」的罪名。不少宦官能武、能文、能理财、能治水、能开河,简单说就是作为皇帝的佣人,他们的任务随皇帝的志趣而转向。 除了徽宗一朝外,北宋君臣大都谨守太祖和太宗的家法,防范宦官滥权和越权。最重要的政策是,当宦官离开内朝到外间工作,大都不是以钦差的身分,而是被任命为外朝官僚制度内的正式一员,交由外朝监督和制衡。第一关要过的,是负责草拟和检阅诏旨的官员,他们可以拒绝起草或封驳不当的任命。第二关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大臣,如不签署,任命便难以通过。第三关是言官,可以要求皇帝收回或更改成命。三关都过了,出外当差,便受上司的管辖。仁宗时保州有乱事,都转运使把监军的宦官也召来平乱,「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宦官带着护卫到来,都转运使看不顺眼,骂他「诸军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耶?」把护卫逐退。其实,若无宰相蔡京的护航,童贯是当不了枢密使的。文人可制衡而不制衡,反沆瀣一气,弄到国破家亡,不能独怪宦官。 重文,但并非轻武 有谓五代重武轻文而宋代重文轻武,何能同属一个历史时段?这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关键词要明确界定,不要陷入朦胧史学。「文」和「武」相对清楚,但「重」在何处、「轻」些甚么?有人说科举一方面吸收人才另方面加以拢络,那么五代北朝的科举从未间断,武人为何要收拢他们看不起的文人?在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大多数文人在战场上是被轻视的,也因此在权力的天平上轻于武人。然而,打仗靠军饷,要有充足的军饷,便要发展各行各业,此处便是文人用武之地,他们恐怕也会在此轻视武夫。乱世出人才,五代有些文人兼擅民政、军政和财政,颇有盛唐宰相之风,例如最先提出「先南后北」大战略的后周文臣王朴,「马前拜侯伯,阶下列椹斧。叱咜气生风,将校汗如雨」,他们何敢轻文? 除去少数例外,五代在军事上轻文,在民事和文化上仍然重文。五代毕竟有五十三年,许多武二代都兼习文武,希望继承唐代允文允武和出将入相的传统。读者要研究五代的文武交流,至少有四个切入点:文武俱习、文武兼治、文武通婚、文武并仕。假如一家之中,父习武而子习文武、叔既领军也能治民、婿来自武家而媳来自文家、兄为武职而弟为文职,则文武相轻可能不如想象中的严重。史料在哪里?在墓志里,其中的家庭信息,远多于正史。这样切入,可将家庭史和政治史一炉共冶。 许多人说宋代不是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代,事实上宋代初年在不少地方继承五代,尤其是后周的措施。五代武人凭军功向上流动,成为刺史和节度使等地方首长,必须兼管民政,有时留下吏治败坏的恶名。对此,不少人相信《宋史‧文苑传》的说法,谓「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亦即重文轻武的由来。又有不少人相信太祖的名言,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以为宋代不再用武人治理地方。其实两者都仅说了「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读者要发掘更多的真相,可从制度切入。 宋代的地方制度是路、府、州、军、监,都可由文人和武人担任正副首长。武人大多出任军、监,和较需用武的路、府和州,如沿边和盗贼等重区。北宋末年,府大约有三十八个,州二四三,军五十二,监四,州与军的比例是四.六七比一,多少可看到武人长贰之众,遍布今日的河北、河东、陕西、湖南、广西、广南等地。宋代对武人的批评,很多是针对他们的民政、文事而非武功。反过来说,能吏治的武人,往往得到士大夫的赞美和重视,而吏治欠佳的文人,同样受到士大夫的轻视。仁宗时,进士出身的夏竦(英公)为南京留守,喜欢额外用刑,武人马洵美为路级的提点刑狱(即陆剧〈大宋提刑官〉宋慈的职位),实在看不下去,上章弹劾夏竦欺罔。司马光说,「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可见不管文人武人,都会看不起做歪事的人,不管此人是文是武。读者必须注意,这里所轻的是事,不是人。 因此,所谓轻武或抑武,可分两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文人。一是武人或文人的作为实在可议,这种轻或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且对事不对人,不能说是歧视。二是文人为了揽权独断等原因而故意贬抑武人,这种就是不合理、别有用心或似是而非的轻武。欧阳修引述武人的抱怨说:「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未尝不是一种党同伐异或争权夺利,可能正是所谓武人不得干政、不得进身中书和枢密,及不得为大帅的重要原因。 另方面,武人也受到重视。纵使他们本来因为武人的身分受到歧视,但后来在品德、知书、民事,或司法上有所表现,便由被轻转为被重。宋代不少高层武臣来自民间,每以百姓疾苦为念,或亲力亲为,或借助僚幕,成就一番文治,得到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庞籍、范镇、梁适、贾昌朝、王安石和曾巩等许多进士名臣的赞扬、举荐、立传或撰写墓志。即使是中下层武人,亦有机会赚得朝廷和百姓的赏识,因为宋代以军人修桥筑路灭火治水救灾和重建,不乏表现的机会。好男未必不当兵,且可能赢得名垂久远的颂德碑,或进入供奉武人的诸多官祠和民庙,影响民众对武人的观感。《宋史》说:「大抵武夫悍卒,不能无过,而亦各有所长;略其过而用其长,皆足以集事」。这何轻之有,反是重其所长,何况既能集事,宜获重视矣。 枪杆子:燕云十六州与澶渊和约 有人说过去的历史课本因为汉族沙文主义,故重宋轻辽。若论文化,的确是辽向宋学习较多,辽道宗甚至许下「愿后世生中国」的愿望,写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诗章。若论武功,乍看辽胜于宋,其实不然。有人说宋代舍征兵而募兵,是常败的一个原因。平心而论,征兵是业余兵,兵罢归农,训练不如专业兵。五代也是募兵,时常打败契丹,也曾大输一次。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交换契丹的援军,建立后晋和称臣,其子不服,引来契丹问罪之师。后晋先是大胜,却因用人不当,将帅移忠,稍战便降,不过契丹随即发现统治不易,匆忙北返。后周世宗收复了部分的燕云,发展为关南要地。北宋初年也曾屡败契丹,后来乘胜北伐,打算收复全燕,可惜功败垂成。休养生息之后,再次北伐失败,元气和士气俱伤,才开始屡败。辽人反守为攻,也曾惨败,双方僵持不下,开启了澶渊缔盟之前长达十年的和平。真宗初生之犊,不愿主动谋和,且不惮亲自巡边,曾对一位大将说:「契丹入塞,与卿所请北伐之日同」,可见君臣都有第三次北伐的打算,可能导致辽人先下手为强。 澶渊之战是辽人进攻、宋人防守。辽人竭尽全力,死伤无数,竟未能攻下关南之重镇瀛州,故兵抵澶州时不无后顾之忧。澶渊之和是辽人放弃关南的主权,换取宋人的岁币,是否屈辱,要看读者如何认定燕云十六州的归属了。无论如何,宋不能攻辽,辽也无力克宋,双方平等,各有一个朝贡体系。陶晋生先生喻之为天有二日,可谓一语中的。 笔杆子:科举与中产阶级政权 宋代科举彻底改变了唐宋统治阶级的构成和性质。唐代虽有科举,但名额常被世家大族占去,寒门难以争胜,故统治阶级仍以世家大族为主,开放程度不高。北宋统一,是以北统南,统治阶级其实跟唐末五代差不多。抽象来说,宋初政权仍是北方性格,常以北人的价值观念来治理天下,例如太祖和太宗看到南方诸国有些已实行父子分居分产,就无法忍受,硬要恢复同籍共财,违者处死。变革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才真正发生,拜科举改良所赐,社会流动快速展开,有四重意义: 一、统治阶级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旧的和新的世家大族虽仍占有各种优势,但已无力垄断。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再有如天地之隔,彼此的流动是史无前例的频繁,平民子弟上升为统治者的比例是史无前例的高,仕宦子弟下降为被统治者的比例也是史无前例的高。这既带给被统治者无尽的希望,认为富贵并非全然命定,后天仍有可期,也带给统治者无穷的压力,因为不但富不过三代,贵也是难逾三代,而各种得富贵和保富贵的方法,实质的如家族制度,虚无的如积阴德看风水,乃成热门话题,超越前代。 三、南方人透过科举逐渐入主中央政府,登墉拜相者比比皆是,形成南北人共治,打破了宋代开国由北人主政的局面。由北方人以枪杆子打来的政权,现在由四方人士凭着笔杆子共享合治,也算是一种和平的政权转移,其性格也由北方转变为兼具四方,未尝没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科举入仕者的出身是高低与贵贱俱有。就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来自士、农、工、商、军、医、仆等家庭;就家庭身分来说,他们有的是嫡子,有的是庶子(妾之子如宰相韩琦和史弥远),甚至私生子,有的是守节妇之子,有的是改嫁妇之子(如副相范仲淹)。他们执政之后,是否多少会照顾这些家庭和人士的利益? 无论如何,能够负担举业的,大多是中产之家(年收入可折合常米二百担)。可以大胆的说,宋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产之家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对前代是断裂,对后代是开启,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统治阶级的成分改变了,许多改变随之而来,例如平民和南人成为立法和司法者之后,将民间和南方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念带进法律领域,使宋代的法律文化呈现中产之家的特色。 新的法律主动允许子女与父母同籍而异财,承认子女独力赚得的财富属于个人私财,局部打破了同居共财的儒家传统,反映宋代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新法也容许子女控告继母侵犯他们对家脉或家产的继承权,局部打破子女不得控告父母的礼法传统,反映宋代法律由强调当事人的身分,转而依据其罪行来审判。南方女子多投入生产,有见及此,新法提高未婚女儿对父亲遗产的继受权,她以前只能得到兄弟聘财的一半,现在可得到兄弟继承分额的一半。新法让寡妾享有对亡夫遗产的受养权,司法上也让她享有一定程度的立嗣权。新法也提高赘婿的继受权,以反馈他们对妻家经济的贡献。 总之,新的法律注重「责任」与「权利」的对应,不大管这个人的性别或地位。在这前提下,新法造就了有条件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力保障中产之家的财产权,刺激了宋代经济的革命性进展。也许资本主义不能在传统中国发生,问题不在韦伯所说的法律,而在其他因素。
(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作者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