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菊 然而有人说这些例子仅仅表现了现代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些方面,是不是需要一整套现代戏曲程式呢? 郭汉城 这不是谁能设计出来的,而是戏曲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根据生活、剧情、人物的需要不断创造不断积累出来的。程式问题解决了,戏曲的现代化与民族性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用戏曲程式表现现代生活这个矛盾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我们要予以肯定。建国以后,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文化遗产特别是戏曲?像日本那样博物馆式的保护是必要的。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根据艺术的发展规律、特点,发展它,这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因此,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发展,戏曲现代戏已摸索出规律性、经验性的东西,可以说已经成熟,今后的发展会更快、更好。 “谁泼青山,片片火般娇?”
李小菊 您和张庚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等是研究中国戏曲的重要著作,戏曲科研人员、戏曲院校的学生几乎都要读这几部著作。您能谈谈当初编撰这些著作的缘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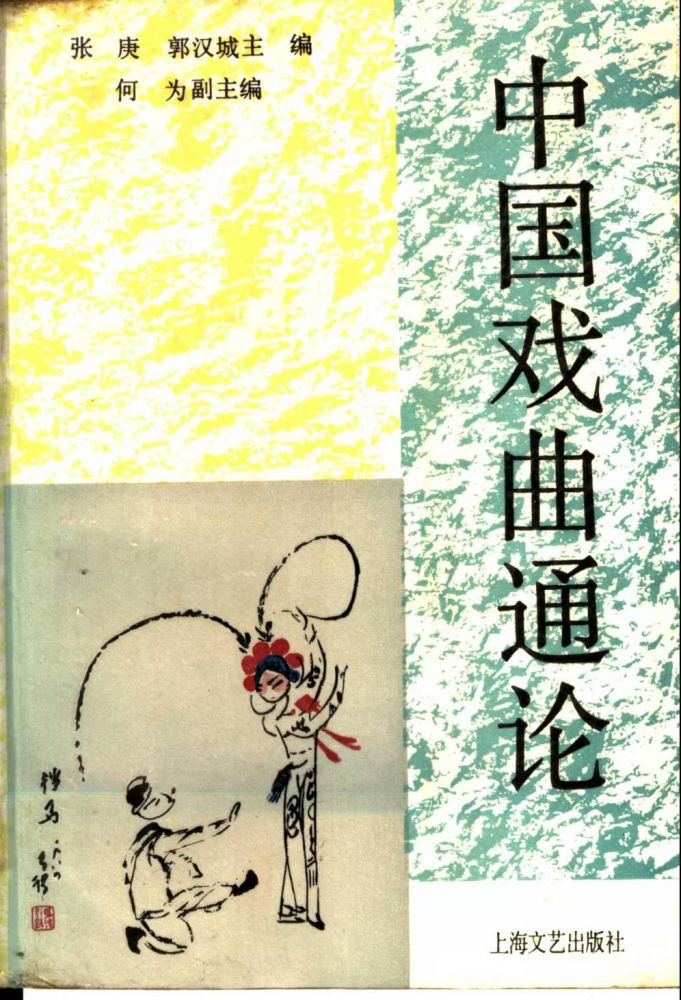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郭汉城 从长远来看,《通史》、《通论》的编撰是为了中国戏曲理论的建设。在此之前,有一些研究戏曲史论的著作,如王国维、日本青木正儿的著作等,为戏曲史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不足,主要是研究戏曲文学,对戏曲表演研究不足。我们的史、论是以新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作为指导进行编写的,系统研究了戏曲的发展规律,尤其是《通史》,在比较丰富的史料、文物的基础之上,勾勒出戏曲的发展历史,寓论于史;更重要的是不单讲文学,而且讲舞台艺术,是对戏曲全面、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戏曲改革的客观需要。随着戏曲改革和创作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从事戏曲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剧团、演员的理论水平有限,因此客观实际需要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来指导、解决这些问题。 李小菊 尽可能完备地搜集研究对象的资料,进而勾勒其历史发展轨迹,最后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程。您和张庚先生主编的一史、一论等,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戏曲研究又与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同,除了固定的文献资料之外,还有许多文物资料,更是动态的舞台综合艺术,你们在编撰过程中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郭汉城 密切关注现实问题,从戏曲艺术的客观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研究戏曲艺术、撰写戏曲史论的重要方法,这也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学风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由于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不但包括戏曲文学,也包括舞台艺术,也由于戏曲《通史》、《通论》的撰写目的是为了解决戏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有思想上的,也包括艺术上的,因此,我们的《通史》、《通论》很自然地要关注这些问题,这就突破了以往戏曲史论研究的局限,成为我们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李小菊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以前是学中文的,对戏曲的了解更多的是对古代戏曲剧本的关注,而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之后,接触到舞台表演,对戏曲艺术才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戏曲通史》的学术价值也更加重视。 郭汉城 我们通史、通论的编撰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参与编撰的人员,大多是从事戏曲改革、戏曲研究的同志,他们对戏曲的现状、对舞台艺术都非常熟悉。我们当时为编写戏曲通史,成立了一个研究组,还调了各省搞戏曲改革、戏曲理论的同志,请他们对编写《通史》和《通论》提意见,把他们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提出来,供我们参考。 李小菊 集思广益是《通史》和《通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能够突破前人研究的重要原因。过去戏曲研究主要是靠文献资料,而且都是文人、学者的个人行为,《通史》、《通论》都是集体研究、集体攻关,因此能够做到全面、系统、综合。但是每个参与课题的人水平可能参差不齐,见解可能也有不同,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郭汉城 我们的《通史》、《通论》不但在撰写之前写出提纲,请许多人来提意见,然后修改更订;而且在每一章节写完之后,都请人来审阅批评,然后再进行修改;完稿之后也请人进行通稿审阅,才最后定稿。包括在《通史》和《通论》已经出版之后,我们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再版中进行修订。但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非常有限,有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譬如我们在撰写过程中想尽可能脱离简单的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用简单的阶级观来看待问题,我们也难免受到影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不只研究作家作品,而是将其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艺术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综合研究,现在看来这也是有优点的,不能完全否定,否则又回到以前戏曲研究就文学论文学、就艺术论艺术的研究路子。 李小菊 这个问题在《通论》中似乎更明显,这可能与《通史》客观描述、寓论于史的编撰特点有关,而我在阅读《中国戏曲通论》时,就发现有一些时代局限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郭汉城 《中国戏曲通论》的情况有一些不同。除了上面讲的时代影响之外,它主要是结合实际问题,为解决戏曲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而编写的。我前面讲过,《通史》、《通论》的编写除了为建设中国戏曲理论,还为解决戏曲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这一点《通论》比《通史》更加鲜明。《中国戏曲通论》与一般艺术概论的著作不同,它讲的不是一般的艺术原理,而是在分析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比如《通论》讲戏曲文学的人民性,是结合当时的情况,为了解决用简单的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进行戏曲研究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撰写的。 李小菊 您这样一讲就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些疑惑。《中国戏曲通论》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立足现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特点是值得研究者借鉴的,比如第一章“中国戏曲与中国社会”中,从新剧种的诞生过程推论中国戏曲的产生过程,我觉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郭汉城 是的,这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 李小菊 中国戏曲研究院对我国戏曲研究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其理论研究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以张庚先生和您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人员,由于地处前海,被称为“前海学派”(中国戏曲研究院原址在北京饭店西的南甲道,后迁至东郊白家庄,1958年迁至东四八条,后来又迁到了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您对这个称呼有什么看法? 郭汉城 这个称呼是别人叫的,具体怎么出来的,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通史》、《通论》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这个称呼就出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要创一个学派的想法,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也并不是到前海才开始的。我们只是为了戏曲理论研究和戏曲改革工作需要,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李小菊 您觉得一个学派的形成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郭汉城 “学派”历来都有。在一个开拓进取的时代,会出现各种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戏曲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其理论、创作都有变化。新的时代出现新的变化特点,出现一个学派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学派,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作为“学术共识”,来阐释戏曲,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条件。第二,要有与前面一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比如说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看待戏曲、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比较统一的、科学的方法、观点和立场。第三,要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实践上都要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三个条件是一个学派必须具备的。 李小菊 以您的三个条件来看,以张庚先生和您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科研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文艺理论为指导,采取理论与实践密切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戏曲进行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编撰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戏曲志》等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局面,完全具备成为一个学派的条件。 郭汉城 (笑)所谓的“前海学派”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张庚先生和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过态,在各种“头衔”满天飞的年头,还是听听大家说的吧。 李小菊 2008年第4期《艺术评论》有一篇关于王文章先生的访谈,题为《学术自省与文化创新》,王文章先生在文中指出:“‘前海学派’所体现出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关注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客观表达,尽可能地从不同的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去生发,做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独到的结论。”“其本质是在总结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学术自省。”我觉得这个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无论是您还是张庚先生,都一直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进行反省。 郭汉城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的学说都不是完美的,完美是不可能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认识的不足总是有的。时代发展了,应该有更好的、更科学的学派出现。戏曲艺术历史这么长,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必然会有错误的地方。有很多同志指出我们研究的不足,我们应该改进。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我们的研究是完美的,这是有自知之明的。 李小菊 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无论如何,这种研究都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角度和视野。 李小菊 您和张庚先生在学术合作中结成深厚的学术友谊。您能谈谈你们学术友谊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 郭汉城 我觉得学术合作和学术友谊最主要的基础,是学术目标和观点的一致。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合作得好。如解放以后戏曲要完成的任务,戏曲现代化问题等,我和张庚先生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这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实现戏曲现代化、戏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为共同目标,运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这是我们学术合作的基础。我和张庚先生一起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实际上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张庚先生人品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新型学者。他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戏剧都非常了解,对中国戏曲独特的民族特色认识非常清楚。他自觉地将戏曲研究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是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工作的前提下进行戏曲研究的。这是我最佩服张庚先生的地方。 李小菊 也就是说,共同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并且将这种理想与追求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促使你们在工作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学术合作中每个人的见解都会有所不同,你们在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郭汉城 张庚先生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精神,使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比如我们编《通史》和《通论》,大家都没有搞过,各自主要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争论非常多。怎么才能把大家的观点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就需要发扬学术民主。张庚先生在这方面特别好,他对戏曲的了解比较全面,但是他又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从学术框架的构建,到具体每一章节的内容,都让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集体讨论,然后定下来。他从不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压制不同的批评意见,而是把问题提出来,促进大家的讨论,在论证的过程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假若领导者没有学术民主精神,没有宽洪大度的胸怀,很难想象《通史》、《通论》能够出来。 李小菊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严峻,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单纯的学术研究也会动辄得咎,但也正是在患难之中你们的学术友谊才更能经得起考验,是这样吗? 郭汉城 是的。就中国戏曲研究院来说,大家一起编撰《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是出于共同的学术目标和学术理想,因此相互之间不会太计较其他问题,能够包容观点不一致的人,而且采取保护的态度。张庚先生态度很宽容。他是一个真正讲学术的、实事求是的老实人,他以科学的态度做事,从来不随便跟风,从来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张庚先生非常爱护同事。在反“右倾”中,他自己挨了不少批斗,却默默地保护着我,6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评《斩经堂》的文章,遭到批判。张庚先生没有表态,只是邀请很少的人进行了小范围的批判,这就是一种保护。 
李小菊 相互尊重,相互爱护,并且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也是学术友谊能够长久的一个重要方面。您和张庚先生在合作中结成的深厚友谊令人羡慕,也令人敬仰。目前,中国艺术研究院仍然有许多集体项目,您对现在的年轻学者参与集体项目有什么建议? 郭汉城 集体攻关很重要。因为戏曲这种综合艺术,有些大的研究项目不是个人能完成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志同道合又有学术素养的集体来进行。另外,集体攻关也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有效办法。我们在《通史》、《通论》、《戏曲志》的编撰过程中,对中国戏曲的历史、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许多人都成了戏曲研究各个方面的专家。如果没有集体攻关,就没有《通史》、《通论》,也不会培养出这么多的戏曲专业人才。 李小菊 参加集体合作课题肯定会影响到个人的学术研究,您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郭汉城 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绝对的,处理好了,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比如《中国戏曲通史》从编写到出版,先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1962年,《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校样都出来了,但是后来政治形势紧张起来,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东西成了“封、资、修”,被封了起来。这三十年肯定会对个人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学术合作对个人的治学、为人得益更多更大。现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经济条件和政策条件都非常好,应该发扬集体攻关的长处和优点,在集体项目中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点,集体攻关与个人研究兼顾。因此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珍惜机会,珍惜时间,在为集体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同时,搞好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的戏曲理论建设做出贡献。
“偶入红尘里,诗戏结为盟” ——诗词创作的成就与特点 李小菊 长期以来,您一直在进行古体诗词的创作,有《淡渍集》。您的《淡渍诗词钞》又在2009年刚刚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张庚先生曾经书写了一首您创作的词,是吗? 
郭汉城:《淡渍诗词钞》,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郭汉城 (指着客厅里挂着的一幅横轴)这首词是1983年撰写《中国戏曲通论》时我创作的《江城子·香山红叶》,张庚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就把它写了下来,也算是编撰《中国戏曲通论》的一个纪念。 李小菊 这幅书法非常有纪念意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词创作的? 郭汉城 我从小就喜欢诗词,也喜欢民歌,也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写过古体诗词,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诗词创作上有所发展。在杭州学习期间,接触到许多新诗,尤其是郭沫若的诗词创作,对我也有影响,写过不少新诗。抗战时期在解放区也写过新诗。真正开始格律诗词的创作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心中有许多想法和意见,没地方说,也不敢说。一切工作都没有了,脑子又不能闲着,因此在下放到干校之后,开始尝试创作格律诗。格律诗好记,四句、八句、一个曲牌,可以装在脑子里,又能够抒发感情,因此就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诗词创作,一开始就再也放不下了。现在我九十多岁了还在写。 李小菊 您能谈谈您的诗词创作都受到哪些诗人和词人的影响吗? 郭汉城 我比较喜欢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辛弃疾、苏轼、李清照的诗词。特别是毛泽东的诗词,我非常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说明古体诗词仍然有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能力,就像传统的戏曲程式还可以表现现实生活。 李小菊 您在上世纪60、70年代创作的诗词创作,虽然充满悲愤,却始终积极乐观,苍劲雄浑,这与您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分不开。您能谈谈当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境吗? 郭汉城 我的诗词作品功力不深,但从不无病呻吟,都是有感而发。也从来不悲观,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这与学习马列主义和我前面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那段艰苦生活有关。另外,我的诗有理想主义的特点,我对生活、对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充满信心。著名画家、诗人蔡若虹先生说我的诗“穷年从不唱悲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李小菊 正如沈祖安先生所说,您的诗词中充满一种豪雄之气,这在晚年创作中尤为突出,如您的《八十自吟》:“镜里犹堪能饭对,兴来未倦少年歌。”显示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豪迈。这与您为人处事和理论研究的谦逊质朴可以互补。哪一面才是您的真实性情呢?抑或平易与豪雄,都是您的真性情? 郭汉城 我觉得“平易”和“豪雄”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心中充满悲愤,这种情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词创作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国家又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仍然对我们的祖国充满信心。 李小菊 观剧诗词和赋赠演员的诗词也是您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类诗词的? 郭汉城 我最早写观剧诗大概是在60年代,是我看了京剧《白蛇传》后写的。这首诗的创作有一个背景,当时印尼的苏哈托发动政变,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我看过《白蛇传》后,白素贞的身世使我产生了联想,就写了一组四首诗,其中一首是:“四周寂寂乱云飞,塔底沉音究可哀。裂石崩云终有日,红旗似火映天来。” 李小菊 这是从白素贞最终从雷峰塔救出来,表现共产党人终究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虽然您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但是一直在关心我们国家和党的命运,而且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学术研究文章无法表达您这方面的思想,就通过诗词创作表现出来。您大量创作咏剧诗,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写咏剧诗的比较少,您为什么会创作咏剧诗呢? 郭汉城 我写咏剧诗也有一种“探索”的意思。咏剧诗从古就有,但过去的咏剧诗主要是评演员,像演员的声色、声容等。我写的咏剧诗主要是从戏曲对当时国家、社会、人民的社会价值的角度写的,有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容,但得失如何就难说了。 李小菊 戏曲是叙事性的,而诗歌主要是抒情性的,您是怎么用诗歌来评论戏曲的呢? 郭汉城 咏剧诗要兼顾戏曲的情节与诗歌的抒情,同时也要把生活中的感慨、感受和情感融合进去。剧评是用理性的逻辑思维来阐释戏曲的意义、价值,而咏剧诗是用感性的形象思维来创作。 李小菊 您对上海昆剧团演的《钗头凤》既有评论文章,又有咏剧诗,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剧评与咏剧诗的不同特点。 郭汉城 是的。戏曲评论与咏剧诗虽然体裁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要对剧目的意义、价值进行阐释、评价。我关于《钗头凤》的剧评和诗,就体现了用不同体裁来表达相同的观点。 | 

